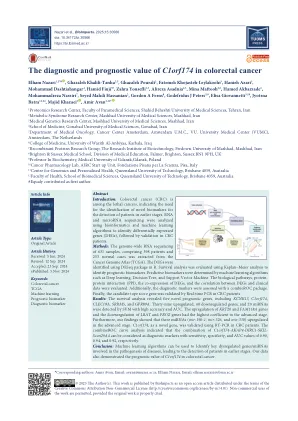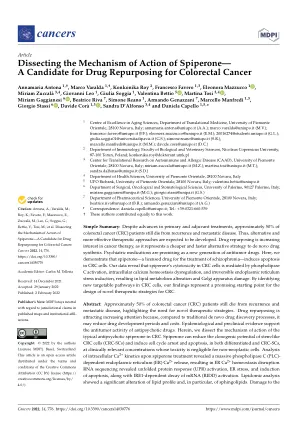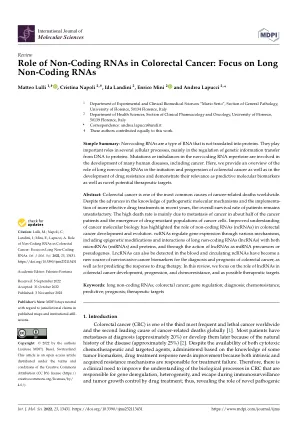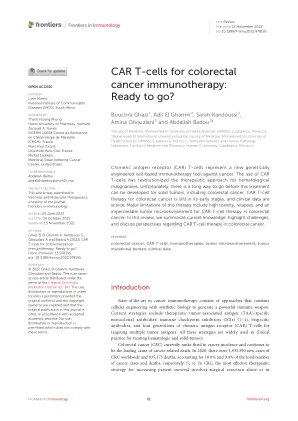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人工智能在基于 MRI 的直肠癌分期中的作用:系统评价
多项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 (AI) 在基于磁共振成像 (MRI) 的直肠癌 (RC) 分期中的应用,但仍然缺乏全面的评估。本系统评价旨在回顾 AI 模型在基于 MRI 的 RC 分期中的表现。对 PubMed 和 Embase 进行了搜索,从数据库建立之初到 2024 年 10 月,没有任何语言和年份限制。本评价纳入了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这些研究评估了 AI 模型(包括机器学习 (ML) 和深度学习 (DL))在基于 MRI 的 RC 分期中的诊断性能与任何比较器进行比较。绩效指标被视为结果。两名独立审阅者参与了研究的选择和数据提取,以限制偏见;任何分歧都通过相互协商或与第三位审阅者讨论解决。从数据库中共找到 716 条记录。其中,14 项研究(1.95%)最终被纳入本综述。这些研究发表于 2019 年至 2024 年之间。这些研究采用了各种 MRI 技术,并开发了多种 AI 模型。深度学习是最常见的。用于开发 AI 模型的 MRI 图像包括来自不同景观和系统的 T1 加权图像(14.28%)、T2 加权图像(85.71%)、扩散加权图像(42.85%)或这些图像的组合。这些模型是使用各种技术构建的,主要是深度学习,例如传统神经网络(28.57%)、深度学习重建(14.28%)、弱监督模型开发框架(7.12%)、深度神经网络(7.12%)、基于更快区域的 CNN(7.12%)、ResNet、基于深度学习的临床放射组学列线图(7.12%)、LASSO(7.12%)和随机森林分类器(7.12%)。所有使用单一类型图像或组合成像模式的模型在准确度、灵敏度、特异性、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和曲线下面积方面均表现出优于人工评估的性能,得分 >0.75。这被认为是良好的表现。目前的研究表明,基于 MRI 的 RC 分期 AI 模型表现出很高的性能,前景广阔。
C1ORF174在结直肠癌中的诊断和预后价值
摘要简介:结直肠癌(CRC)是致命的癌症之一,表明需要鉴定新的生物标志物以在早期阶段检测患者。RNA和microRNA测序,以鉴定差异表达的基因(DEG),然后在CRC患者中进行验证。方法:从631个样品中的全基因组RNA测序,包括398例患者和233例正常病例,从癌症基因组地图集(TCGA)中提取。使用deseq套件在R中鉴定了DEG。使用Kaplan -Meier分析评估生存分析以鉴定预后生物标志物。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例如深度学习,决策树和支持向量机)来确定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评估了生物学途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DEG的共表达以及DEG和临床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此外,使用Combioroc包装评估诊断标记。最后,CRC患者的实时PCR验证了候选TOPE评分基因。结果:生存分析揭示了五个新型的预后基因,包括KCNK13,C1ORF174,CLEC18A,SRRM5和GPR89A。39个上调,40个下调的基因和20个miRNA通过SVM检测到高精度和AUC。KRT20和FAM118A基因的上调以及LRAT和ProZ基因的下调在晚期阶段的系数最高。此外,我们的发现表明,三个miRNA(miR-19b-1,miR-326和miR-330)在晚期阶段上调。C1ORF174作为一种新基因。组合曲线分析表明,C1ORF174-AKAP4-DIRC1-SKIL-SCAN29A4的组合可以将其视为具有敏感性,特异性和AUC值0.90、0.94和0.92的诊断标记。结论:机器学习算法可用于识别与疾病发病机理有关的关键失调基因/miRNA,从而导致早期患者的检测。我们的数据还证明了C1ORF174在结直肠癌中的预后价值。
结直肠癌的新潜在治疗靶点
结直肠癌(CRC)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最致命的恶性肿瘤之一。尽管采用手术、放疗和/或全身治疗(包括化疗和靶向治疗)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晚期CRC患者的预后仍然很差。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治疗CRC的新型治疗策略和靶点。微小RNA(miRNA / miR)是一类参与转录后基因表达调控的短非编码RNA(约22个核苷酸)。其表达失调被认为是与CRC的发展,进展和转移相关的关键调节因子。近年来,许多miRNA已被鉴定为CRC耐药的调节因子,一些miRNA作为克服CRC耐药性的潜在靶点而受到关注。在本综述中,我们介绍了miRNA以及miRNA在CRC中的多种机制,并总结了基于miRNA的CRC的潜在靶向治疗方法。
结直肠癌中的致瘤细菌:机制和治疗
摘要 结直肠癌 (CRC) 是第三大常见癌症和第二大致命癌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肠道菌群在 CRC 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根据 CRC 患者的测序研究以及细胞培养和动物模型中的功能研究,一些细菌物种,如具核梭杆菌、大肠杆菌、脆弱拟杆菌、粪肠球菌和沙门氏菌与 CRC 有关。这些细菌可通过基因毒性物质导致宿主 DNA 损伤,包括 pks + 大肠杆菌分泌的大肠杆菌素、脆弱拟杆菌产生的脆弱拟杆菌毒素 (BFT) 和沙门氏菌的伤寒毒素 (TT)。这些细菌还可以通过影响宿主信号通路(如 E-cadherin/β-catenin、TLR4/MYD88/NF- κ B 和 SMO/RAS/p38 MAPK)间接促进 CRC。此外,其中一些细菌还可以通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创造促炎环境或影响自噬过程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反应,从而促进 CRC 进展。研究发现,使用经典抗菌药物甲硝唑或红霉素、抗菌活性成分 M13@ Ag(由无机银纳米粒子和 M13 噬菌体的蛋白质衣壳静电组装而成)、小檗碱和泽兰酮治疗可不同程度地抑制致瘤细菌。在这篇综述中,我们介绍了阐明几种 CRC 相关细菌的致瘤机制的进展,以及开发有效抗菌疗法的进展。特定细菌已被证明在 CRC 的致癌和进展中具有活性,一些抗菌化合物已显示出对细菌诱发的 CRC 的治疗潜力。这些细菌可能可用作 CRC 的生物标志物或治疗靶点。关键词 结直肠癌;微生物群;致瘤机制;基因毒性;癌症途径;肿瘤免疫
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再利用候选药物
1 意大利诺瓦拉 28100 皮埃蒙特东方大学转化医学系老龄化科学卓越中心;annamaria.antona@uniupo.it (AA);marco.varalda@uniupo.it (MV);francesco.favero@uniupo.it (FF);eleonora.mazzucco@uniupo.it (EM);20016274@studenti.uniupo.it (GL);giulia.soggia01@universitadipavia.it (GS);simone.reano@uniupo.it (SR);marcello.manfredi@uniupo.it (MM);davide.cora@uniupo.it (DC) 2 波兰托伦 87-100 尼古拉·哥白尼大学生物与兽医学学院免疫学系; konkonika.roy@doktorant.umk.pl 3 自身免疫和过敏性疾病转化研究中心(CAAD),皮埃蒙特东方大学,28100 诺瓦拉,意大利;miriam.zuccala@uniupo.it(MZ);martina.tosi@uniupo.it(MT);sandra.dalfonso@uniupo.it(SD) 4 皮埃蒙特东方大学健康科学系,28100 诺瓦拉,意大利 5 皮埃蒙特东方大学 UPO 生物库,28100 诺瓦拉,意大利;valentina.bettio@uniupo.it 6 巴勒莫大学外科、肿瘤和口腔科学系,90127 巴勒莫,意大利;miriam.gaggianesi@unipa.it(MG); giorgio.stassi@unipa.it(GS)7 意大利诺瓦拉东方皮埃蒙特大学药学系,28100;beatrice.riva@uniupo.it(BR);armando.genazzani@uniupo.it(AG)* 通信地址:daniela.capello@uniupo.it;电话:+39-0321-660-539 † 这些作者对这项工作做出了同等贡献。
与肝转移有关的结直肠癌的微生物群
肿瘤被认为存在于无菌环境中;但是,测序技术的进步改变了这一观点,并推动了肿瘤内微生物组研究的增加。研究表明(19-21)大多数人类癌症类型都有肿瘤内菌群,包括位于肿瘤组织周围和深处的细菌群落。基于肿瘤组织的某些内在特征,例如漏水,缺氧,坏死组织和免疫特权(22),肿瘤病变可能支持细菌侵袭,生存和生长。作为消化道中最大的部分,结肠菌包含大量的各种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与宿主肠上皮细胞紧密相关(23)。代表性的肠道微生物组可能包含数十亿种不同类型的微生物细胞,超过300万基因(24),并且可能占人类微生物组的70%(25)。肠道系统可以有助于细胞致癌,并在许多人类疾病中起关键作用(26)。大约20%的肿瘤与定期定居肠道的微生物群有关(27)。尽管已知肠道微生物群对CRC的发生和进展有明显的影响,并且新证据表明它也会影响CRC
使用多维类器官模拟结直肠癌
与大多数癌症一样,CRC 由一组分子异质性亚型组成,每种亚型都具有一系列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改变以及不同的肿瘤驱动因素。这种异质性使得标准的“一刀切”式 CRC 治疗方法无效。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某些 CRC(例如 EOCRC)的致病机制仍然不太清楚,对其分子特征的了解仍然很少。如果没有这样的见解,相关临床前模型的开发也将无法实现。因此,使用生理相关的人类临床前模型系统进行全面研究以描述疾病发病机制的潜在分子基础的需求既迫切又尚未得到满足。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疾病机制,还可以确保发现的转化潜力仍然很高。
非编码RNA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
摘要:结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之一。尽管近年来对结直肠癌发病分子机制的认识不断进步以及更有效的药物治疗的实施,但患者的总体生存率仍然不令人满意。高死亡率主要是因为大约一半的癌症患者发生癌症转移以及癌细胞耐药群的出现。对癌症分子生物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突出了非编码RNA(ncRNA)在结直肠癌发展和进化中的作用。ncRNA通过多种机制调控基因表达,包括表观遗传修饰和长链非编码RNA(lncRNA)与微小RNA(miRNA)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以及通过lncRNA作为miRNA前体或假基因的作用。 LncRNA 也可在血液中检测到,循环 ncRNA 已成为结直肠癌诊断和预后以及预测药物治疗反应的非侵入性癌症生物标志物的新来源。在本综述中,我们重点关注 lncRNA 在结直肠癌发展、进展和化学耐药性中的作用,以及作为可能的治疗靶点。
用于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的 CAR-T 细胞
癌症免疫疗法的最新进展包括将细胞工程与合成生物学相结合以产生强大的免疫武器的方法。当前的策略包括治疗性肿瘤相关抗原 (TAA) 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CI) (1-4)、双特异性抗体和四代针对多种肿瘤抗原的嵌合抗原受体 (CAR) T 细胞。所有这些策略都广泛用于治疗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的临床实践中。结直肠癌 (CRC) 目前在癌症发病率中排名第三,并且仍然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2020 年,全球有 1,931,590 例 CRC 新病例和 935,173 例死亡病例,分别占癌症病例总数和死亡总数的 10.0% 和 9.4% (5,6)。在 CRC 中,提高患者生存率的最有效治疗策略是单独或联合手术切除
结直肠癌,肝转移和生物疗法 - 纯
摘要:(1)背景:大肠癌(CRC)是全球癌症死亡最致命的原因之一。其第一个主转移扩散扩散到肝脏。不同的机制,例如上皮 - 间质转变和血管生成是这种侵袭的特征。在此阶段,可能的选择是可能的,并且仍在争论中,尤其是在靶向治疗剂和生物疗法方面的使用。(2)方法:对文献的综述着重于结直肠癌肝转移的临床管理以及在该领域的生物疗法的贡献。(3)结果:在临床环境中,外科医生和肿瘤学家认为CRC中的肝转移分为两组,以发射适应性的治疗方法:可切除和不可切除。围绕这两个实体,靶向疗法和生物疗法的组合具有很高的兴趣,目前经过测试,以了解它们必须在哪种分子和临床状况下用于对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