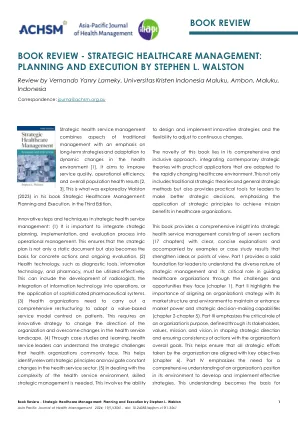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书评:现代战略的新缔造者
在另一篇重要文章中,约书亚·罗夫纳 (Joshua Rovner) 描述了新的作战领域如何带来新的战略,并概述了必然会出现的三重历史模式。最初,随着新的作战领域的出现,人们寄予厚望。然后,随着人们对对手在这些新领域能做什么以及他们调整战略来对抗我们的问题产生担忧,人们开始感到恐惧。最后,随着技术和对抗在冲突中遭遇挫折,人们开始接受局限性。罗夫纳对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之外的潜在人造领域的出现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四十年前,很少有人预测到互联网的发展。二十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当今社交媒体的性质。类似的意外变化将迫使观察者重新考虑他们对网络空间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影响”(1,091)。
书评:……时代的合同和合同法
这篇书评是褒扬性的。Ebers、Poncibo 和 Zou 的书中每一章的内容都值得称赞。这些章节探讨了对合同学者、法律从业者、法官、立法者和缔约方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本书也很及时。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几家初创公司开发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帮助律师及其客户减少合同过程中的摩擦,更好地理解合同条款的后果。例如,Kira Solutions(一家成立于多伦多的公司)使用机器学习来高效准确地自动识别、提取和分析合同内容。2 但随着人类将越来越多的合同自主权交给人工智能,人们不禁想知道合同原则将需要如何改变。
书评:空中力量先驱:从比利·米切尔到大卫·德普图拉
理查德·P·哈利恩 (Richard P. Hallion) 巧妙地捕捉到了比利·米切尔准将 (Billy Mitchell) 在处理根深蒂固的作战思维和“所有权”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激情、毅力和坚定的信念。米切尔是一位真正的特立独行者,他在美国战略界心中种下了独立空军的种子。在与美国海军陷入“地盘”之争并面临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后,米切尔于 1926 年初辞去了空军职务。然而,他仍然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可行的军事航空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以独立空军、创新研究和充满活力的航空工业综合体为中心。米切尔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斗士,他为美国空军的创建提供了自我维持的动力,影响了乔治·C·马歇尔将军等关键决策者。
书评:《白色狙击手》:西蒙·海赫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在珍珠港爆发,但对于芬兰人来说,这场战争有时被称为继续战争,因为他们刚刚在冬季战争中与苏联打完一场僵局。1939 年 11 月 30 日,苏联入侵芬兰,1940 年 3 月 13 日,苏联与未尝败绩的芬兰签署和平协议,芬兰保持独立,但必须放弃 10% 的领土给苏联(以及 30 年租借汉克海军基地)。在这三个半月里,拥有约 340,000 名士兵、10 辆坦克和 114 架战斗机的芬兰军队面对拥有约 100 万人、6,500 辆坦克和 3,800 架飞机的苏联军队。芬兰人死亡 21,396 人,失踪 1,434 人,受伤 43,557 人。
书评:心理射击的秘密
很多文章都大肆宣扬士兵的思想作为武器的重要性。尽管如此,通常的优先事项是获得更多可以“砰”地一声响或需要电池才能确保胜利的东西。完成工作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但乔治·S·巴顿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战争》中引用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的一句话,如下:“在每场战斗中,都会有双方都认为自己被打败的时候,然后继续进攻的人就会获胜。” 那么,除了互相喊口号之外,我们如何训练射击之类的心理方面?这让我们想到了手头的这本书。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为了充分披露,我认识作者很多年了,并为他们之前的作品《风之书》贡献了一个章节。话虽如此,尽管我没有为这本最新著作做出任何贡献,但他们在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做得非常出色。
书评:人工智能时代和我们的人类未来
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学习和处理的结果,但并不总是能看到结果产生的过程,人工智能软件也无法描述它实现目标的方式。革命性的国际象棋动作等人工智能成就的相对微不足道,与其在国防战略或武器系统部署中的实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作者意识到了这些担忧,他们指出:“我们都必须注意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我们不能把它的开发或应用留给任何一个群体,无论是研究人员、公司、政府还是民间社会组织”(77)。我想到两个保留意见:(1)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雇主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包括持反对观点的各方,(2)计划中的应用和用户将不可避免地包括不关心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风险或功能的群体。后者的问题在于,“尽管创建一个复杂的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
书评:反叛乱中的战略武力使用
“考虑到连续性和变化,我们需要一般实用指导”(180)。基于反思行动,反叛乱有几个战略要务:制定概念/方法和政策,将反叛乱分析纳入概念/方法和政策审议,减少叛乱暴力,以及继续为当地行为者提供外部支持(180)。基茨建议反叛乱政策制定者应“避免说他们的政治目标是‘胜利’”(180)。相反,他们应该强调弹性,这包括提高反叛乱抵抗冲击、从挫折中恢复和适应变化的能力(180)。基茨还指出了反叛乱挑战期间第四个要务的重要性——在外部力量撤出后继续支持当地行为者(186)。一旦宣布撤军,如果政策目标没有明确陈述和实现,叛乱部队必须准备好填补权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