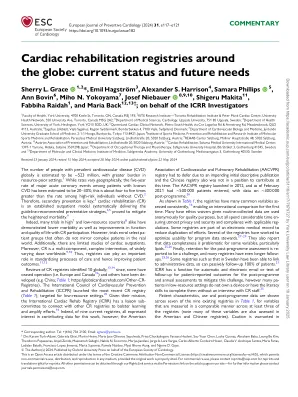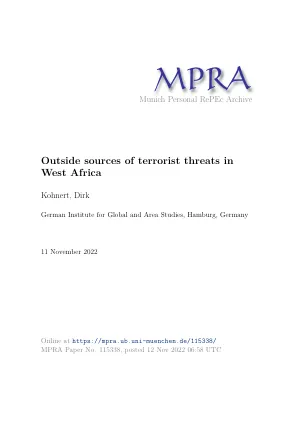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全球心脏康复登记处
1约克大学卫生学院,4700 Keele ST,多伦多,安大略省,加拿大M3J 13; 2风筝研究所 - 托隆托康复研究所和彼得·穆克心脏中心,大学卫生网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大街550号,M5G 2A2; 3乌普萨拉大学心脏病学医学科学系,瑞典751 85乌普萨拉; 4约克大学卫生科学系,赫斯灵顿,约克YO10 5DD,英国; 5昆士兰州心脏临床网络,Metro South Health,通过CNR Loganlea Rd&Armstrong Rd,Meadowbrook,QLD 4113,澳大利亚; 6 SygehusLillebælt,Vejle Sygehus,Syddanmark地区,Beriderbakken 4,7100 Vejle,Sydjylland,丹麦; 7日本,日本东京邦基 - 库(Bunkyo-ku)2-1-1 Hongo的Juntendo University医学院心血管生物学和医学系113-8421,日本; 8运动医学,预防与康复研究所与研究所分子运动医学与康复研究所,帕拉辛斯医科大学萨尔茨堡,林德霍夫斯特拉斯,奥地利5020萨尔茨堡; 9萨尔茨堡康复中心,MüllnerHauptstraße48,5020萨尔茨堡,奥地利; 10奥地利预防与康复协会,林德霍夫斯特拉斯20号,奥地利萨尔茨堡5020; 11心脏康复,西塔玛医科大学国际医学中心,1397-1,山达卡,西塔玛,日本3501298; 12职业治疗和物理治疗系,Sahlgrenska大学医院,Blåstråket3,哥德堡41345,瑞典; 13哥德纳堡大学Sahlgrenska学院医学院分子与临床医学系,Medicinarearegatan 3,哥德堡40530,瑞典1约克大学卫生学院,4700 Keele ST,多伦多,安大略省,加拿大M3J 13; 2风筝研究所 - 托隆托康复研究所和彼得·穆克心脏中心,大学卫生网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大街550号,M5G 2A2; 3乌普萨拉大学心脏病学医学科学系,瑞典751 85乌普萨拉; 4约克大学卫生科学系,赫斯灵顿,约克YO10 5DD,英国; 5昆士兰州心脏临床网络,Metro South Health,通过CNR Loganlea Rd&Armstrong Rd,Meadowbrook,QLD 4113,澳大利亚; 6 SygehusLillebælt,Vejle Sygehus,Syddanmark地区,Beriderbakken 4,7100 Vejle,Sydjylland,丹麦; 7日本,日本东京邦基 - 库(Bunkyo-ku)2-1-1 Hongo的Juntendo University医学院心血管生物学和医学系113-8421,日本; 8运动医学,预防与康复研究所与研究所分子运动医学与康复研究所,帕拉辛斯医科大学萨尔茨堡,林德霍夫斯特拉斯,奥地利5020萨尔茨堡; 9萨尔茨堡康复中心,MüllnerHauptstraße48,5020萨尔茨堡,奥地利; 10奥地利预防与康复协会,林德霍夫斯特拉斯20号,奥地利萨尔茨堡5020; 11心脏康复,西塔玛医科大学国际医学中心,1397-1,山达卡,西塔玛,日本3501298; 12职业治疗和物理治疗系,Sahlgrenska大学医院,Blåstråket3,哥德堡41345,瑞典; 13哥德纳堡大学Sahlgrenska学院医学院分子与临床医学系,Medicinarearegatan 3,哥德堡40530,瑞典
全球心脏康复登记处 - 约克空间
1约克大学卫生学院,4700 Keele ST,多伦多,安大略省,加拿大M3J 13; 2风筝研究所 - 托隆托康复研究所和彼得·穆克心脏中心,大学卫生网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大街550号,M5G 2A2; 3乌普萨拉大学心脏病学医学科学系,瑞典751 85乌普萨拉; 4约克大学卫生科学系,赫斯灵顿,约克YO10 5DD,英国; 5昆士兰州心脏临床网络,Metro South Health,通过CNR Loganlea Rd&Armstrong Rd,Meadowbrook,QLD 4113,澳大利亚; 6 SygehusLillebælt,Vejle Sygehus,Syddanmark地区,Beriderbakken 4,7100 Vejle,Sydjylland,丹麦; 7日本,日本东京邦基 - 库(Bunkyo-ku)2-1-1 Hongo的Juntendo University医学院心血管生物学和医学系113-8421,日本; 8运动医学,预防与康复研究所与研究所分子运动医学与康复研究所,帕拉辛斯医科大学萨尔茨堡,林德霍夫斯特拉斯,奥地利5020萨尔茨堡; 9萨尔茨堡康复中心,MüllnerHauptstraße48,5020萨尔茨堡,奥地利; 10奥地利预防与康复协会,林德霍夫斯特拉斯20号,奥地利萨尔茨堡5020; 11心脏康复,西塔玛医科大学国际医学中心,1397-1,山达卡,西塔玛,日本3501298; 12职业治疗和物理治疗系,Sahlgrenska大学医院,Blåstråket3,哥德堡41345,瑞典; 13哥德纳堡大学Sahlgrenska学院医学院分子与临床医学系,Medicinarearegatan 3,哥德堡40530,瑞典1约克大学卫生学院,4700 Keele ST,多伦多,安大略省,加拿大M3J 13; 2风筝研究所 - 托隆托康复研究所和彼得·穆克心脏中心,大学卫生网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大街550号,M5G 2A2; 3乌普萨拉大学心脏病学医学科学系,瑞典751 85乌普萨拉; 4约克大学卫生科学系,赫斯灵顿,约克YO10 5DD,英国; 5昆士兰州心脏临床网络,Metro South Health,通过CNR Loganlea Rd&Armstrong Rd,Meadowbrook,QLD 4113,澳大利亚; 6 SygehusLillebælt,Vejle Sygehus,Syddanmark地区,Beriderbakken 4,7100 Vejle,Sydjylland,丹麦; 7日本,日本东京邦基 - 库(Bunkyo-ku)2-1-1 Hongo的Juntendo University医学院心血管生物学和医学系113-8421,日本; 8运动医学,预防与康复研究所与研究所分子运动医学与康复研究所,帕拉辛斯医科大学萨尔茨堡,林德霍夫斯特拉斯,奥地利5020萨尔茨堡; 9萨尔茨堡康复中心,MüllnerHauptstraße48,5020萨尔茨堡,奥地利; 10奥地利预防与康复协会,林德霍夫斯特拉斯20号,奥地利萨尔茨堡5020; 11心脏康复,西塔玛医科大学国际医学中心,1397-1,山达卡,西塔玛,日本3501298; 12职业治疗和物理治疗系,Sahlgrenska大学医院,Blåstråket3,哥德堡41345,瑞典; 13哥德纳堡大学Sahlgrenska学院医学院分子与临床医学系,Medicinarearegatan 3,哥德堡40530,瑞典
目录
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的历史 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87 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慷慨资助成立的富兰克林学院。学院是新国家种族最多元化地区的英语和德语社区开拓性合作的产物,由路德宗和归正会领袖在包括四位《独立宣言》签署人、三位未来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两位制宪会议成员和七位革命军军官在内的董事支持下创办。他们的目标是“维护我们现有的共和政体”和“促进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变得受人尊敬、伟大和幸福。” 马歇尔学院以伟大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于 1836 年在德国归正会的赞助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默瑟斯堡成立。它吸引了一批杰出的教师,他们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知识分子运动“莫瑟斯堡神学”的领袖。1853 年,马歇尔学院迁至兰开斯特,与富兰克林学院合并,成立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美国第十五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是第一任校董会主席。从建校一百周年开始,学院除其在古典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优势外,还开设了广受尊敬的科学课程。然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它又增加了商科课程。二战后,学院的转型仍在继续,规模和学术范围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校园设施不断扩大,学院主要改为寄宿制。1969 年,学院成为男女同校。与后来成为归正会一部分的归正会的联系
西非恐怖主义威胁的外部来源
摘要:打击恐怖主义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不仅限于军事选择。它还涉及国家建设、民族主义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潜在冲突的根源早在殖民主义、奴隶贸易、资源掠夺和任意设立边界期间就已奠定。仅靠占领或受影响国家的内部努力无法赢得这场战斗,尤其是当恐怖分子得到部分军队和该国政治精英的秘密支持时。有外部因素通过跨国犯罪和恐怖分子网络的密切合作煽动暴力冲突。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是问题的一部分。此外,许多活动家和战斗人员不仅仅是受到宗教狂热和意识形态狂热的驱使。复仇、生存和冲突团体之间的局部斗争也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治理不善和无政府的空间有利于军阀主义,无论是激进的圣战分子还是非宗教恐怖分子运动,都是由地方主义和非正式网络驱动的。一些政府和安全部门的军事反应退化为不充分的国家反恐,完全不顾当地居民。这导致这些国家的法治和人权受到挑战。虽然西非经共体政府之间的跨国军事反叛乱有所改善,但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前殖民统治者法国和英国的既得利益仍然阻碍着它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恐怖分子还有效地利用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来制造恐惧并传播他们的暴力意识形态。在可预见的未来,西非的犯罪与恐怖之间的互动将继续。考虑到 COVID-19 大流行的破坏性影响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导致谷物进口失败而造成的饥荒,这种互动甚至可能会增加。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包括民众对国家行政部门的信任度不断下降以及村民愿意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要考虑到反恐、法治和人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关键词:恐怖主义、反叛乱、跨国犯罪、失败或即将失败的国家、独裁、治理、专制、权力下放、军阀、可持续发展、网络恐怖主义、社会运动、社交媒体、后殖民主义、人权、伊斯兰国、西非、撒哈拉以南非洲、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加纳、多哥、贝宁、非洲研究 JEL 代码:D31、D72、D74、E26、F22、F35、F51、F52、F54、H26、H56、K14、N47、N97、O17、Z12、Z13
项目标题:生物学样本中新的第二次谐波生成方式,以分离胶原蛋白和肌球蛋白
肌球蛋白移动真核生物的肌肉,是一种微小的分子运动[1]。它通过消耗三磷酸腺苷(ATP)来产生力并进行机械工作。作为线性电动机,它可以通过活细胞内的细胞骨架的轨道样肌动蛋白丝或微管进行运动。以这种方式,亚细胞结构,以及较大的单位(例如细胞或生物)可以以定向方式移动[1,2]。使用基因工程方法,已经有可能产生向后移动的肌球蛋白纳米运动[3]。X射线结构分析和动力学研究等方法进一步阐明了具有技术兴趣的运动蛋白的有序纳米结构的自我组织。对于分子医学,了解分子线性运动和组织中稳定结构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很重要。骨骼肌由伸长的纤维细胞和肌纤维沿整个长度平行排列[1]组成。肌原纤维包含纵向肉瘤,其肌动蛋白肌膜的高阶和肌球蛋白蛋白具有收缩。骨骼肌的众所周知的横向条纹是由于肌纤维在肌肉纤维中的平行排列而产生的(图1)。几种肌肉纤维沿相同方向捆绑在一起。这些由细胞外基质的结构蛋白(尤其是胶原蛋白纤维)组织。从胶原蛋白家族的大而异构的群体中,发现大部分是纤维状胶原蛋白。但是这种变化可能具有很大的潜力。由于非中心对称结构,胶原蛋白和肌球蛋白的特异性显微成像是可能的[4,5,6,7,8]。使用聚焦激光辐射的超短脉冲会导致瞬态高功率密度和二阶频率加倍(第二次谐波产生,SHG)[7,8]。通过在近红外范围内使用激发波长,第二个谐波渗透到组织中,肌肉组织可以在三个维度中无损地映射(图2)。SHG极化法可用于区分肌球蛋白和胶原蛋白,并进一步胶原蛋白纤维的方向[7,8,9]。可以通过对向后信号进行评估来获得进一步的对比信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调节SHG生成波长以区分肌球蛋白和胶原蛋白纤维[8,9]。但是,一些矛盾的结果要求通过评估光谱信息进行多模式研究。到目前为止,在生物样品中的第二次谐波中,尚未证明完全kleinman对称性的假设和SHG效率的单调降低。相反,最近的研究表明了一种复杂的行为,更明显地使用向后信号而不是前向信号[8,9]。
室温下产生稳定的量子比特研究人员观察到分子系统中具有四个电子自旋的五重态的量子相干性
日本福冈——在《Science Advances》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九州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柳井伸宏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与九州大学宫田清副教授和神户大学小堀康弘教授合作,报告称他们已经在室温下实现了量子相干性:量子系统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明确状态而不受周围干扰影响的能力。这一突破是通过将发色团(一种吸收光并发射颜色的染料分子)嵌入金属有机骨架(MOF,一种由金属离子和有机配体组成的纳米多孔晶体材料)中实现的。他们的发现标志着量子计算和传感技术的重大进步。虽然量子计算被定位为计算技术的下一个重大进步,但量子传感是一种利用量子比特(经典计算中比特的量子类似物,可以存在于 0 和 1 的叠加中)量子力学特性的传感技术。可以采用各种系统来实现量子比特,其中一种方法是利用电子的固有自旋(与粒子磁矩相关的量子特性)。电子有两种自旋状态: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基于自旋的量子比特可以存在于这些状态的组合中,并且可以“纠缠”,从而允许从另一个量子比特推断出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通过利用量子纠缠态对环境噪声极其敏感的特性,量子传感技术有望实现比传统技术更高的分辨率和灵敏度的传感。然而,到目前为止,将四个电子纠缠并使其对外部分子作出反应,即使用纳米多孔 MOF 实现量子传感一直具有挑战性。值得注意的是,发色团可用于在室温下通过称为单重态裂变的过程激发具有所需电子自旋的电子。然而,在室温下会导致存储在量子比特中的量子信息失去量子叠加和纠缠。因此,通常只有在液氮水平温度下才能实现量子相干性。为了抑制分子运动并实现室温量子相干性,研究人员在 UiO 型 MOF 中引入了基于并五苯(由五个线性稠合苯环组成的多环芳烃)的发色团。“这项研究中的 MOF 是一种独特的系统,可以密集地积累发色团。此外,晶体内的纳米孔使发色团能够旋转,但角度非常受限,”Yanai 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