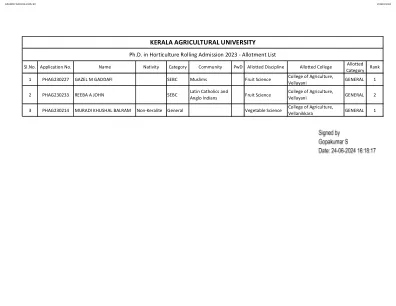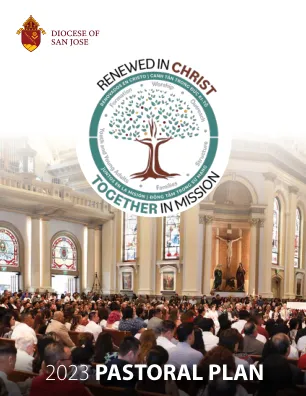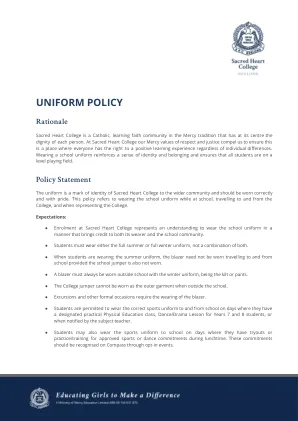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英格兰和威尔士对天主教儿童性虐待的天主教徒的态度
本报告基于由Marcus Pound博士领导的研究,作为达勒姆大学边界破坏项目的一部分。边界破坏团队由马库斯·庞德(Marcus Pound)博士,凯瑟琳·塞克斯顿(Catherine Sexton)博士和帕特·琼斯(Pat Jones)博士组成,并与保罗·D·默里(Paul D.Giuseppe Bollota博士在第一年是研究团队的一员,Adrian Brooks博士加入了该团队,进行了一段时间,进行了文学审查,以协助神学反思。Gregory A. Ryan博士与团队合作完成了本报告的分析和撰写,并收到了Mathew Guest教授的宝贵建议。 为了支持这项研究,由格拉斯哥大学朱莉·克拉格(Julie Clague)博士主持了指导委员会。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相关者团体将一群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或经验和/或代表机构(例如宗教会议)的人聚集在一起,该机构召集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工作的宗教众群体领导人。 1两组包括虐待幸存者的成员。Gregory A. Ryan博士与团队合作完成了本报告的分析和撰写,并收到了Mathew Guest教授的宝贵建议。为了支持这项研究,由格拉斯哥大学朱莉·克拉格(Julie Clague)博士主持了指导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利益相关者团体将一群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或经验和/或代表机构(例如宗教会议)的人聚集在一起,该机构召集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工作的宗教众群体领导人。1两组包括虐待幸存者的成员。
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安大略省家庭医生 COVID-19 实践社区
好问题,CBC 的文章很棒。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catholic-bishops-astra- zeneca-vaccine-1.5945928 “主教们拒绝向加拿大天主教徒提供关于选择阿斯利康疫苗替代品的建议” “……所有经相关卫生当局医学批准的 COVID-19 疫苗都可以合法接种。澄清中写道:“天主教徒受邀接种疫苗,这既符合他们的良心要求,也通过促进他人的健康和安全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心脏心脏
大二学生莎拉·凯尔顿(Sarah Kelton)说,参加会议的听力会议“使我感到与天主教社区更加紧密联系。作为学生和教区的天主教徒,我都会更加赞赏。”少年莱拉·尼托(Laila Nieto)同意。“这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声音,他们珍视我们的意见。”初中Lyle Moise最初感到紧张,人们不会分享他们的意见,但这是一个非常包容和舒适的环境,可以在不同的思想和想法上进行合作。我对我们的班级同意并提出的新想法和策略的数量感到惊讶。”大一新生吉利安·林(Jillian Lim)发现:“主教伯恩斯(Bishop Burns)认为我们的思想对教会的未来很重要,”她的同学伊丽莎白·韦恩(Elizabeth Wayne)同意:“即使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也必须参加。他们仍然真的想知道我的感受。”
85 关于信徒洗礼、基督教的个人反思......
为什么要信徒洗礼? 在我和女婿因洗礼问题发生严重争执后不到三个月,我收到了写一篇关于洗礼的个人感想的邀请。我的女婿是天主教徒。争执的原因是他想让女儿埃斯特尔在天主教堂洗礼。她六岁了。我女婿所在的天主教教区宣布,教堂将在当月提供洗礼。教堂通常每年提供几次洗礼仪式,并且总是在星期五举行。碰巧的是,教堂当月提供洗礼仪式的星期五是我女婿的生日。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要让埃斯特尔在那天受洗。我坚决拒绝了他的主意。这主要不是因为我的孙女将接受天主教徒的洗礼,而是因为作为一名门诺派牧师和教师,儿童洗礼的概念和做法违背了我的信仰。
2023 年牧区计划
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天主教会都必须了解时代特征,然后创造性地、积极地应对。今天的教会与 100 年前、40 年前甚至 20 年前的教会已经大不相同,但教会仍然在同样的结构和传福音模式中运作。虽然我们天主教徒珍视我们的传统,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天主教徒的人口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人口中信奉特定宗教和遵守宗教习俗的比例持续下降。婴儿潮一代的宗教信仰最高,随后每一代都在下降。此外,年轻人推迟结婚,结婚后生育的孩子也更少。我们当地教会的结构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或可持续。这些宏观趋势在圣何塞教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