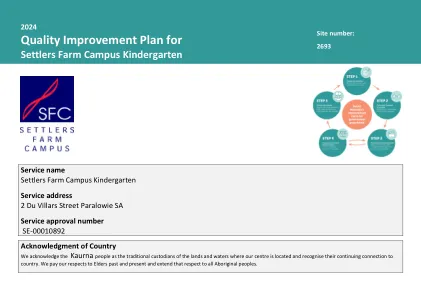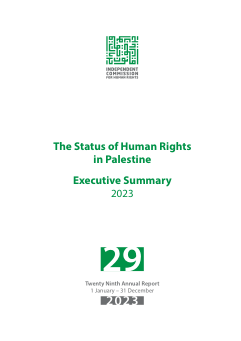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定居者农场校园幼儿园
定居者农场是一个成熟的社区,位于帕拉洛维(Paralowie)阿德莱德(Adelaide)以北19公里。有一个靠近幼儿园的购物/社区中心。有各种文化背景的广泛代表(将其标识为原住民/托雷斯海峡岛民和英语的儿童作为附加语言/方言(EALD)。 div>大约90%的幼儿园儿童出口参加了定居者农场校园。家长志愿者积极通过理事会进行决策。在2023年,定居者农场校园幼儿园由教育部分配为“类别1”站点,其学龄前董事乐队A-2。幼儿园的上限为70个合格的入学率,每周15个小时参加,每周一次。人员配备包括1.0董事,1.4名教师,1.5个幼儿工人(教师助理),通用访问人员配备,学龄前支持人员和双语助手。儿童连续两天(周三早上有另一种情况)参加,以通过学习为学习提供更多的一致性。儿童参加各种文化庆典,包括农历新年,Shrove Tuesday,Harve Day,高棉新年,复活节,Anzac Day,Anzac Day,和解周,排灯节,万圣节,Naidoc Week,母亲节,父亲节,庆祝儿童和员工的孩子和员工的生日,纪念日和圣诞节。每天,儿童都会在一个开放的幼儿园里与所有教育者一起教授。Throughout the year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a variety of special events and experiences including incursions with 'Mobile junk and nature playground', Kindergarten photos, attending co-located campus assemblies visits to the reception classes and events, caring for the vegetable garden, Discothon, National Simultaneous story time, transition visits to Settlers Farm Campus, Recycling Show, art show, Summer Celebration, Magician show, and the End of Year celebration.小组时间每天一次实施一次(识字 - 口语语言,语音意识和儿童保护课程)以及两个大型小组时间 - 早上向教育工作者致意,承认我们的国家,讨论课程焦点领域,并在一天结束时放松,讨论,讨论,故事和故事和歌曲,并说Goodbye。
生活在死亡中: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新反乌托邦现实
摘要:巴勒斯坦/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当代案例引发了有关巴勒斯坦人经历的不同类型的暴力 - 身体,领土和精神的辩论。已有15多年的历史,加沙地带一直受到封锁,并与其他巴勒斯坦领土和世界隔绝。这一现实导致了对加沙作为实验室的解释,在该实验室中,对遥控武器和人类生存的局限性进行了测试。这使Gazans使用“缓慢死亡”或“活死”等表达来描述他们的生活。本文分析了科幻小说中的六个短篇小说《巴勒斯坦+100:Nakba之后的一个世纪的故事》(2019年),以调查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如何影响巴勒斯坦的小说对加沙的虚构pro duction。我们认为,通过持续驱逐,以色列的毁灭和暗杀的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人的持久性使生活成为日常反乌托邦。此外,它使巴勒斯坦人对他们的未来不再是乌托邦式解放的梦想的想象力,而是反乌托邦和周期性的监禁和死亡噩梦。在巴勒斯坦艺术作品中观察到的那样,在噩梦中永恒地生活在殖民地反凝结策略中。在这种凄凉的现实中,甘兰人还有“死亡”的选择。
14.773 制度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讲座 1:介绍和概述
A 高死亡率阻碍定居。B 欧洲定居者抵制殖民者为榨取性制度所设计的方案,使得包容性制度的出现更有可能。C 制度通过上述渠道得以持续存在。D 利用这一变异源估计当前制度对发展的因果影响,但排除潜在定居者死亡率对当前表现没有直接影响的限制(“IV 策略”)。
地图作为殖民力量和替代制图的修辞工具:美洲制图
地图是最强大的视觉文物之一,讲述了有关我们的地理位置的故事,并告知我们如何体验物理环境的空间(Propen,“视觉交流”)。1因此,地图的讲故事力量历史上被用于建造公共和世界遗产记忆(€ozyes≥Nar和Beltran)。作为视觉量工部,已使用地图用于推进和实现定居者殖民和帝国权力关系和暴力(Hayes; na'putipi)。此外,地图还用于构建替代故事,以揭示由定居者殖民地和帝国制图项目和实践所造成的认知暴力,提供了设想反殖民和分离的愿景的方法,这些愿景是社会空间和环境正义和环境正义和抵抗的愿景(eichbergerger; eichberger; eichberger; greene and kus and kus; uptuti; uttuti; uttuti; uttuti;
斯图尔特湖县公园自然群落植被...
在过去的 200 年里,丹县的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因人类活动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图 1)。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欧洲定居者来到该地区,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重大变化。曾经席卷这片土地并塑造植被的野火被定居者扑灭,或被农田和道路阻止。农业和牲畜放牧破坏了土壤并取代了本地物种。此外,非本地入侵物种的引入和传播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重大损失,并为恢复造成了障碍。如今,气候变化等全球力量进一步威胁着这些土地和水域以及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物种的健康。通过生态修复的科学和实践,一门起源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科,丹县公园试图恢复因人为力量而严重改变或消失的自然群落。
支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建造符合当地文化且节能的新建筑
本报告由社区和区域规划学院 (SCARP) 原住民社区规划专业的研究生 Jenna Hildebrand 撰写。Jenna 是一名白人定居者,她生活、学习和工作在 Skwxwú7mesh (Squamish)、xʷməθkʷəy̓ əm (Musqueam) 和 səl ̓ ílwətaʔɬ (Tsleil-Waututh) 民族的传统、祖传和未割让的领土上。作为一名白人定居者,她正在研究影响原住民的主题,她认识到承认自己在这项工作中的地位的重要性。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Jenna 一直享有住在安全舒适的房子里的特权;这些房子有家的感觉。她认识到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原住民并没有同样的经历。出于对改善原住民社区住房和基础设施的真诚渴望和热情,她开展了这项研究。除此之外,詹娜的工作还基于积极支持原住民自治和自决的承诺。
2021 年 5 月 11 日通过 2024 年 2 月 13 日修订
早在鹅溪被欧洲移民定居之前,该地区就居住着几个美洲原住民部落,包括埃蒂万、韦斯特科、塞维和亚马西。17 世纪 70 年代初,英国定居者(大多是巴巴多斯大种植园主的儿子和前契约奴)在被奴役的非洲人的陪同下首次遇到了居住在丹尼尔岛的埃蒂万。定居者在卡罗莱纳领主的统治下在鹅溪沿岸建立了种植园,当地部落称他们为“鹅溪人”。伯克利县最初于 1682 年命名,一度包括圣约翰伯克利、圣詹姆斯鹅溪、圣詹姆斯桑蒂、圣斯蒂芬和圣托马斯和圣丹尼斯教区。1769 年,该地区成为查尔斯顿区的一部分,直到 1882 年才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