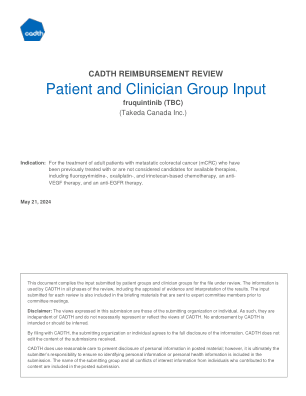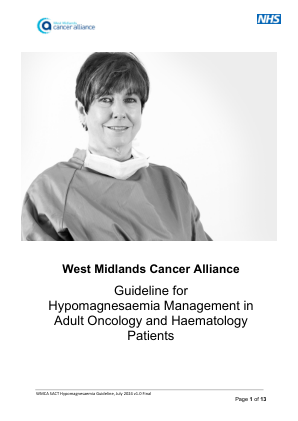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患者和临床医生组输入
患者 4 于 2014 年被诊断为 III 期 CRC。他接受了 6 个月的 CAPOX 治疗,并且大约 1 年没有进食。CAPOX 引起了严重的恶心和手足综合征。在常规随访中,发现腹膜复发,患者被诊断为 IV 期疾病。他接受了 CRS- HIPEC 和手术以切除乙状结肠复发,导致临时造口术。2017 年初,患者接受了 3 个月的二线化疗 - FOLFIRI。他几个月没有进食,直到他注意到右腿疼痛。扫描显示结肠、肝脏、肺、骨骼和腹膜出现明显复发。他无法行走和参与许多日常任务。患者参加了临床试验并接受了派姆单抗和比尼替尼治疗,但由于对后者的严重反应,不得不退出试验。 2018 年末,患者接受了 Lonsurf 治疗,但由于严重的不良反应,不得不停止服用该药物。患者最终前往美国进行第二意见咨询,并接受了 ipilimumab-nivolumab 的标签外治疗。患者经历了剧烈疼痛,停用 ipilimumab,并被开具强效阿片类药物。最终,疼痛开始好转,在下一次扫描时,医疗团队表示肿瘤到处都在缩小。最终,他不得不停止服用 nivolumab,因为他出现了肾上腺危象。2021 年,患者接受了全结肠切除术,并进行了永久性造口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扫描显示他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患者目前患有慢性神经病变、永久性造口术以及阿片类药物使用的长期副作用,包括睡眠障碍。此外,为了获得额外的治疗选择,患者自掏腰包花费了 20 万至 25 万美元,这凸显了一旦加拿大的标准治疗方案用尽,获得额外的治疗选择的成本极高。
病例报告:晚期十二指肠腺癌化疗联合靶向治疗及放疗后完全缓解一例
十二指肠腺癌(DA)是极为罕见且侵袭性极强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由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漏诊,治疗方面也缺乏特异性的共识和推荐,因此常将其合并胃癌、结直肠癌。现报告1例晚期DA患者,接受放化疗联合靶向治疗后获完全缓解(CR)。患者2020年10月根治术后病理诊断为DA,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按时接受辅助化疗,术后6个月患者发现多发淋巴结肝脏及腹部转移。考虑病情进展,给予XEL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化疗1周期,1周期治疗后肿瘤标志物持续升高;癌胚抗原(CEA)5.03ng/ml(0~5ng/ml),糖类抗原19-9(CA19-9)747.30U/ml(0~37U/ml)。患者还出现了无法耐受的卡培他滨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即手足综合征。针对以上原因,患者在第2周期将卡培他滨换为S-1,化疗方案变为SOX(奥沙利铂+S-1);在SOX方案中同时加入贝伐单抗注射液,继续以SOX加贝伐单抗的方案定期治疗7个周期。整个治疗期间肝转移灶呈持续缩小趋势;肿瘤标志物亦呈下降趋势。最终患者在第7个周期获得完全缓解(CR)。完成化疗后,对患者腹腔内存在的耐药转移淋巴结进行放疗,共计10次。但患者在放疗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骨髓抑制和阻塞性黄疸,最终未能完成放疗计划。目前患者继续使用贝伐单抗和S-1维持治疗,复查未见复发或转移。本例晚期DA,
原创研究 D-TACE-HAIC、仑伐替尼和 PD-1 抑制剂联合治疗对 2019 年美国癌症协会 (ASCO) 癌症研究项目 (CSCO) 的 10 项研究均获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D-TACE-HAIC+仑伐替尼+PD-1抑制剂联合治疗与TACE+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HCC患者的疗效。患者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18年3月至2022年3月间接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的无法切除的HCC患者。共60例患者接受药物洗脱珠-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D-TACE-HAIC)联合仑伐替尼和PD-1抑制剂治疗(A组),21例患者接受TACE和索拉非尼联合治疗(B组)。结果:在本研究队列中,A组的手术中转率明显高于B组(33.3% vs 9.5%)。按照修订的实体肿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标准,A组客观缓解率显著高于B组(86.6% vs 33.4%)。A组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也显著高于B组,包括高血压、腹痛、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低蛋白血症,但A组手足综合征的发生率显著低于B组(13.3% vs 42.8%)。A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PFS和OS)分别为13.2个月和28.8个月,均显著高于B组(分别为5.7个月和10.8个月)。Cox多变量分析显示,D-TACE-HAIC+仑伐替尼+PD-1抑制剂联合治疗与患者PFS和OS独立相关。结论:总之,对于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D-TACE-HAIC + lenvatinib + PD-1 抑制剂治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优于 TACE + 索拉非尼治疗,同时提高了总的转化有效率,增加了手术转换率,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并带来了长期生存益处。关键词: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药物洗脱珠-经动脉化疗栓塞-肝动脉灌注化疗,临床疗效,预后
成人低镁血症管理指南...
1.0 目的/目标 制定本文件的原因是需要为西米德兰兹郡的癌症患者提供无缝服务。本指南并不凌驾于卫生专业人员根据个别患者的情况与患者和/或护理人员协商后做出适当决定的个人责任之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准备好对任何偏离本指南的行为进行说明。 2.0 受众 本文件适用于参与化疗和其他全身抗癌药物途径任何方面的所有从业者。 3.0 简介 低镁血症是一种常见的医学问题,是导致癌症患者发病和死亡的原因(Workeneh 等人,2020 年)。低镁血症的原因可根据病理生理机制分为:摄入量减少、跨细胞转移、胃肠道损失和肾脏损失。癌症患者有机会性感染的风险,经常出现心血管并发症,并且经常接受导致或加剧低镁血症的药物。此外,癌症特异性疗法也是导致低镁血症的原因,包括铂类化疗、抗 EGF 受体 mAb、人类 EGF 受体 2 靶向抑制剂 (HER2) 和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镁在细胞的许多功能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包括能量转移、储存和使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谢;维持正常细胞膜功能;以及调节甲状旁腺激素 (PTH) 的分泌。因此,与低镁血症相关的症状范围很广;患者可能无症状并表现出非特异性症状(如厌食、恶心和疲劳)和严重症状(如手足搐溺症、癫痫发作和致命心律失常)。从系统上讲,镁会降低血压并改变外周血管阻力。镁水平异常会导致几乎所有器官系统紊乱,并可能导致致命的并发症(例如室性心律失常、冠状动脉痉挛、猝死)(Fuller 2009)。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程度的低镁血症都可能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反应和后果(Workeneh 等人,2020 年)。普通人群中低镁血症的患病率为 2.5-15%(Schimatscheck 和 Rempis 2001)。癌症患者的发病率可能更高。据了解,某些化疗药物可能会导致低镁血症。然而,它也会发生在胃肠道疾病中,包括腹泻、营养不良和饮食摄入减少,以及使用利尿剂和其他药物治疗(Saif 2008)。传统化疗药物会导致低镁血症,并且这种症状在停止癌症治疗后可能会持续数月至数年。
针刺对缺血性中风偏瘫患者大脑和小脑的双侧影响:一项随机临床和神经影像学试验
摘要 背景 针刺涉及肢体区域可能在临床上对中风康复有效,但可视化和解释证据有限。我们的目的是评估针刺对缺血性中风 (IS) 偏瘫患者的具体效果,并研究其治疗驱动的功能连接改变。方法 IS 患者随机分配(2:1)接受 10 次手足 12 针针刺 (HA,n=30) 或非穴位 (NA) 针刺 (n=16),招募性别匹配和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者 (HCs,n=34)。临床结果是改进的 Fugl-Meyer 评估评分,包括上肢和下肢 (ΔFM、ΔFM-UE、ΔFM-LE)。神经影像学结果是体素镜像同伦连接 (VMHC)。静态和动态功能连接 (sFC、DFC) 分析用于研究神经可塑性重组。结果 46 名 IS(平均(SD)年龄,59.37(11.36)岁)和 34 名 HC(平均(SD)年龄,52.88(9.69)岁)被纳入临床和神经影像学的符合方案分析。在临床方面,HA 组的 Δ FM 评分为 5.00,NA 组的 Δ FM 评分为 2.50,Δ FM 与 Δ VMHC 之间存在双重相关性(角度:r=0.696,p=0.000;小脑:r=−0.716,p=0.000),符合线性回归模型(R 2 =0.828)。神经影像学检查发现,IS患者双侧中央后回及小脑VMHC降低(高斯随机场,GRF校正,体素p<0.001,簇p<0.05),符合逻辑回归模型(AUC=0.8413,准确率=0.7500)。针刺后,双侧额上回眶部VMHC增高,伴有脑-小脑改变,患侧额上回眶部与对侧眶额皮质及小脑之间的sFC增高(GRF校正,体素p<0.001,簇p<0.05)。双侧后扣带回 (PPC) 局部 VMHC 变异系数降低 (GRF 校正,体素 p<0.001,簇 p<0.05),整体整合状态转变为分离状态 (p<0.05)。没有针灸相关的不良事件。结论随机临床和神经影像学试验表明,针灸可以通过双侧静态和动态重组促进 IS 偏瘫患者的运动恢复和改善脑小脑 VM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