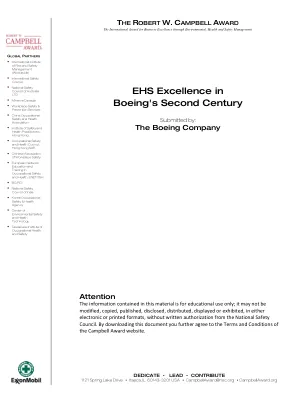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结交朋友:新生儿免疫系统对共生体的积极选择和病原体的拒绝
北极陆地生态系统目前存储在地球高纬度地区的最大碳。在过去30年中,这些区域的温度水平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为每十年0.6℃(Cohen等,2014; Schuur等,2015)。这是一种强大的现象,称为北极扩增(Fengmin等,2019)。土壤微生物在将碳化合物转化为有机或无机化合物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变暖,它们的代谢率提高。当微生物分解有机碳时,它们会释放温室气体(GHG),例如二氧化碳(CO 2),一氧化二氮(N 2 O)和甲烷(CH 4),导致全球气候变化(Mehmood等人,2020年,2020年; Marushchak等人,2021年)。在过去的800,000年中,大气二氧化碳,N2O和CH4的水平显着增加。CO 2的目前水平为390.5份百万分之390.5份,n 2 O的零件为390.5份(ppb),CH 4分别为1,803.2 ppb,这些水平分别为40、20、20和150%,比工业时代之前(Tian et et an e an and an an and an and and an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ch 4,仅次于CO 2之后的第二大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占自工业前时代以来变暖剂的人为辐射强迫的20%。此外,CH 4的温室作用是100年内CO 2的28倍(Tian等,2016; Ganesan等,2019; Hui等,2020)。在2000年至2017年之间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和大气反转估计,CH 4排放量为15至50 tg/yr(Saunois等,2016,2020)。在2000年至2017年之间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和大气反转估计,CH 4排放量为15至50 tg/yr(Saunois等,2016,2020)。由于北极扩增,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北极土壤变暖和CH 4排放。然而,尚未发现变暖对CH 4释放的影响,从而导致气候变化。微生物代谢过程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和反应者(Singh等,2010)。根据研究发现,不同的土壤微生物通过与微生物组成相关的不同代谢途径产生温室气体,从而提高了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理解。例如,大多数土壤微生物通过分解和异养呼吸对CO 2排放产生了巨大贡献(Watts等,2021)。类似于CO 2排放,生物CH 4的排放受土壤微生物甲烷生成和CH 4氧化的控制,来自土壤,湖泊和其他陆地陆地,尤其是北极土壤(Nazaries等,2013; Tveit et al。微生物甲烷生成是一组厌氧甲烷古细菌进行的过程(Song等,2021)。虽然其他微生物可以分解CH 4,从而减少CH 4向大气中的释放,但微生物甲烷发生对全球CH 4排放造成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了解其对变暖时间的反应至关重要,这对于预测有效的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反馈(Lee等人,2012年; Chen等,2020年)。此外,预计在按年来衡量的长期变暖的情况下,微生物组成将发生变化(Deslippe等,2012; Pold等,2021; Zosso等,2021; Rijkers等,2022; Zhou等,2023)。同时,生物CH 4排放也是由于长期微生物发酵而变暖引起的(Altshuler等,2019; Hui等,2020; Zhang等,2021)。但是,气候变化是一个过程
建模气候变化对流量的影响...
干旱是世界各地自然灾难的主要原因(Bekele等人2019)。气候变化对几个因素有重大影响,包括水文周期,生物多样性,领土生态学,水资源,环境,农业和粮食安全以及人类健康(Gupta 2015)。降雨量是主要因素之一,它对农业,能源平衡,水力发电,工业和粮食安全的水可用性的时间和空间模式产生了影响(Ayehu等人2018)。科学证据现在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地球大气的平均温度将继续升高。虽然预计温度会始终如一地升高,但根据各种气候模型和排放场景,降水表现出可变的结果(IPCC 2014; Tessema等。2021)。中纬度和亚热带干燥区域有望在RCP8.5场景下降水下降,而高纬度,赤道pacifife,赤道和湿区的降水有望增加(Sesana等人。2019)。例如,IPCC(2021)指出,除非CO 2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显着减少,否则在21世纪将超过1.5和2°C的变暖。21世纪非洲的预期温度高于平均全球温度(IPCC 2013)。世界不同等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Thornton等人2008; Kotir 2011)。 2017)。2008; Kotir 2011)。2017)。非洲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大陆(Collier等人2008);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脆弱的地区,因为使用雨水农业种植了所有农作物中的96%,这可能会加剧问题(Serdeczny等人。 物理和经济缺乏的缺乏对非洲大角(GHA)具有复杂的影响,经常导致严重的水和粮食短缺(Nicholson 2014; Awange等人 2016)。 该地区的未来水稀缺问题可能会因该地区的迅速扩大和高度不可预测的气候而加剧(Hirpa等人。 2019)。 在东非,来自各种GCM场景的降雨揭示了不确定的幅度和趋势(Getahun等人。 2020)。 例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尼罗河流域的流流量有望减少(Haile等人 2017),还有其他研究发现(Worqlul等人 2018)表明,尼罗河流域的流流量估计在未来几十年中会增加。 Haile等人报道。 (2017)有力的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的气候变化在过去50年中发生了变化。 在2007年气候变化国家适应计划(NAPA)下,前埃塞俄比亚国家气象局(NMA)确定国家平均年度年度温度在1960年至2006年之间。。。 这一数字表明,在过去的46年中,每十年增加0.28°C。 根据这项研究的发现,在主要潮湿季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增长最为明显时。2008);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脆弱的地区,因为使用雨水农业种植了所有农作物中的96%,这可能会加剧问题(Serdeczny等人。物理和经济缺乏的缺乏对非洲大角(GHA)具有复杂的影响,经常导致严重的水和粮食短缺(Nicholson 2014; Awange等人2016)。该地区的未来水稀缺问题可能会因该地区的迅速扩大和高度不可预测的气候而加剧(Hirpa等人。2019)。在东非,来自各种GCM场景的降雨揭示了不确定的幅度和趋势(Getahun等人。2020)。例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尼罗河流域的流流量有望减少(Haile等人2017),还有其他研究发现(Worqlul等人2018)表明,尼罗河流域的流流量估计在未来几十年中会增加。Haile等人报道。 (2017)有力的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的气候变化在过去50年中发生了变化。 在2007年气候变化国家适应计划(NAPA)下,前埃塞俄比亚国家气象局(NMA)确定国家平均年度年度温度在1960年至2006年之间。。Haile等人报道。(2017)有力的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的气候变化在过去50年中发生了变化。在2007年气候变化国家适应计划(NAPA)下,前埃塞俄比亚国家气象局(NMA)确定国家平均年度年度温度在1960年至2006年之间。这一数字表明,在过去的46年中,每十年增加0.28°C。根据这项研究的发现,在主要潮湿季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增长最为明显时。粗略的全球气候模型(GCM)决议无法捕获小规模的降雨模式,GCM和RCM降雨预测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使用东非的测量流流缺乏模型验证,所有的水都具有水力影响研究(Otieno and Anyah 2013; Shiferaw eyh and Anyah and Anyah and any Anyah and anyah and anyah and y. shiferaw et al.2018; Endris等。2019)。一般气候模型(GCM)(CMIP; Chen等人。2022)。广泛应用缩小的GCM由于对潜在的未来气候场景的准确和信任而获得了受欢迎程度(Bhatta等人。2019; Bermúdez等。2020; Touseef等。2020; Ji等。2021)。不同气候模型的偏见和内部变异性可能会产生对未来Climeate的完全不同的投影。结果,为了更好地表征结构不确定性并改善气候预测,首选气候模型的集合而不是单个模型(Gaur等人。2021)。在埃塞俄比亚的12河盆地中,Awash River盆地(ARB)是最脆弱和广泛的剥削(Tadese等人2019)。增加人口,定居点,加强农业实践,高地侵蚀和污染物都导致了ARB淡水供应量的下降(Bekele等人2019)。由于多种原因,选择了Kessem流域来研究气候变化对流流的影响。Bekele等。首先,凯塞姆河是奥瓦斯河的一条小支流,为下游的用水使用者提供了更大的流动。第二,在凯西姆流域的下游地区,计划每年有一个25,000公顷的政府拥有的灌溉项目,每年生产500,000吨糖(Hailu 2020)。第三,流域是许多人的家园,他们的生计受到潜在的雨季和气候变化下降的负面影响(CSA 2011)。使用代表性浓度途径(RCP)在ARB的不同子囊中研究了气候变化(例如2019; Daba&You 2020; Getahun等。2020)。这些研究的预测表明,气候变化对ARB的流流动变化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气候变化方案随着时间而变化。 目前,共享的社会经济道路(SSP)情景是根据全球发展开发的,导致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同挑战(O'Neill等人。 2017)。表明,气候变化对ARB的流流动变化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气候变化方案随着时间而变化。目前,共享的社会经济道路(SSP)情景是根据全球发展开发的,导致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同挑战(O'Neill等人。2017)。
波音第二个世纪的 EHS 卓越成就 - 坎贝尔奖
执行摘要 航空业将人们、国家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每天,全球有超过 900 万名乘客登上商用飞机。这些飞机中约有一半由波音公司制造。作为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波音公司致力于设计和制造历史上最安全的长途运输方式。每 1.5 秒就有一架波音 737 飞机起飞或降落,即可感受这一成就的规模。任何时刻,空中平均有 2,800 多架 737 飞机在飞行。737 已飞行超过 1,220 亿英里,相当于绕地球 500 万圈。吉尼斯世界纪录证实,737 是有史以来产量最多的商用喷气式飞机。2017 年是航空业有史以来最安全的一年。全球没有发生过一架客机坠毁事故。波音致力于让我们的飞机在制造和飞行过程中都同样安全。 20 世纪 60 年代,航空旅行的普及度增长了 100 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担心航班数量增加会导致事故增多。1 这似乎是一种逻辑关联,但事实上,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每十年致命事故率都在下降。这是怎么回事?通过研究航空安全从帆布到复合材料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航空安全的几个转折点。这些转折点通常以悲剧为标志,随后是重大的安全创新。航空和飞机制造商团结起来,挑战航班增加与风险增加之间的逻辑关联,并立志实现一个看似不合理的目标:零风险。因此,是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改变了航空安全。五年前,在我们的工厂接连发生三起悲剧事件后,波音公司着手重新发明生产安全,就像我们重新发明产品安全一样。我们回顾了过去的工作场所安全数据,将产品交付率与 2000 年以来的可记录伤害率叠加。我们发现生产水平和伤害状况之间存在关联。产量增加,事故也增加。这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关联。但在 2013 年,波音领导层在工作场所安全问题上表明了立场,挑战了这种合理的关联,并敢于将伤害事故率降至零。我们再次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来改变安全状况。我们研究了包括 USG、雪佛龙、陶氏、杜邦、雷神、杜克能源和 UTC 在内的行业领导者的安全计划。接下来,我们进行了更高层次的自我审视,挑战自己重新评估一切,甚至是我们珍视的关于我们做对了什么的想法。我们发现,在我们一百年的增长和多元化历史中,我们的工作场所安全政策和流程日益专业化,我们的组织也本地化了。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我们发现,好是最佳的敌人。我们对改进的持续关注使我们无法达到超越改进的目标,即零伤害。显然,要重塑工作场所安全,我们必须重塑自我。我们与一家咨询公司合作,转变我们的安全文化,并对我们进行新的安全范式培训:所有伤害都是可以预防的。超过 93,000 名波音员工参加了零事故零伤害 (IIF) 2 活动,其中包括文化评估、承诺研讨会、安全文化入职培训、组建零伤害思维领导团队和个人辅导。这一经历使我们公司对安全的看法发生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领导和员工都表示,培训后,他们再也不能让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