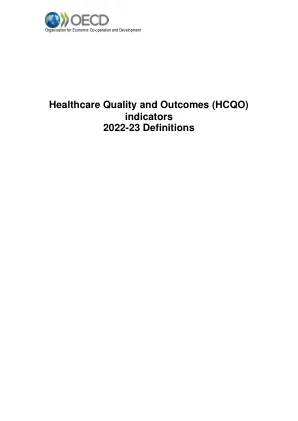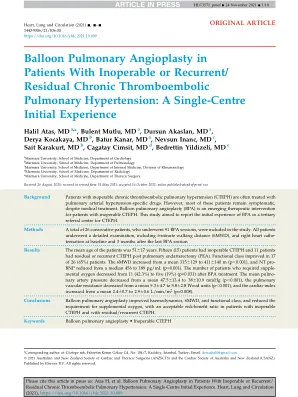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耐化学妊娠滋养细胞肿瘤和免疫疗法的使用:病例报告和文献审查
这是该国抗性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N)中使用免疫疗法的第一个案例。最初用10个蛋白质剂,甲氨蝶呤,乙他霉素D- cyclophophomide和19 cycise etopies of GTN诊断为GTN的41岁,Gravida 4 para 3(3013),诊断为GTN,第三阶段:WHO风险评分为13(绒毛膜脊髓瘤)。甲氨蝶呤和放线霉素D(EP-EMA)。随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ßHCG)水平的持续增长,该患者被称为滋养细胞疾病中心,那里有肿瘤向大脑进展的注意。她开始接受紫杉醇和卡铂(PC)的第三线打捞化疗,随之而来的整个大脑辐照完成了三个周期,此后再次被诊断出了HCG滴度的增加,并增加了HCG滴度的增加,并增加了肺部肿块的数量和大小,而肺部肿块的数量和大小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免疫疗法开始时是pembrolizumab,显示出良好的反应,明显下降了ßHCG水平。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作导致随后的免疫疗法周期明显延迟。通过对伊拉斯的管理,给出了降低剂量降低50%的pembrolizumab的两个周期,在ßHCG水平中相应下降。然而,随后患者患有革兰氏阴性败血症,可能是血液学恶性肿瘤,最终屈服于大量的肺栓塞。该病例强调了迅速诊断并转介到滋养细胞中心的重要性以及在耐化学GTN中使用免疫疗法的重要性。
医疗保健质量和结果(HCQO)指标2022- ...
图1.1。医院入院与医院发作之间的结构和关系5图2.1。糖尿病患者的充分使用降低胆固醇治疗26图2.2。糖尿病患者的首选抗高血压27图2.3。长期使用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一年> 365 DDD)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相关的药物28图2.4。在65岁的人中使用长效苯二氮卓类药物29。图2.5。头孢菌素和喹诺酮的体积是所有系统性抗生素的一部分,处方30图2.6。全身使用抗生素的总体量31图2.7。与口服NSAID结合使用的任何抗凝药物32图2.8。75岁及以上的比例同时服用了5种以上的药物(> 90天不包括皮肤病学和抗生素)34图2.9。规定的阿片类药物的总量(每天1000人口DDD)35图2.10。慢性阿片类药物使用者的人口比例(一年中≥90天的供应)37图2.11。65年及以上的抗精神病药的人比例38图2.12。保留手术项目或未退休设备片段93图2.13。术后肺栓塞 - 臀部和膝盖置换97图2.14。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 - 臀部和膝盖置换102图2.15。术后败血症107图2.16。具有仪器的产科创伤阴道递送112图2.17。产科创伤阴道分娩没有仪器115
手稿ID:ZUMJ-2409-3599 doi:10.21608/ZUMJ.2024.323682.3599评论文章寄生虫交感神经多动症:临床特征,识别
抽象背景:在患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个体中,阵发性交感神经多动症发作(也称为自主风暴)并不罕见。发烧,心动过速,高血压,呼吸症,多汗症和肌张力姿势是它们的一些显着特征。这些情节可以自行开始或被刺激带来。尽管它们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但它们的症状无疑表明激活或抑制交汇区域。这些咒语经常被误认为是癫痫发作,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抗癫痫药物治疗。足够的水合,排除模仿疾病(感染,肺栓塞,脑积水,癫痫),提供有效的镇痛药,并避免触发时避免触发因素,是管理偏离性交感神经多余的一般准则。最有益的药理药物是硫酸吗啡和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例如普萘洛尔。处理难治性实例时,鞘内巴氯芬可能是有用的。尽管它们的有效性较不恒定,但溴o不般的和可乐定对某些患者可能是有益的。结论:PSH是一个很常见的,但通常忽略了急性弥漫性或多灶性脑疾病的并发症。最常见的是遭受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无意识的人。反复发作,心动过速,呼吸症,高血压,汗水以及偶尔发烧和肌张力的姿势的突然发作是病情的标志。有临床诊断。减少可能引起发作并引发预防和流产药物的任何外部刺激(例如静脉注射吗啡,加巴喷丁,普萘洛尔和可乐定)也是治疗的一部分。早期和足够的PSH治疗可能会降低随后问题的风险,例如肌肉染色,营养不良和脱水。关键字:阵发性交感神经多动症,创伤性脑损伤,重症监护病房
Olokizumab,一种针对静脉血栓栓塞和JAK抑制剂和其他免疫调节药物: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瑞典比较安全研究
抽象的目的是评估和比较用Janus激酶抑制剂(JAKI)治疗的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静脉血栓栓塞(VTE)的发生率,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TNFI)或其他修饰抗病毒药物(BDMARDS)。进行上下文化,以评估瑞典一般人群和RA源人群中的VTE发生率。我们在2010年至2021年在瑞典进行了全国性登记册,主动比较器,新的用户设计队列研究。瑞典风湿病学质量登记册与国家卫生登记册有关,以识别Jaki,TNFI或非TNFI BDMARD(n = 32 737治疗计划)的jaki,TNFI或非TNFI BDMARD的治疗群体(暴露)。我们还确定了一般人群队列(匹配1:5,n = 92 108)和“总RA”比较器队列(n = 85 722)。结果是在随访期间首次进行VTE的时间,整体和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和肺栓塞(PE)。我们使用COX回归计算了发病率(IR)和多变量调整后的HR。基于559起事件事件的结果,VTE的年龄和性别标准的IR(95%CI)为5.15人为每1000人年(4.58至5.78),用于治疗的TNFI患者,11.33(8.54至15.04)(8.54至15.04)的患者对Jaki,5.86 and coh and 3.6 9 and 3.69 and 3.69,in 3.69 and 3.6 9 (3.14至3.43)在一般人群中。使用Jaki与TNFI的VTE进行了完全调整的HR(95%CI)为1.73(1.24至2.42),PE的相应HR为3.21(2.11至4.88)和0.83(0.47至1.45),DVT的相应HR为0.83(0.47至1.45)。与用BDMARDS治疗的人相比,在临床实践中用JAKI治疗的RA治疗的RA治疗的患者的结论越来越限于PE。
严重血流动力学障碍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患者肺动脉内膜切除术前药物治疗的应用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CTEPH) 是急性肺栓塞的一种罕见并发症,其特征是肺大动脉的纤维血栓性阻塞无法解决。肺动脉内膜切除术 (PEA) 是该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可显著提高生存率。血流动力学状况较差的患者手术后预后较差,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手术前使用药物治疗来优化血流动力学是否可以改善预后。本研究的目的是根据诊断时的血流动力学状况评估 PEA 前药物治疗的作用。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接受 PEA 的所有患者。收集功能、临床和血流动力学数据以评估主要的预后决定因素。根据血流动力学严重程度和手术前使用靶向疗法对患者进行分层。共纳入 108 名患者。 35 名患者 (32.4%) 在 PEA 前使用了靶向治疗。药物治疗将手术时间推迟了约 7 个月。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和仅接受支持治疗的患者的总生存率没有差异(分别为 87.8% 和 80.3%,p = 0.426)。尽管如此,在分析严重血流动力学障碍(定义为基线时心输出量低 (< 3.7L/min))的患者组时,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的一年生存率明显更高。对于心输出量低的高危 CTEPH 患者,在 PEA 前使用靶向治疗与更好的结果相关,这表明在这一特定亚组中术前使用药物治疗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J. Pediatr。 Cardiol。卡片。外科。 4(2):63-74(2020)美国的儿科心脏重症监护
TE心脏手术的下一个巨大进步是心肺旁路机的开发。TIS技术最初旨在在肺栓塞切除术期间使用。约翰·吉本博士在1953年成功使用了原始的心脏肺机器来进行心脏内部修复,以封闭心房间隔缺陷。4)在开放心脏手术期间成功使用心脏旁搭桥,这迅速扩大了其用于修复和抑制各种先天性心脏病变的使用,以及对专门的外科外科重症监护病房的伴随需求。第一批小儿重症监护病房(PICU)于1955年在瑞典的Gotebord的儿童医院建立,他们成功治疗了一个莫里斯·邦德男孩的侵害性手术,以通过内托肠炎,手动插管,手动插管和血液转移来进行破裂的阑尾炎。在这种早期模型中,主要的麻醉剂Goran Haglund博士认识到护士和护士助理对这一成功结果的重要重要性。5)随后的十年在1967年在费城儿童医院的整个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第一个PICU之间开发了类似单位。6)随着这些PICU的发展和扩展,专业培训计划的发展,美国儿科学会于1984年创建了一部分重症监护医学,美国儿科委员会在1987年在跑场上进行了首次认证考试。te扩展PICUS以及监测和支持设备的技术进步已将小儿重症监护的领域推向其当前状态,具有救助和抚养儿童的能力,为在先前的ERA中丧生的患者提供了生存。
血浆中 C1 抑制剂水平高与未来静脉血栓栓塞风险降低相关
[1] Naess IA、Christiansen SC、Romundstad P、Cannegieter SC、Rosendaal FR、Hammerstrom J。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J Thromb Haemost。2007;5:692-9。[2] Arshad N、Isaksen T、Hansen JB、Braekkan SK。从一般人群中招募的大型队列中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病率的时间趋势。Eur J Epidemiol。2017;32:299-305。[3] Winter MP、Schernthaner GH、Lang IM。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慢性并发症。J Thromb Haemost。2017;15:1531-40。 [4] Schulman S、Lindmarker P、Holmstrom M、Larfars G、Carlsson A、Nicol P、Svensson E、Ljungberg B、Viering S、Nordlander S、Leijd B、Jahed K、Hjorth M、Linder O、Beckman M. 首次静脉血栓栓塞症发作后用华法林治疗 6 周或 6 个月 10 年的血栓后综合征、复发和死亡。J Thromb Haemost。2006;4:734-42。[5] Klok FA、van der Hulle T、den Exter PL、Lankeit M、Huisman MV、Konstantinides S. 肺栓塞后综合征:肺栓塞慢性并发症的新概念。血液评论。2014;28:221-6。 [6] Jorgensen H、Horvath-Puho E、Laugesen K、Braekkan S、Hansen JB、Sorensen HT。丹麦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后永久性工作相关残疾养老金的风险: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PLoS Med。2021;18:e1003770。[7] Cushman M。静脉血栓形成的流行病学和风险因素。Semin Hematol。2007;44:62-9。[8] Lijfering WM、Rosendaal FR、Cannegieter SC。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从流行病学角度看目前的认识。Br J Haematol。2010;149:824-33。 [9] Kearon C、Ageno W、Cannegieter SC、Cosmi B、Geersing GJ、Kyrle PA。抗凝控制和血栓性疾病预测与诊断变量小组委员会。将患者分为诱发性或非诱发性静脉血栓栓塞症:ISTH SSC 指导。J Thromb Haemost。2016;14:1480 – 3。https://doi.org/10.1111/jth.13336 [10] Christensen DM、Strange JE、Phelps M、Schjerning AM、Sehested TSG、Gerds T、Gislason G。2005 年至 2021 年丹麦心肌梗死发病率的年龄和性别特定趋势。动脉粥样硬化。 2022;346:63-7。[11] Sulo G、Igland J、Vollset SE、Ebbing M、Egeland GM、Ariansen I、Tell GS。挪威急性心肌梗死发病趋势:使用 CVDNOR 项目的国家数据对 2014 年进行更新分析。Eur J Prev Cardiol。2018;25:1031-9。[12] Munster AM、Rasmussen TB、Falstie-Jensen AM、Harboe L、Stynes G、Dybro L、Hansen ML、Brandes A、Grove EL、Johnsen SP。不断变化的形势:2006-2015 年静脉血栓栓塞症住院患者发病率和特征的时间趋势。Thromb Res。2019;176:46-53。 [13] Ghanima W、Brodin E、Schultze A、Shepherd L、Lambrelli D、Ulvestad M、Ramagopalan S、Halvorsen S。2010-2017 年挪威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病率和患病率。血栓研究。 2020;195:165 – 8 。 [14] 万德尔 P,福斯伦德 T,Danin Mankowitz H, Ugarph-Morawski A, Eliasson S, Braunschwieg F, Holmstrom M. 2011-2018 年斯德哥尔摩静脉血栓栓塞症:人口统计学研究。《血栓溶解杂志》。2019;48:668 – 73。
糖尿病状况和其他因素作为SARS-COV-2感染期间血栓和血栓栓塞事件风险的相关性:使用Cerner Real-World Data™
我们试图在SARS-COV-2感染的个体中试图检查的抽象目标是否通过存在糖尿病诊断来改变血栓形成和血栓栓塞事件(TTE)。此外,我们分析了1型糖尿病(T1DM)与2型糖尿病(T2DM)中是否存在TTE的差异风险。设计回顾性案例对照研究。设置2020年12月版本的Cerner Real-World Data Covid-19数据库是来自87个基于美国卫生系统的电子医疗记录(EMR)数据的全国性数据库。参与者我们分析了322 482名患者的EMR数据,> 17岁,涉嫌或确认的SARS-COV-2感染,他们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9月中旬接受了护理。,2750具有T1DM; 57 811具有T2DM; 261 921没有糖尿病。结果TTE,定义为存在心肌梗塞,血栓性中风,肺栓塞,深静脉血栓形成或其他TTE的诊断代码。T1DM(调整或(AOR)2.23(1.93-2.59))和T2DM(AOR 1.52(1.46–1.58))的TTE结果 TTE的结果较高,而无糖尿病。 在糖尿病患者中,T2M与T1DM相比(AOR 0.84(0.72-0.98))TTE的几率较低。 结论在19009年期间TTE的疾病风险在糖尿病患者中较高。 此外,T1DM与T2DM的TTE风险更高。 在未来的研究中确认与糖尿病相关的凝血风险增加可能需要将糖尿病状态纳入SARS-COV-2感染治疗算法。TTE的结果较高,而无糖尿病。在糖尿病患者中,T2M与T1DM相比(AOR 0.84(0.72-0.98))TTE的几率较低。结论在19009年期间TTE的疾病风险在糖尿病患者中较高。此外,T1DM与T2DM的TTE风险更高。在未来的研究中确认与糖尿病相关的凝血风险增加可能需要将糖尿病状态纳入SARS-COV-2感染治疗算法。
SARS-COV-2中的突变导致峰值蛋白质的抗原变异:疫苗发育的挑战
抽象的背景糖尿病被认为是静脉血栓栓塞(VTE)的危险因素,但观察性研究已经报道了爆发的发现。这项研究旨在研究1型和2型糖尿病与VTE的因果关系,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和肺栓塞(PE)。方法,我们通过使用来自欧洲个体进行的大型基因组关联研究的摘要级别的数据,设计了双向两样本的孟德尔随机分析(MR)分析。使用乘法随机效应方法的逆差异加权来获得主要因果估计值,并补充了加权中值,加权模式和MR EGGER回归,作为灵敏度分析以测试结果的鲁棒性。结果我们发现1型糖尿病对VTE的因果关系没有显着的因果影响(优势比[OR]:0.98,95%的置置间隔[CI]:0.96 - 1.00,p¼0.043),dvt(or::0.95%CI:0.95%CI:0.95%CI:0.95%:0.95 – 1.00 – 1.00,pE 1.00,pETE,pE 1.102),或:e或:0.102),或:e102),或eL¼10.10.10.10.10.10.10.1.10.10.10.10.beLeel和eel¼.1.1.1.1.1.1.1.1.10.1.beLeel和: 0.96 - 1.01,p¼0.160)。Similarly, no signi fi cant associations of type 2 diabetes with VTE (OR: 0.97, 95% CI: 0.91 – 1.03, p ¼ 0.291), DVT (OR: 0.96, 95% CI: 0.89 – 1.03, p ¼ 0.255), and PE (OR: 0.97, 95% CI: 0.90 – 1.04, p ¼还观察到0.358)。多变量MR分析的结果与单变量分析中的发现一致。在另一个方向上,结果没有显示VTE对1型和2型糖尿病的重要因果作用。结论该MR分析表明,在这两个方向上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和2型糖尿病与VTE的因果关系,这与先前的观察性研究相结合,该研究为理解糖尿病和VTE的潜在发病机理提供了线索。
气球肺部血管成形术患有无法手术或复发/残留/残留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单中心初始经验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是一种疾病,是由有组织的纤维状凝块持续阻塞肺动脉动脉引起的,导致流量再分配和肺微血管微血管血管的继发重塑。cteph是肺高血压(pH)的显着原因,如果没有治疗而导致右心力衰竭和死亡[1]。肺部内膜(PEA)是已建立的治疗性干预措施,具有最多的证据,是针对CTEPH患者的指南建议治疗。,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不符合PEA的资格,因为在手术过程中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或者存在禁止手术的严重合并症。另一方面,大约一半接受PEA的患者具有持续的pH值,通常是轻度,但有时是中度或重度,需要额外的治疗[2-4]。此外,CTEPH患者可能由于无效的抗凝或血栓形成而出现肺栓塞,即使在那些以前接受过治疗手术的患者中,也会导致复发性pH值。患有无法手术的CTEPH和豌豆后残留或复发性pH的患者均用肺动脉高压(PAH)患者治疗。然而,尽管用PAH特异性药物进行治疗,但这些患者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有明显的症状。气球肺血管成形术(BPA)是一种新兴的治疗干预措施,是Feinstein等人首先描述的。CTEPH患者[5]。然而,尽管血流动力学的改善,但由于重新灌注肺损伤和肺部出血的显着并发症的频率很高,因此被放弃了。日本研究人员通过重复上演的过程对BPA进行了限制,以减少再灌注肺损伤和肺出血[6,7]。越来越多的研究最近显示出血流动力学,症状和功能能力的改善,并通过重新固定的BPA技术降低了重大并发症的率显着降低[8-11]。因此,2017年10月,目前的中心开始了一个BPA计划,该计划被认为是无法使用或持续性或经常性pH的患者。本研究旨在报告当前中心BPA的初始经验,该中心是第三级转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