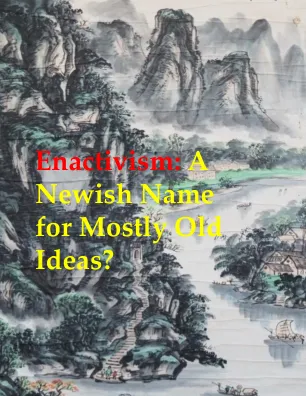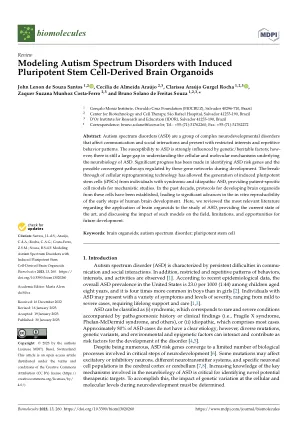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到大脑或不脑官
自2013年脑器官成立以来,有关该主题的研究和讨论成倍增长。他们概括人脑解剖和功能特征的能力引起了全球兴趣。在2013年至2022年之间,平均每月发表了10篇以上文章(1826),其中1/3超过1/3不是原始研究,而是评论(587,Source PubMed)。科学家将脑器官剥削为基础研究,毒性和药物测试的脑模拟工具,并考虑了其潜在的发音和意识。虽然尚未检测到这些脑官的争论特征,但对当前可能的高级应用程序的猜测是令人兴奋的前景。Smionerova等。(1)就其计算和认知能力以及功耗非常低的作用而言,为人脑的至高无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将这些参数与最佳计算机进行比较,这些计算机已知具有实质性的碳足迹。他们还为利用脑器官作为生物计算的下一代机械而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由于这些3D构造可能是人脑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认为,与我们的大脑一样,与众不同的不同构造可能会像我们的大脑一样有效。因此,设想了一项跨学科研究计划用于利用–
何时脑官是候选感知者?
摘要本文认为,杜威(Dewey)表达了对建构主义的核心发挥作用:生物不会遇到现实的现实,而是通过改变周围环境来将它们带出来。他补充说,建构主义并不能消除现实主义,因为一旦引入了变化,就与生物的能力有关。这构成了困境。如果启用主要需要改变外部环境,那么该运动就会重复实用主义,也崩溃了一个基础,其许多作者将他们的观点与生态心理学的真实性ISM不同。然而,正如颁布主义者的语言有时所暗示的那样,如果建设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部的,那么批评家可能会说,运动反向运动陷入了早期的现代孤独主义。一个更广泛的论点是,颁奖主义者有时会使詹姆斯的描述为一致的经验主义。在这里,风险是研究人员担任职位不是因为证据而是不管有证据,或者规定了术语定义,这些定义会提前排除反对意见。即使是物理学仍然不合同,并且可能会有伴侣的心理记载空间。或通常是敌对的立场,例如发挥作用和功能主义,具有一些术语 - 逻辑重新构架,可调和。本文还涉及历史事务,例如美国哲学和实施主义具有亚洲和进化论的意义,或者它们会对普通学校做出反应。目的是阐明所讨论的行动,并通过将自己的对抗敌人定向,而不是事实,以确定颁奖主义者在何处参与中途经验主义。
神经炎症疾病建模的透视性晚期脑官
尽管用小鼠组织完成了脑器官的第一项工作,但它代表了基于细胞培养的人脑建模之前和之后(Lancaster等,2013)。脑类器官具有高细胞异质性,许多细胞类型都集成到同一系统中。类器官不仅代表了研究健康中神经过程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患病的环境中,尤其是那些具有复杂遗传方面的那些在动物中构成挑战的遗传方面。对人类神经系统疾病的临时研究意味着由于遗传背景的多样性,在遗传疾病的情况下,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复杂性(CNS),动物模型缺乏可重复性以及在获得人脑活检方面的困难。大脑器官系统的发展在模仿中枢神经系统的复杂性并克服所有这些缺点方面取得了突破。由各种神经元细胞类型组成的脑器官的细胞异质性,可以彼此连接和相互作用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获得患者样品,将其重新编程为干细胞的简单性,并将其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建模,增强其翻译价值和更个性化的方法。IPSC衍生的人脑器官已用于研究脑感染(Qian等,2016),神经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病(Chen等,2021)。IPSC衍生的人脑器官已用于研究脑感染(Qian等,2016),神经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病(Chen等,2021)。
用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的脑官
摘要: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组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沟通和社交互动,并以受限的兴趣和重复行为模式出现。对ASD的敏感性受到遗传/可遗传因素的强烈影响;但是,了解ASD神经生物学的基础机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识别ASD风险基因以及在开发过程中这些基因网络调节的可能收敛途径已取得了显着进步。通过细胞重编程技术的突破使综合症和特发性ASD个体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产生,从而为机械研究提供了患者特异性细胞模型。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建立了从这些细胞开发脑器官的方案,从而导致人脑发育早期步骤的体外可重复性的显着进步。在这里,我们回顾了有关脑器官在ASD研究,提供当前艺术状态的最相关文献,并讨论了此类模型对未来发展的领域,局限性和机会的影响。
脑官,嵌合体和其他“怪物”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1818年写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欧洲的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科学革命只是出现了。Luigi Galvani(1737–1798)最近证明了电力对解剖动物的作用,而他的侄子Giovanni Aldini(1762-1834)用电力“动画”了人类尸体。在考虑伦理学之前,采用了这种技术,但是公平地说,生物伦理学的纪律不会再过一个半世纪。归雪莱这样的作家创造了叙事,可以通过科学进步的道德含义来帮助社会思考。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出发写她的哥特式恐怖故事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微妙而深刻的方式操纵生活已经有可能。我们现在有生物伦理学,但是科学进步定期超过我们思考的能力。没有比当前神经生物学研究更清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