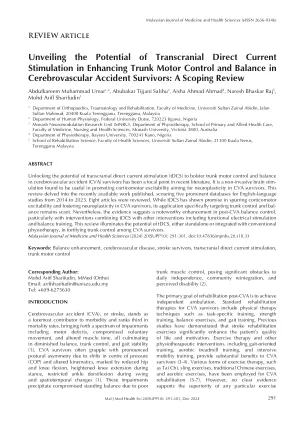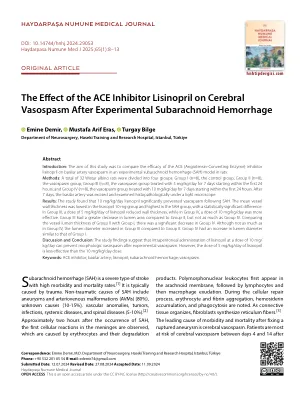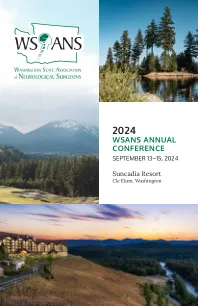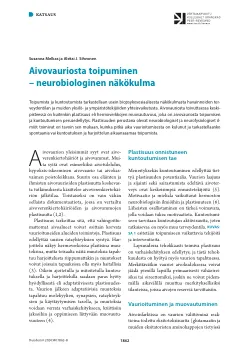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A2V:通过两阶段训练血管造影到世纪的半监督域适应框架,用于脑血管分割
我们提出了一个半监督的域适应框架,用于来自不同图像模式的脑血管序列。现有的最新方法集中在单一模态上,尽管可用的脑血管成像技术广泛。这可能导致重大分布变化,从而对跨模式的概括产生负面影响。By relying on annotated angiographies and a limited number of an- notated venographies, our framework accomplishes image-to-image translation and se- mantic segmentation, leveraging a disentangled and semantically rich latent space to represent heterogeneous data and perform image-level adaptation from source to tar- get domains.此外,我们降低了基于周期的架构的典型复杂性,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抗性训练的使用,这使我们能够通过稳定的培训构建一个高效且直观的模型。我们评估了有关磁共振血管造影和静脉曲张的方法。在源域中实现最先进的性能时,我们的方法在目标域中达到了仅8个目标域的骰子得分系数。降低了9%,突出了其在不同模态上稳健脑血管图像分割的有希望的潜力。
最初发表于:Subochev,Pavel;斯莫利纳,叶卡捷琳娜;谢尔盖娃,叶卡捷琳娜;基里林,米哈伊尔;奥尔洛娃,安娜;仓吉娜,达莉亚;埃米亚诺夫,丹尼尔;
摘要:啮齿动物脑血管成像是光声学研究大脑活动和病理的热门应用之一。深层脑结构成像常常受到光传输和声学检测系统布置不合理所阻碍。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重新审视了光声信号生成背后的物理原理,以便从理论上评估最佳激光波长,以超越光在高度散射和吸收的脑组织中扩散所造成的穿透障碍,对啮齿动物进行脑血管光声血管造影。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扩散近似的综合模型,使用与典型鼠脑非常相似的光学和声学参数来模拟光声信号生成。该模型揭示了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谱中的三个特征波长范围,最适合对不同大小和深度的脑血管进行成像。数值模拟证实了理论结论,而体内成像实验进一步验证了准确分辨 0.7 至 7 毫米深度范围内脑血管的能力。
在阿尔茨海默氏病中脑血管损伤和淀粉样蛋白β的平行神经炎症途径
要点问题:神经炎症如何影响脑血管损伤的下游特征和淀粉样蛋白β(Aβ)在阿尔茨海默氏病中?发现:在这项研究的126名没有痴呆症的老年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神经炎症途径的证据,这些途径导致神经变性和记忆缺陷。一条路径涉及血浆YKL-40及其对脑血管损伤的影响,如白质高强度(WMH)在MRI扫描时测量。另一种涉及血浆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及其对通过18F氯二肽(FBP)PET测量的Aβ沉积的影响。通过等离子体PTAU-217测量的Tauopathy上的两种途径都与较低的内侧颞叶(MTL)皮质厚度和海马体积相关,因此是记忆缺陷。含义:炎症通过多种不同的平行途径作用于阿尔茨海默氏病的机制,这些途径下游会趋于神经变性。
揭示了经颅直流刺激在增强躯干运动控制和脑血管事故幸存者平衡方面的潜力:
解锁经颅直流电流刺激(TDC)的潜力增强脑血管事故(CVA)幸存者的平衡控制和平衡一直是最近文献的焦点。这是一种非侵入性脑刺激,可用于促进CVA幸存者中神经可塑性的皮质运动兴奋性。这篇评论深入研究了最近发布的工作,从2014年到2023年,搜索了五个著名的英语研究数据库。审查了八篇文章。TDCS在刺激皮质运动兴奋性和促进CVA幸存者中的神经可塑性方面表现出了希望,但其专门针对躯干控制和BALCE的应用仍然很少。尽管如此,证据表明,CVA后平衡控制中值得注意的增强,尤其是将TDC与其他干预措施(包括功能性电刺激和平衡训练)结合起来的干预措施。本评论阐明了TDC的潜力,即独立或与常规物理疗法集成,以强化CVA幸存者之间的躯干控制。马来西亚医学与健康科学杂志(2024)20(SUPP10):291-301。 doi:10.47836/mjmhs.20.s10.33马来西亚医学与健康科学杂志(2024)20(SUPP10):291-301。 doi:10.47836/mjmhs.20.s10.33
实验性亚蛛网膜下腔出血后,ACE抑制剂赖诺普利对脑血管痉挛的影响
简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比较ACE(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赖因普利在大鼠基底动脉血管痉挛上的疗效。方法:总共32个Wistar白化大鼠分为四组:I组(n = 8),对照组; II组(n = 8),血管痉挛组;第三组(n = 8),在前24小时内用5 mg/kg/天处理的血管痉挛组7天;和IV组(n = 8),在前24小时内用10 mg/kg/天处理的血管痉挛组开始7天。在7天后,在光学显微镜下切除基底动脉并在组织病理学上检查。结果:研究发现10 mg/kg/day Lisinopril在SAH后明显阻止了血管痉挛。在赖诺普利10 mg组中,平均容器壁厚度最低,在SAH组中最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在第三组中,丽索普利的剂量为5 mg/kg/kg/天的壁厚度减小,而在第四组中,剂量为10 mg/kg/day的剂量更有效。III组的管腔面积降低更大,但不如第四组。将II组的血管管腔厚度与I组的血管厚度进行比较,IV组显着下降。尽管在第四组中不如第IV组中的管腔直径增加与II组相比增加。第四组的管腔直径与I组相似。组的直径相似。 讨论和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以10 mg/ kg/ day的剂量腹膜内施用林顿甲求,可以防止实验性血管痉挛后的形态血管痉挛。第四组的管腔直径与I组相似。讨论和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以10 mg/ kg/ day的剂量腹膜内施用林顿甲求,可以防止实验性血管痉挛后的形态血管痉挛。然而,赖诺普利的5 mg/kg/天的剂量不如10 mg/kg/day剂量的剂量。关键字:ACE抑制剂;基底动脉; Lisinopril;亚蛛网膜下腔出血;血管痉挛。
自我耗尽与健康促进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在不断增加的城市化,人口的进一步衰老以及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糖尿病患病率(DM)以及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数一直在令人震惊的速度增殖,这使其成为全球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的另一个主要挑战,这是另一个主要挑战。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2)发布的全球糖尿病图,全球约有5.37亿成年人(20 - 75岁)患有糖尿病,占总数的11.30%。65岁及以上糖尿病的老年人的数量高达1.36亿,占19.9%。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数量最多,老年人(≥60岁)中糖尿病的患病率为30.49%,总数为7813万,而老年人已成为主要人群
WSANS 年度会议
11:15–12:15 PM “使用人工智能预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预后和并发症” Margaret McGrath 医学博士,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住院医师 “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了解脑血管痉挛期间 Willis 环的侧支流动及其临床意义” Zachary Abecassis 医学博士,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住院医师 “AR 在规划脑血管手术中的作用” Radwan Takroni 医学博士、理学硕士,神经外科脑血管/血管内研究员,瑞典 “多级脊柱融合后骨矿物质密度与远端连接性脊柱后凸和远端连接性衰竭的关系: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Clifford Pierre 医学博士,神经外科研究脊柱研究员,瑞典
脑损伤的恢复——神经生物学视角
脑损伤最常见的原因是脑血管疾病和脑损伤。其他原因包括脑炎、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或脑瘤切除手术。大多数关于动物和人类脑损伤可塑性的研究都涉及脑血管意外的后果。迄今为止,比较脑血管疾病和脑损伤的可塑性的文献很少(1,2)。可塑性是指未受损的大脑区域可以部分替代受损区域的功能。可塑性要求创建新的轨道连接。训练体现在神经网络的可塑性变化上,但另一方面,这些变化无论是否训练都会发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变化也可能是有害的 (3)。适当时间和量身定制的康复和训练将带来有益的或适应性的可塑性的最佳效果。受伤后,分子、突触、通路和行为水平都会发生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化可与早期发育、关键期和学习相关的可塑性进行比较(4)。
小鼠中无机磷酸盐出口商的杂合性导致脑血管钙化,微血管病和小胶质细胞增多
在没有全身性钙和磷酸盐失衡的情况下,基底神经节中脑微血管的抽象钙化是原发性家族性脑钙化(PFBC)的标志,这是一种罕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在钠依赖性磷酸磷酸转运蛋白2(SLC20A2),异形和多层逆转录病毒受体1(XPR1),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B(PDGFB),血小板生长因子受体β(PDGFRB),脑质量发生的gylasise(PDGFB)的基因(pDGFB),脑料beta和脑电图调节(XPR1)的反应(PDGFB)调节gycose(pDGFB),已知分子2(JAM2)引起PFBC。 XPR1的功能丧失突变是Meta-Zoans中唯一已知的无机磷酸盐出口剂,引起了主要遗传的PFBC,但在2015年首次报道,但到目前为止,在大脑中,尚无研究的研究是否尚未解决一种功能等位基因的损失,是否导致一种常用的生物体(一种对人类疾病模拟人类疾病的常用生物体)的病理学改变。 在这里我们表明,用于XPR1的小鼠(XPR1 WT/LACZ)的杂合子存在脑脊液中的无机磷酸盐水平,以及丘脑中血管钙化的年龄和性别依赖性生长。 血管钙化被血管基底膜包围,位于平滑肌层的小动脉。 与先前特征的PFBC小鼠模型相似,XPR1 WT/LACZ小鼠中的血管钙化含有骨基质蛋白,并被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包围。 但是,小胶质细胞激活不仅限于钙化血管,而是显示出广泛的存在。 除了血管钙化外,我们还观察到血管在钠依赖性磷酸磷酸转运蛋白2(SLC20A2),异形和多层逆转录病毒受体1(XPR1),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B(PDGFB),血小板生长因子受体β(PDGFRB),脑质量发生的gylasise(PDGFB)的基因(pDGFB),脑料beta和脑电图调节(XPR1)的反应(PDGFB)调节gycose(pDGFB),已知分子2(JAM2)引起PFBC。XPR1的功能丧失突变是Meta-Zoans中唯一已知的无机磷酸盐出口剂,引起了主要遗传的PFBC,但在2015年首次报道,但到目前为止,在大脑中,尚无研究的研究是否尚未解决一种功能等位基因的损失,是否导致一种常用的生物体(一种对人类疾病模拟人类疾病的常用生物体)的病理学改变。在这里我们表明,用于XPR1的小鼠(XPR1 WT/LACZ)的杂合子存在脑脊液中的无机磷酸盐水平,以及丘脑中血管钙化的年龄和性别依赖性生长。血管钙化被血管基底膜包围,位于平滑肌层的小动脉。与先前特征的PFBC小鼠模型相似,XPR1 WT/LACZ小鼠中的血管钙化含有骨基质蛋白,并被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包围。但是,小胶质细胞激活不仅限于钙化血管,而是显示出广泛的存在。除了血管钙化外,我们还观察到血管
VEGFR3 调节 22q11.2 缺失综合征小鼠模型中的脑微血管分支
单个 TBX1 拷贝的丢失是 22q11.2 缺失综合征大部分临床体征和症状的根源,22q11.2 缺失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疾病,以多种先天性异常和脑相关临床问题为特征,其中一些可能与血管有关。Tbx1 突变小鼠有脑血管异常,因此使其成为了解人类疾病的有用模型。在这里,我们发现 TBX1 在小鼠脑中的主要形态发生功能是通过调节 Vegfr3 来抑制血管分支形态发生。我们证明,在 Tbx1 突变背景下,使 Tbx1 表达域中的 Vegfr3 失活可增强脑血管分支和伪足形成,而增加该域中的 Vegfr3 表达则完全挽救了这些表型。使用内皮小管生成的体外模型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总体而言,该研究结果提供了遗传证据,表明 VEGFR3 是小鼠脑内早期血管分支和丝状伪足形成的调节器,并且可能是 Tbx1 功能丧失导致的脑血管表型的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