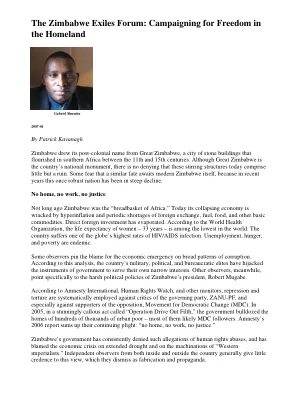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数字解决方案 | GSMA
人口。由于城市贫民无力居住在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社区,许多非洲城市的特点是低层非正规住房和城市蔓延。对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政当局和国有公用事业公司来说,城市蔓延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许多城市都在努力解决负担能力与覆盖范围之间的差距(见图 2)。大多数城市都必须在向中央政府或投资者证明其财务可行性的同时,调动大量投资来扩大和改善对城市贫民的基本服务。虽然发展中国家只有不到 20% 的城市被认为有足够的信用度向当地投资者发行债券,只有 4% 的城市可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所需的估计超过 2.5 万亿美元的投资中,很大一部分必须投资于这些城市。9
马尼拉的“危险地带”、“死亡地带”和基础设施空间建设的悖论
基于城市化分裂的遗产和随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我们反思了马尼拉的基础设施发展轨迹及其实施产生的空间关系。空间工作基础设施在融入城市结构时所起的作用表明,城市空间的多种共同生产模式正在发挥作用。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全球南方城市的经验探讨了基础设施空间的悖论及其影响。我们关注两种基础设施空间建设模式:通过城市“危险区”驱逐实现的基础设施剥夺,以及在边缘地区的“死亡区”维持基础设施。第一种模式是,为实现世界一流、具有韧性的城市建设愿望,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导致城市贫民被迫迁离,贫民窟被划定为“危险地带”——国家指定为不适合居住且有洪水危险的边缘空间,因此计划进行清理(Alvarez and Cardenas,2019 )。第二种模式以匮乏和缺失为框架,城市贫民在“死亡地带”——偏远的城市边缘地区——为获得居住空间和获取重要服务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被驱逐者在这些地方过着更加凄惨的生活(Dalisay and De Guzman,2016 ;Ortega,2020 )。这两种基础设施模式产生了剥夺性和维持性的逻辑、政治和想象,城市贫民与之产生了矛盾的共鸣。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将中心和边缘的生产联系在一起,
C6T6u2_Waste_Materials_in_Ar...
我们的经济体系建立在耗尽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的原则之上,这必然导致废物的产生。这一体系的运作是以牺牲我们的社会诚信和环境可持续性为代价的。城市贫民在热气腾腾的垃圾填埋场寻找贵重物品的画面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性表现。垃圾场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经济成功和快速城市化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隔离之间的纠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画面几乎只出现在城市群中,而绝大多数非有机废物都是在这里产生的。废物不属于商品和资源的代谢循环和流动模型,而是被视为线性过程的死胡同;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被埋葬——看不见,也忘了——作为一种无形的、没有价值的物质,因此被厚厚的土层覆盖或烧成灰烬。
城市公共空间战略 城市领导者指南
某些公共空间效益无法通过基于场地的公共空间或个别空间和场所方法实现,无论这些方法本身多么成功。舒适、清洁、安全和活力可以扩展到城市的许多场地,但通常无法提供分布、连通性、位置可达性或程序多样性。这些需要全市范围的公共空间系统,如果协调得当,其总体效益将超过其各部分之和。街道和开放空间的连接矩阵构成了城市其余部分依附的骨架。除了公园、游乐场和市场之外,这还可能包括建筑物和路边之间的边缘空间(正面和/或小巷)或仅仅是路边边缘,这些空间本身很少被视为此类空间。许多这些空间已被重新分配给城市贫民使用。
津巴布韦流亡者论坛
津巴布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1 世纪到 15 世纪,当时的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发展迅速。尽管大津巴布韦是该国的国家纪念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激动人心的建筑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有些人担心现代津巴布韦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因为近年来,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家急剧衰落。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正义。不久前,津巴布韦深受恶性通货膨胀和外汇、燃料、食品和其他基本商品周期性短缺的困扰。外国直接投资蒸发殆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津巴布韦女性的预期寿命为 33 岁,是世界上最低的。该国是全球 HIV/AIDS 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失业、饥饿和贫困随处可见。一些观察家将原因归咎于根据这种分析,该国的军事、政治和官僚精英劫持了政府工具来为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其他观察家则特别指出了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严酷政治政策。据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其他观察员称,政府系统性地对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批评者,尤其是对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 (MDC) 的支持者实施镇压酷刑。2005 年,政府在一次令人震惊的“驱逐污秽行动”中,推倒了数十万城市贫民的房屋——其中大多数人可能是 MDC 的追随者。大赦国际 2006 年的报告总结了他们持续的困境:“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正义。”津巴布韦政府一直否认这种人为操纵的指控,将经济危机归咎于长期干旱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国内外独立观察员一般不相信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是捏造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