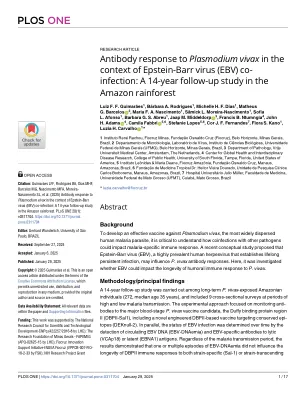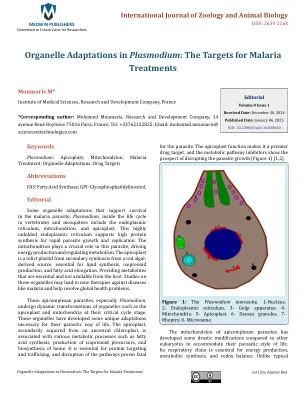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免疫力会对人类疟原虫的繁殖与生存造成影响
许多病原体,包括疟原虫,都会产生专门的生命阶段,用于在宿主体内繁殖和向外传播。能够加快繁殖速度的特性(包括对传播阶段的有限投入)应该会使宿主健康面临更大的风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然而,尚不清楚为什么寄生虫没有进化出更快的繁殖速度,因为疟原虫似乎并不遵循传统预测会限制寄生虫进化的传播速度和持续时间之间的权衡。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引入了一个感染年龄结构的宿主内数学模型,该模型结合了动态免疫清除,以研究潜在的权衡并了解寄生虫如何优化其传播投资。当投资在所有感染年龄中保持不变时,增加传播投资会减少感染持续时间和寄生虫适应度,最佳投资发生在相对较低的值(约 5%),远低于从缺乏寄生虫投资和免疫清除之间动态反馈的模型中恢复的最佳值。对于年龄变化策略,我们的模型表明,疟原虫可以通过延迟传播投资来提高其适应性,从而最初在宿主内更快地繁殖。我们的结果表明,适应性免疫可以施加生存-繁殖权衡,这解释了为什么疟原虫无法在宿主内更快地进化。我们的理论框架为理解传播投资策略如何改变疟疾感染生命周期内的传染时间提供了基础,这对寄生虫响应控制努力的进化具有影响。
双氢青蒿素哌喹和青蒿琥酯阿莫地喹间歇性预防治疗对学龄儿童抗六种血型恶性疟原虫抗原 IgG 应答的影响
在疟疾高发地区,已经实施了几种干预策略,其中包括间歇性预防治疗 (IPT),这是一种阻断传播并降低疾病发病率的策略。然而,实施 IPT 策略引起了真正的担忧,因为它干预了对疟疾的自然获得性免疫的发展,而这种免疫需要与寄生虫抗原持续接触。本研究调查了在学童中应用二氢青蒿素-哌喹 (DP) 或青蒿琥酯-阿莫地喹 (ASAQ) IPT (IPTsc) 是否会损害对六种疟疾抗原的 IgG 反应性。坦桑尼亚东北部的一项 IPTsc 试验以四个月的间隔施用了三剂 DP 或 ASAQ,并对学童进行了随访。本研究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技术比较了干预组和对照组中 IgG 对恶性疟原虫红细胞膜蛋白 1 (PfEMP-1) 的 GLURP-R2、MSP1、MSP3 和 CIDR 结构域 (CIDRa1.1、CIDRa1.4 和 CIDRa1.5) 的反应性。研究期间,共有 369 名学童参与分析,对照组、DP 组和 ASAQ 组分别有 119 名、134 名和 116 名参与者。在干预期期间和干预期后,疟疾抗原识别的广度显著增加,且研究组间并无差异(趋势检验:DP,z 分数 = 5.92,p < 0.001,ASAQ,z 分数 = 6.64,p < 0.001 和对照组,z 分数 = 5.85,p < 0.001)。在所有访视中,对照组和 ASAQ 组对任何测试抗原的识别均无差异。然而,在 DP 组中,干预期期间 IPTsc 不会削弱针对 MSP1、MSP3、CIDRa1.1、CIDRa1.4 和 CIDRa1.5 的抗体,但会削弱针对 GLURP-R2 的抗体。
间日疟原虫枯草杆菌蛋白酶样药物靶标 SUB1 的 3D 结构揭示了构象变化以适应底物衍生的-酮酰胺抑制剂
多重耐药性疟原虫的不断选择和繁殖要求我们鉴定出参与尚未被靶向的代谢途径的新的抗疟药物候选物。枯草杆菌蛋白酶样 1(SUB1)属于新一代药物靶点,因为它在寄生虫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从受感染的宿主细胞中逃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B1 的特点是具有一个不寻常的脯氨酸区域,该区域与其同源催化结构域紧密相互作用,因此无法对酶-抑制剂复合物进行 3D 结构分析。在本研究中,为了克服这一限制,采用严格的离子条件和控制重组全长间日疟原虫 SUB1 的蛋白水解,以获得没有脯氨酸区域的活性稳定催化结构域 (PvS1 Cat) 晶体。 PvS1 Cat 的高分辨率 3D 结构(单独存在以及与-酮酰胺底物衍生的抑制剂 (MAM-117) 复合存在)表明,正如预期的那样,SUB1 的催化丝氨酸与抑制剂的-酮基形成共价键。氢键和疏水相互作用网络使复合物稳定,包括抑制剂的 P1 0 和 P2 0 位置,尽管 P 0 残基在确定枯草杆菌蛋白酶的底物特异性方面通常不太重要。此外,当与底物衍生的肽模拟抑制剂结合时,SUB1 的催化槽会发生显著的结构变化,尤其是在其 S4 口袋中。这些发现为未来设计优化的 SUB1 特异性抑制剂的策略铺平了道路,这些抑制剂可能定义一类新的抗疟候选药物。
在爱泼斯坦-巴尔病毒 (EBV) 合并感染的情况下对间日疟原虫的抗体反应:亚马逊雨林的 14 年跟踪研究
1 Rene´ Rachou 研究所,Fiocruz Minas,Oswaldo Cruz 基金会 (Fiocruz),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州,巴西,2 微生物学系,病毒实验室,生物科学研究所,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UFMG),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州,巴西,3 病理学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中心,荷兰,4 全球卫生和跨学科疾病研究中心,公共卫生学院,南佛罗里达大学,佛罗里达州坦帕,美国,5 Leonidas & Maria Deane 研究所,Fiocruz Amazonia,Oswaldo Cruz 基金会,马瑙斯,亚马逊州,巴西,6 Dr. Heitor Vieira Dourado 热带医学基金会,Carlos Borborema 临床研究中心,马瑙斯,亚马逊州,巴西, 7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库亚巴马托格罗索联邦大学 (UFMT) 医学院胡里奥·穆勒大学医院
溴结构域因子 5 作为抗利什曼原虫药物研发的靶点
摘要:利什曼病是由利什曼属的动基体寄生虫引起的一组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目前的化疗非常有限,对新型抗利什曼病药物的需求在国际上具有迫切的重要性。溴结构域是表观遗传读取结构域,已显示出对癌症治疗的良好治疗潜力,并且也可能成为治疗寄生虫病的有吸引力的靶点。在这里,我们研究了杜氏利什曼原虫溴结构域因子 5 (Ld BDF5) 作为抗利什曼病药物研发的靶点。Ld BDF5 在 N 端串联重复序列中包含一对溴结构域 (BD5.1 和 BD5.2)。我们纯化了杜氏利什曼原虫 BDF5 的重组溴结构域,并通过 X 射线晶体学确定了 BD5.2 的结构。使用组蛋白肽微阵列和荧光偏振分析,我们确定了 Ld BDF5 溴结构域与源自组蛋白 H2B 和 H4 的乙酰化肽的结合相互作用。在包括热位移分析、荧光偏振和 NMR 在内的正交生物物理分析中,我们表明 BDF5 溴结构域与人类溴结构域抑制剂 SGC − CBP30、溴孢菌素和 I-BRD9 结合;此外,SGC − CBP30 在细胞活力分析中表现出对利什曼原虫前鞭毛体的活性。这些发现证明了 BDF5 作为利什曼原虫的潜在药物靶点的潜力,并为未来开发针对这种表观遗传读取蛋白的优化抗利什曼原虫化合物奠定了基础。关键词:利什曼原虫、溴结构域、表观遗传学、药物发现、结构生物学
一种针对疟疾病原体恶性疟原虫的溴结构域PFBDP1的新型抑制剂
疟疾中耐药性的兴起需要探索新颖的治疗策略。靶向表观遗传途径可以开放新的有前途的治疗途径。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关注PF BDP1,这是恶性疟原虫中必不可少的溴脱域蛋白。 利用泛选择性溴结构域抑制剂MPM6,我们确定了有效的初始命中率,然后将其开发到纳摩尔粘合剂中。 通过虚拟对接,等温滴定量热法和X射线晶体学的结合,我们阐明了新抑制剂与PF BD1的分子相互作用。 我们的发现包括PF BD1和PV BD1与这些抑制剂的第一个共晶结构,提供了对其结合机制的见解。 使用PF BDP1在恶性疟原虫中的有条件敲低的进一步验证表现出对抑制剂的寄生虫敏感性,强调了其作为针对疟疾的靶向治疗方法的潜力。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关注PF BDP1,这是恶性疟原虫中必不可少的溴脱域蛋白。利用泛选择性溴结构域抑制剂MPM6,我们确定了有效的初始命中率,然后将其开发到纳摩尔粘合剂中。通过虚拟对接,等温滴定量热法和X射线晶体学的结合,我们阐明了新抑制剂与PF BD1的分子相互作用。我们的发现包括PF BD1和PV BD1与这些抑制剂的第一个共晶结构,提供了对其结合机制的见解。使用PF BDP1在恶性疟原虫中的有条件敲低的进一步验证表现出对抑制剂的寄生虫敏感性,强调了其作为针对疟疾的靶向治疗方法的潜力。
2b 期临床研究评估 RTS,S/AS01E 对接受抗疟化学预防药物治疗的接触恶性疟原虫的肯尼亚成年人的疗效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许可不得重复使用。 (未经同行评审认证)是作者/资助者,他已授予 medRxiv 永久展示预印本的许可。此预印本的版权所有者此版本于 2025 年 1 月 12 日发布。;https://doi.org/10.1101/2025.01.10.25320353 doi:medRxiv preprint
Moumaris M. 疟原虫的细胞器适应性:疟疾治疗的目标。Int J Zoo Animal Biol 2025, 8(1): 000640。
在脊椎动物和蚊子的生命周期中,支持疟原虫疟原虫生存的一些细胞器适应性包括内质网、线粒体和顶质体。这种高度展开的内质网支持高蛋白质合成,从而促进寄生虫的快速生长和复制。线粒体在这种寄生虫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能量产生和调节新陈代谢。顶质体是来自红藻来源的次级共生的残留质体,对脂质合成、异戊二烯生产和脂肪酸延长至关重要。提供必需的、宿主无法获得的代谢物。对这些细胞器的研究可能会带来针对疟疾等疾病的新疗法,并有助于解决全球健康问题。
比较3D恶性疟原虫配子细胞的超微结构
尽管疟疾人寄生虫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但其超微结构的一些基本特征仍然晦涩难懂。在这里,我们采用高分辨率体积电子显微镜检查和比较了恶性疟原虫的可传染性男性和女性性血统的超微结构,以及更深入研究的无性血液阶段,重新审视了3D中先前描述的现象。这样做,我们通过示例在配子细胞中表现出多个线粒体的存在来挑战单个线粒体的广泛接受概念。我们还提供了配子细胞特异性细胞抑制剂或细胞口的证据。此外,我们生成了寄生虫内质网(ER)和高尔基体设备的第一个3D重建,以及在感染的红细胞中诱导的配子细胞诱导的外质结构。评估细胞器之间的互连性,我们发现了细胞核,线粒体和apicoplast之间的频繁结构作用。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ER是与众多细胞器和配子细胞的三叶骨膜的混杂相互作用。这些体积电子显微镜资源的公共可用性将有助于其他具有不同研究问题和专业知识的其他人的重新介入。总的来说,我们以纳米尺度重建了恶性疟原虫配子细胞的3D超微结构,并阐明了这些致命的寄生虫的独特细胞器生物学。
布基纳法索首次产前保健孕妇中恶性疟原虫感染的相关风险因素
1 布基纳法索中西部地区理事会生物医学部卫生科学研究所,BP 18 Nanoro; berengerkabore@yahoo.fr(BK); rouambatoussaint@gmail.com (土耳其); hamidou_ilboudo@hotmail.com(夏威夷); palponet@yahoo.fr(波兰); halidoutinto@gmail.com (HT)2 纳诺罗临床研究部门,BP 18 纳诺罗,布基纳法索; meli.sougue@gmail.com(MMHTS); nadege.zoma@yahoo.fr(新西兰); kazienga_adama@yahoo.fr (AK)3 Tengandogo 教学医院,CMS 104,BP 11 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 dantola.kain@ujkz.bf 4 ISGlobal,巴塞罗那大学医院,08036 巴塞罗那,西班牙; quique.bassat@isglobal.org 5 Manhiça 健康研究中心 (CISM),92 Avenida Cahora Bassa,马普托,莫桑比克 6 ICREA,Pg. Lluís Companys 23, 08010 巴塞罗那,西班牙 7 巴塞罗那大学 Sant Joan de Déu 医院儿科,Passeig Sant Joan de Déu 2, 08950 Esplugues,巴塞罗那,西班牙 8 CIBER de Epidemiología y Salud Pública III,Instituto de Salud,28, 101. 29 马德里,西班牙 * 通讯作者:marctahita@yahoo.fr;电话:+226-78809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