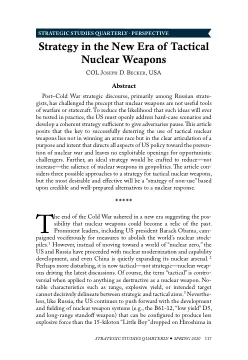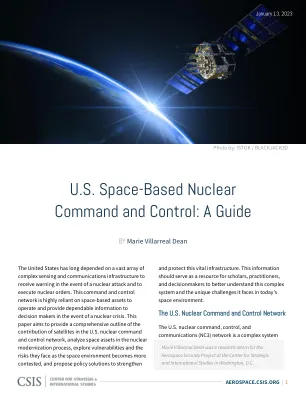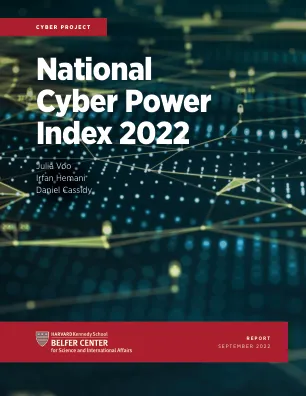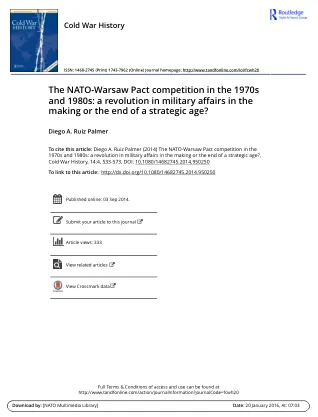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行星保护:监管的新发射台......
外层空间条约通过解决冷战问题、促进外层空间利用的和平合作以及防止潜在的核战争,实现了其规范外层空间法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条约继续关注这些问题。1967 年,大会制定了《营救宇航员、送回宇航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营救协定》)。20《营救协定》详细阐述了外层空间条约第五条,该条要求各国互相协助营救遇险宇航员并回收空间物体并将其送回各自国家。21 后来在 1972 年,联合国制定了《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条约(《责任公约》)。22《责任公约》扩大了外层空间条约第七条,关于各国对其自身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责任。 23 1976 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登记公约》)生效,要求各国向联合国登记并提供有关其在外层空间的物体的信息。
[研究笔记]人工智能技术对核威慑的影响
4 Rafael Loss 和 Joseph Johnson,“人工智能会危及核威慑吗?”War on the Rocks,2019 年 9 月 19 日,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9/will-artificial-intelligence-imperil-nuclear-deterrence/。5 Michael C. Horowitz、Paul Scharre 和 Alexander Velez-Green,“稳定的核未来?自主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影响,”ArXiv.org,2019 年 12 月,第 2 页,https://arxiv.org/ftp/arxiv /papers/1912/1912.05291.pdf 6 Edward Geist 和 Andrew J. Lohn,“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核战争风险?“兰德公司,2018 年,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200/PE296/RAND _PE296.pdf。7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和核风险的影响,第一卷:欧洲-大西洋视角”,编辑。Vincent Boulanin,2019 年 5 月,https://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5/sipri1905-ai-strategic-stability-nuclear-risk.pdf。
摆脱核优势边缘政策理论
本文评估了马修·克洛尼格提出的核优势边缘政策理论,通过历史证据和战略分析强调了其致命缺陷。本文强调,由于美国传统上追求技术发展而没有一个连贯的战略,即所谓的“引导”,重新引发不可持续的军备竞赛的风险。在评估有限核战争的不切实际性和安全的二次打击能力的重要性后,本文主张建立一种现代美国核威慑力量,这种力量以先进核系统的平衡力量为基础,辅以强大的常规能力和基础设施。将可信的威慑优先于威慑力,符合国家利益,并降低了意外核冲突的风险。鉴于其高昂的成本和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追求克洛尼格有缺陷的理论被认为是指导美国核战略的不明智之举。
新时代的战术核武器战略
冷战后的战略话语,主要是俄罗斯战略家们的话语,挑战了“核武器不是有用的战争或治国工具”这一原则。为了降低这种想法在实践中被检验的可能性,美国必须公开应对棘手的情况,并制定一个足以让对手犹豫不决的连贯战略。本文认为,成功阻止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关键不在于赢得军备竞赛,而在于明确表达一种目的和意图,即引导美国政策的所有方面防止核战争,不给机会主义挑战者留下任何可利用的机会。此外,理想的战略应该是制定一种降低(而不是增加)核武器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的战略。本文考虑了三种可能的战术核武器战略方法,但最可取和最有效的将是一种基于可靠且准备充分的核反应替代方案的“不使用战略”。
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避免与中俄联盟开战
自肯尼迪和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末日的前景……如果事情真的按照现在的发展方向发展,我们就面临着使用核武器的直接威胁。”然后他补充说,“[普京]在谈到使用核武器时并不是在开玩笑”,以回应最近乌克兰战场上的胜利,这默认了核战争的风险在过去六十年中从未如此高过。“我认为,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能力,即轻松使用战术核武器而不以世界末日告终。”拜登随后承认,政府的政策并没有给普京一个结束战争的外交选择,他沉思道,“我们正在试图弄清楚:普京的出口是什么?他在哪里下车?他在哪里找到出路?他在哪里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境地——不仅丢了面子,而且在俄罗斯失去了重大权力?” 拜登后来被问及他是否计划与普京会面以缓和美国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他回答说:“我认为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与他会面”,似乎在驳斥他私下警告过的核大决战威胁。
美国天基核指挥与控制: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AEHF 服务的纬度位于北纬 65 度和南纬 65 度以内,覆盖从北极圈底部到南极洲北部的所有地区。AEHF 通信还与特定盟友和合作伙伴共享。在整个核战争期间,AEHF 为总统、高级国家安全领导人以及军事战术和战略部队提供有保障的通信。9 AEHF 是少数几个公开承认的可以传输行政授权命令的途径之一。AEHF 星座为陆、空、海战;特种作战;战略核作战;战略防御;战区导弹防御;以及太空作战和情报提供支持。10 六颗老化的 MILSTAR 卫星,其中第一颗于 1994 年发射,11 此后由较新的 AEHF 星座补充,目前已退役并远离地球静止飞机。 12 最后的 AEHF 有效载荷于 2020 年 3 月作为太空军的首次任务发射,六颗卫星的计划总成本为 150 亿美元。13
2022 年国家网络实力指数 - 贝尔弗中心
四十年前,一群由哈佛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应对冷战期间最大的威胁:苏联和美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担忧。今天,我们寻求重塑这种跨学科方法来应对新的威胁:网络空间冲突的风险。当今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十分重大且多样:如何保护国家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免受网络攻击;如何组织、训练和装备军队,以在未来发生网络冲突时取得胜利;如何阻止民族国家和恐怖分子对手在网络空间发动攻击;如何在发生网络冲突时控制升级;以及如何利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减少国家攻击面,同时又不扼杀创新。这些只是推动我们工作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贝尔弗中心网络项目的目标是成为对这些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严格且政策相关的研究的首要场所。
库尔斯克 1943 - ZMSBw
作为封面图片!红军士兵紧密聚集在 T-34 坦克后方发起攻击。他们面前是一片无法穿透的黑色烟雾,见证着炮弹造成的巨大破坏。所有这些都是彩色的!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些图像,它们并非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记录了俄罗斯联邦对其邻国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惨状。这让我心中产生了疑问:鉴于俄罗斯的战争罪行,是否可以展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此突出提到的军队士兵?编辑们非常有意选择了这张图片。它应该像一个绊脚石,让我们停下来。问题不断出现:如何才能防止欧洲发生战争,从而确保未来与俄罗斯的和平不会带来新的冲突?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来防止乌克兰战争升级到核战争水平?当前交战双方的战争有何特点?坦克是否再次成为焦点,就像封面图片所取的库尔斯克坦克战一样?那么德国联邦国防军又如何呢?她对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吗?它还能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吗?军事史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但它也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军事历史》本期的文章。《历史教育杂志》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马蒂亚斯·彼得展示了冷战期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漫长而有时艰难的谈判过程如何成功建立东西方之间的信任。克劳斯·施托克曼 (Klaus Storkmann) 在重现 1983 年秋季事件时表明,危险情况仍然可能出现。当时,世界濒临核战争,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判断失误。阅读罗曼·托佩尔(Roman Töppel)的《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误判在战争中很常见。与当时的对比也显示出,现代战争形象自那时起已经扩大了多少。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作战准备不佳,与其注重国际危机管理有很大关系。托尔斯滕·科诺普卡 (Torsten Konopka) 在其文章《德国联邦国防军在索马里》中描述了德国如何从早期就希望将其军事行动限制在人道主义任务上。感谢您关注本期内容,希望您能喜欢。
20世纪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北约-华约竞争
1 Dima Adamsky,“中央战线的概念性战役:空地一体战与苏联军事技术革命”,《欧洲缓和危机:从赫尔辛基到戈尔巴乔夫,1975-1985》,Leopoldo Nuti 主编(伦敦:劳特利奇,2009 年),第 150-162 页;Dima Adamsky,“透过镜子:苏联军事技术革命和美国军事革命”,《战略研究杂志》第 31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第 257-294 页;Dima Adamsky,“军事创新文化:文化因素对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革命的影响”(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Gordon S. Barrass,《大冷战:镜厅之旅》(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 年);Gordon S. Barrass,“美国战略的复兴与大冷战的结束”,《军事评论》,2010 年 1 月至 2 月:101-110;Beatrice Heuser,“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华沙条约组织军事理论:东德档案中的发现”,《比较战略》第 13 卷,第 4 期(1993 年):437-457;Beatrice Heuser,“核战争中的胜利:
介绍“人工智能及其不满”
弗洛伊德(1961)曾有句名言:文明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人类免遭苦难,但矛盾的是,它却是不幸的一大根源。同样,人工智能既被吹捧为人类最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又被谴责为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许多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如果不是核战争、气候灾难或另一场全球流行病,那么预示世界末日的将是“超级智能”机器(Barrat 2013;Bostrom 2014;Clark 2014;Yampolskiy 2015;Müller 2016;Cava 2018;Russell 2019)。也可能不是。其他人工智能倡导者声称,新一轮的道德发展将迎来“良好人工智能社会”(Floridi 等人2018),摆脱稀缺和纷争,从而将西方带入目的论的顶峰,正如日本技术专家 Akihito Kodama(2016)所说:重返伊甸园——无需工作就能获得富足,生活没有痛苦——尽管数字化了(Hilton 1964;Noble 1999;Geraci 2010;Diamandis 和 Kotler 2012)。


![[研究笔记]人工智能技术对核威慑的影响](/simg/7\75900a8296f391c1610166ba52d9e4792871020c.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