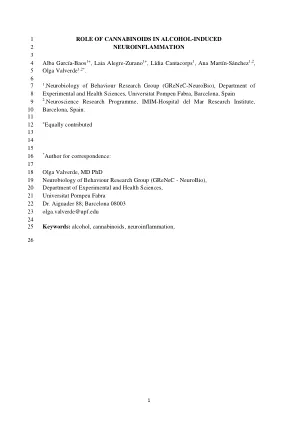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drmy1通过维持细胞分裂素1
。cc-by-nc-nd 4.0国际许可证未通过同行评审获得证明)是作者/资助者,他已授予Biorxiv授予Biorxiv的许可,以永久显示预印本。它是此预印本的版权持有人(该版本发布于5月29日,2024年。; https://doi.org/10.1101/2023.04.04.07.536060 doi:biorxiv Preprint
大麻素在酒精诱导的
AEA N-arachidonoylethanolamine or anandamide AP-1 Activator protein 1 BBB Blood-brain barrier BDN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cAMP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CB1 Cannabinoid receptor 1 CB2 Cannabinoid receptor 2 CBD Cannabidiol CBDA Cannabidiolic acid CBG Cannabigerol CBGV Cannabigivarin CN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OX-2 Cyclooxigenase-2 DAGL Diacylglycerol lipase DAMPs Danger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eCB Endocannabinoid ECS Endocannabinoid system ERK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FAAH Fatty acid amide hydrolase GFAP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PCR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HMGB1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PC Hippocampus Iba1 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or molecule 1 IL Interleukin INF-γ Interferon gamma iNOS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κBα Inhibitory kappa Bα LPS Lipopolysaccharide MAGL Monoacylglycerol lipase MCP-1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1 MCSF Macrophage刺激因子MD2粒细胞分化蛋白-2 MHCII主要组织相容性复杂II MIP-1α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miRNA MicroRNA MRNA MIRNA MRF-1小胶质细胞反应因子1 MyD88髓样分化因子88与2个相关因子2 NF-κB核因子-kappa b oeA乙醇酰胺
针对内源性大麻素系统
1 希腊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特里安大学医学院莱科综合医院预防外科第二系,雅典,希腊;2 希腊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特里安大学医学院 NS Christeas 实验外科和外科研究实验室,雅典,希腊;3 希腊雅典莱科综合医院肾移植科;4 希腊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特里安大学医学院莱科综合医院预防内科第一系,雅典,希腊;5 希腊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特里安大学基菲夏 Agioi Anargyroi 综合肿瘤医院内科学术系 - 内分泌科;6 希腊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特里安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分子肿瘤科;7 希腊雅典莱科综合医院肺病学系;8 希腊雅典 Sotiria 医院肺病学第二系; 9 雅典国立卡波季斯特里亚大学医学院莱科总医院第一外科,希腊雅典; 10 西班牙卡塔赫纳圣卢西亚大学医院内分泌和营养科; 11 西阿提卡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希腊雅典; 12 雅典国立卡波季斯特里亚大学,雅典,希腊
大麻素的好处和风险
早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就可以在中国药物中找到有关大麻药用使用的最早著作,证明了大麻是唾液,甚至在Phar-Macological进展之前也被视为Medicina l。尽管大麻的治疗作用是SAT IVA,以超过两个mil-lennia而闻名,但大约20年前,这种Intere ST引发了使大麻广泛使用的原因,可用于多种多样。在1980年,发现了大麻的抗震颤性质,但是,直到1985年,药理学伙伴才被批准,开始合成Delta-9-9-THC准备疗法的准备。这些制剂是Dronabi-Nol,nabilone,sativex和Epidi-Olex(源自CBD),可以从中得出治疗益处。
酒精和大麻素共同使用
酒精和大麻是孕妇最消耗的精神活性物质之一,并且独立于此,两种物质都与终身对胎儿神经发育的影响有关。重要的是,育龄年龄的个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同时酒精和大麻素(SAC)的使用,这会扩大每种药物的药物动力学作用,并增加对这两种物质的渴望。迄今为止,对人类和非人类流行的调查,对产前多层的使用均受到限制。在本综述的论文中,我们将直接和产前接触这些物质的联合暴露,并从单次暴露范式中确定共享的产前靶标的目前已知,这些范围可能突出显示易感神经生物学机制,以实现未来的研究和治疗干预。最后,我们通过讨论我们认为对未来临床前SAC研究的考虑和实验设计至关重要的因素来结束这一手稿。
胰岛素抵抗的实验室检查
摘要 胰岛素抵抗是一种代谢疾病,其特征是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受损,胰岛素在葡萄糖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疾病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例如 2 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本研究评估了检测胰岛素抵抗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包括高胰岛素正常血糖钳(HIEC)等直接方法和HOMA-IR、QUICKI和TyG指数等间接方法。直接方法可以提供高度准确的结果,但需要复杂的设施和程序,而间接方法则可以提供一种具有良好预测水平的实用替代方法。此外,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替代指标如脂联素和瘦素也在不断开发,以提高诊断效率。本研究强调了根据临床或研究需要选择正确的方法以更有效地检测胰岛素抵抗的重要性。胰岛素抵抗是一种代谢疾病,其特征是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受损,胰岛素在葡萄糖代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疾病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包括 2 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本研究评估了检测胰岛素抵抗的实验室方法,包括高胰岛素正常血糖钳 (HIEC) 等直接方法和 HOMA-IR、QUICKI 和 TyG 指数等间接方法。直接方法可以提供高度准确的结果,但需要复杂的设施和程序,而间接方法可以提供具有良好预测能力的实用替代方法。此外,基于脂联素和瘦素等生物标志物的替代指标也在不断被开发,以提高诊断效率。这项研究强调了选择适合临床或研究需要的方法以更有效地检测胰岛素抵抗的重要性。这是一篇根据 CC BY-SA 许可协议开放获取的文章。这是一篇根据 CC BY-SA 许可协议开放获取的文章。介绍
纳曲酮/安非他酮 (Contrave®) 用于治疗肥胖症
简介肥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神经行为疾病,具有遗传 1-3 或表观遗传 4,5 基础。肥胖会增加患几种慢性疾病(包括 2 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6 肥胖的遗传基础解释了为什么强大的生理机制会坚决保护体重。要了解身体如何保护体重,首先必须了解体重是如何调节的。体重由下丘脑控制。在下丘脑的弓状核中,有两种类型的神经元。一种类型表达神经肽 Y (NPY) 和刺鼠相关蛋白 (AgRP),它们都会刺激饥饿感。另一种类型的神经元表达促阿片黑素皮质素 (POMC)(从中裂解出 α 黑素细胞刺激激素 [α MSH])以及可卡因和苯丙胺调节转录本 (CART)。 α MSH 和 CART 均能抑制饥饿感。在一天中的任何特定时间,这些神经元的活动决定了我们是否想吃东西。那么问题是什么控制着这些弓状核神经元的活动呢?弓状核有许多输入,包括来自位于脑干的孤束核、愉悦通路和皮质。此外,十种循环激素也会影响这些特定神经元的活动,从而调节食物摄入量。这些激素来自肠道、胰腺和脂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这些激素中只有一种(生长素释放肽)会刺激饥饿感,而九种(瘦素、胆囊收缩素、肽 YY、胰高血糖素样肽-1、胃泌酸调节素、尿鸟苷素、胰岛素、胰淀素和胰多肽)会抑制饥饿感!肥胖为何会复发? 1994 年发现瘦素后不久,人们发现这种抑制饥饿的激素水平在节食减肥后会急剧下降。7 相反,刺激饥饿的激素生长素释放肽的水平在减肥后会增加。8 随后的研究显示,减肥后餐后胆囊收缩素的水平也会降低。9 这些变化会导致饥饿感增加。2011 年,研究证明其他调节饥饿的激素也会朝着增加饥饿感的方向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是长期的。10 这些反馈回路解释了为什么减肥效果很难长期保持,以及为什么生活方式的建议只能导致适度的减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抑制饥饿的药物对于减肥来说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对于长期维持体重来说也是如此。肥胖症的药物治疗当作为生活方式干预的辅助手段时,减肥药物可以增加实现临床有意义的(≥5%)减肥的可能性,并降低体重反弹的可能性,包括减肥手术后。11 药物治疗比单纯改变生活方式更能达到减肥的效果,并且有利于防止体重反弹。12
血管紧张素受体抑制剂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Myocardi
荟萃分析中总共包括八项临床试验。六项研究分析了Sacubitril/Valsartan和ACEI组合。合并的分析报告说,与单独的ACEI组相比,Sacubitril/Valsartan的低血压风险(相对风险{RR}:1.29 {1.18,1.41})显着增加。此外,与单独使用ACEI相比,使用Sacubitril/valsartan组合后,在使用sacubitril/valsartan组合后,在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中观察到显着增加(RR:3.08 {2.68,4.48})。Furthermo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groups in terms of mortality rate (RR: 0.86 {0.73, 1.02}), the risk of heart failure (RR: 0.62 {0.39, 1.00}), the frequency of recurrent MI (RR: 0.86 {0.27, 2.76}), and the mean difference of 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两组之间的肽(nt-probnp)(加权平均差异{wmd}:-174.36 {-414.18,65.46})。然而,事实证明,Sacubitril/valsartan组合有益于显着降低重大不良心脏事件(MACE)(RR:0.64 {0.48,0.84})和重新解释性化(RR:0.53 {0.53 {0.39,0.71}),与ACEI POST MI相比。另外,在两项研究中报道了Sacubitril/Valsartan和ARB的组合。与单独使用ARB使用相比,Sacubitril/valsartan组合组中MI的NT -ProBNP浓度显着降低(WMD:-71.91 {-138.43,-5.39})。然而,两组之间的LVEF(WMD:0.88 {-5.11,6.87})的改善中没有观察到显着差异。
肥胖相关胰腺导管腺癌
肥胖是全球范围内一个突出的健康问题,直接影响胰腺健康,肥胖者罹患胰腺导管腺癌 (PDAC) 的风险显著增加。有多种因素可能解释 PDAC 发展风险的增加,包括肥胖引起的胰腺内外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的发展、炎症、前期和恶性阶段期间胰腺内免疫抑制的促进、脂肪组织产生的激素水平(脂联素、生长素释放肽和瘦素)的变化,以及获得对胰腺肿瘤发生至关重要的肿瘤发生和抑制蛋白的体细胞突变。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这些肥胖引起的风险因素对 PDAC 发展和进展的广泛影响,重点关注肿瘤微环境 (TME) 内的变化与预防、当前治疗策略以及针对肥胖管理的未来方向与预防胰腺肿瘤发生的关系。
脑转移切除后与术后结节性瘦脑膜疾病有关的基因组改变
目的尚不清楚脑转移切除与结节性瘦脑膜(NLMD)的风险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检查了在脑转移中发现的基因组改变,目的是在临床和治疗因素的背景下确定术后NLMD的变化。方法对2014年至2022年之间切除脑转移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的单中心研究,并提供了临床和基因组数据。术后NLMD是关注的主要终点。在脑转移酶中进行了> 500个癌基因的靶向下一代测序。COX的优势危害分析,以识别与NLMD相关的临床特征和基因组改变。结果该队列包括101例来自多种癌症类型的肿瘤患者。有15例NLMD患者(占队列的14.9%),从手术到NLMD诊断为8.2个月的中位时间。两种经文的机器学习算法始终鉴定出CDKN2A/B代码和ERBB2扩增为所有癌症类型的术后NLMD相关的主要预测因子。In a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analy- sis including clinical factors and genomic alterations observed in the cohort, tumor volume ( × 10 cm 3 ; HR 1.2, 95% CI 1.01–1.5; p = 0.04), CDKN2A/B codeletion (HR 5.3, 95% CI 1.7–16.9; p = 0.004), and ERBB2 amplification (HR 3.9,95%CI 1.1-14.4; P = 0.04)与术后NLMD的时间减少有关。需要其他工作来确定目标治疗是否会在术后环境中降低这种风险。结论除了切除的肿瘤体积增加,ERBB2扩增和CDKN2A/B缺失与多种癌症类型的术后NLMD风险增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