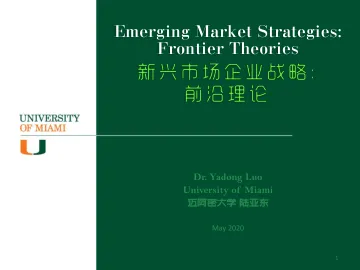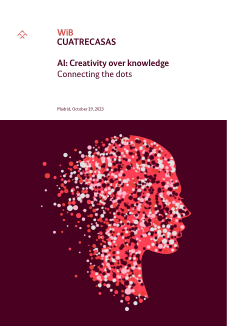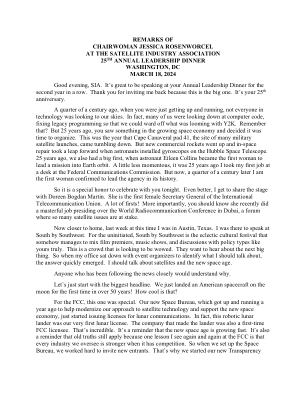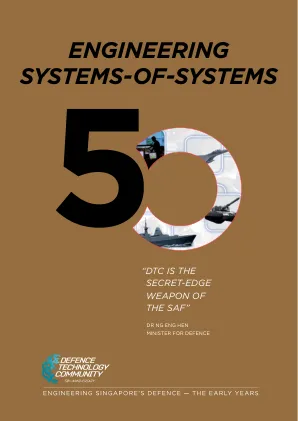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人类系统兴趣社区季刊
总体而言:OSD 创建的 17 个 COI 之一,旨在更好地协调国防部和科技界之间的关键决策。目标:使 COI 成为国防部科技专业知识、领导力和协调的“首选”来源。愿景:开发和提供以人为本的新技术,以量化任务效能,并选择、训练、设计、保护和操作,以显著提高任务效能。使命:通过以下方式提高任务效能:1) 任务训练和实验的综合模拟,2) 任务效能的人机设计,3) 操作员效能评估,4) 在战场压力下操作,5) 掌握 PMESII 战场。主要产品:1) 综合 OSD 和服务路线图,2) COI 分类法、预算和计划,3) COI 合作机会、成就和能力影响。数据链接:有关 COI 的关键信息可在 Marketplace 网站上找到:http://www.defenseinnovationmarketplace.mil/coi.html
投资管理人工智能的现状
2022 年 11 月,OpenAI 发布 ChatGPT,在全球公众、媒体和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 (AI) 热潮。这种生成式 AI 模型(也称为生成式大型语言模型或 LLM)在科技界引发了一场关于谁拥有最佳 AI 产品的新竞赛。一方面,微软与 OpenAI 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将生成式 AI 融入众多应用中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谷歌等其他大公司则以 BARD 的形式加紧推出自己的 AI 技术。最近,诸如 Meta 的 Llama 之类的生成式 AI 的开源版本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们使最终用户能够为自己的特定应用微调生成式 AI,而无需从头开始训练生成式 AI 所需的大量成本和数据。
Signed-International-ST-Engagement-Strategy.pdf
自 2014 年发布上一份此类战略2 以来,国防部见证了重大变化。长期战略竞争的重新出现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削弱了美国的军事竞争优势。为了更好地追求技术优势,国防部长办公室(OSD)进行了重组,这是一代人以来技术和采购方面最重大的转型。新任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USD(R&E))和采购与保障(USD(A&S))的副部长现在必须推动创新,加速作战能力的进步,以比以往更快、更经济的方式向作战人员提供成熟的技术。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国防科技界必须紧跟世界各地新兴科技的发展,利用他人的投资,并积极寻求前沿研究合作。
与 Peter Thiel 一起做出选择的时刻(已完成 2022 年 12 月 15 日......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是科技界为数不多的直言不讳的政治人物之一,支持保守派和自由派候选人。因此,当我们继续讨论共和党的未来时,他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且可能与我们之前听到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他可能比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更清楚地预见未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技术将如何塑造它,以及我们的政治可以且必须如何回应。但他今晚来到这里是为了回答我们向迈克·彭斯、汤姆·科顿、尼基·黑利、迈克·蓬佩奥等人提出的同样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在共和党时代,共有 11 人响应了我们的号召,选择共和党应该代表什么?共和党会回顾过去,还是像罗纳德·里根一样展望未来?它应该优先考虑原则还是党派之争?
人工智能:创造力胜过知识
Cristina 是不同公共和私人机构的技术和多样性顾问。她是西班牙政府经济事务和数字化转型部西班牙语自然语言处理专家委员会和 Red.es 性别办公室的成员,并领导阿拉贡政府智库 Covid19 的技术领域。2018 年 10 月,她被《Business Insider》评为 Twitter 上值得关注的 30 位西班牙科技界人士之一,并被选为 100 强女性之一。2019 年,《Emprendedores》杂志将她评为西班牙 9 位最具影响力的年轻企业家之一,2020 年 12 月,《Merca2》杂志将她评为西班牙数字领域 20 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是 TEDxZaragoza2018 和 BBVA 节目“Aprendemos Juntos”的演讲者。
面向未来:迈向量子安全之旅
如今,量子计算可以说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没有人能保证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能制造出通用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但研究实验室——以及越来越多的科技界私营公司——每天都在突破障碍,在科学前沿进行创新。而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可以解决目前任何(传统)超级计算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卖家和用户都在冒险尝试这种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标普资本 IP Pro 的数据显示(图 1),量子初创公司在过去十年中获得了 24 亿美元的投资。2021 年是兴趣大增的一年,量子公司获得了 11 亿美元的投资。而且这些数据还不包括 IBM、亚马逊、谷歌和霍尼韦尔等老牌 IT 公司的巨额投资。
杰西卡·罗森沃塞尔主席在 2024 年 3 月 18 日于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卫星行业协会第 25 届年度领导力晚宴上的致辞
25 年前,当你们刚刚起步时,并不是所有科技界人士都在关注太空。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低头研究计算机代码,修复遗留程序,以便能够避免迫在眉睫的千年虫问题。还记得吗?但 25 年前,你们看到了不断发展的太空经济的一些东西,并决定是时候组织起来了。这一年,卡纳维拉尔角 41 号发射台,许多军用卫星的发射场,摇摇欲坠。但新的商用火箭升空,当宇航员在哈勃太空望远镜上安装陀螺仪时,太空维修取得了飞跃。25 年前,我们还创造了一个重大的第一次,宇航员艾琳·柯林斯成为第一位领导地球轨道飞行器的女性。25 年前,我接受了第一份联邦通信委员会办公桌上的工作,这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但现在,25 年过去了,我是该机构历史上第一位被确认领导的女性。
迈向新的设计理念
2. 激进的视角 2.1 共同的理解 Nicenboim、Giaccardi 和 Redström 的论文“从对人工智能的解释到共同的理解”开篇明确地阐明了我们在将人工智能定位于日常生活中时所谈论的内容,即在不断变化的使用环境、不断变化的价值观以及人与人工智能体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中。作者认为,设计与人工智能系统的包容性和可持续交互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支持人们理解它们并在情境中与它们建立联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至关重要的是将人和人工智能体都视为建构和分享情境化和动态理解的积极参与者。这需要审查科技界可解释人工智能议程背后的假设,并寻求可以帮助我们“跨越”人工智能系统的复杂性(如 Ananny 和 Crawford,2018 年所建议)并“解决”其故障和崩溃的设计策略。
冷战期间印度人才流失到美国
冷战时期印度为何能培养出如此多的高技能人才?为何有一部分“人才外流”到美国?冷战时期,美国民间基金会和大学与美国政府合作,制定了以产学官合作为基础的系统性技术援助政策。其外交意图也在于将一直保持不结盟中立的印度拉入西方阵营。美国的技术援助促成了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有“印度的MIT”)的成立,印度科技人才的培养工作顺利进行。然而,印度并不具备吸纳此类高技能人才的工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防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却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源短缺。冷战时期,随着与苏联的竞争愈演愈烈,吸引国内外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变得至关重要。美印两国高级人才供需不平衡,加之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导致大量印度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科技界。
工程系统的系统
新加坡国防科技界 (DTC) 的发展历程与新加坡武装部队 (SAF) 的发展历程相似,两者相互依存,不断迭代,相互借鉴。两个领域的先驱者很早就意识到,新加坡是一个地理纵深有限、人力有限的小岛国,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毫不气馁,决心通过坚定的意志、承诺和利用技术的力量,减轻新加坡的脆弱性和制约因素,建立一支可靠的新加坡武装部队。用吴庆瑞博士的话来说,“我们必须用新技术来补充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人力,因为人力限制永远存在。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技术而不是人力。而且我们必须在本土开发这种技术优势。”尽管这些理想很有价值而且很重要,但对于 DTC 来说,这是一段艰苦的旅程。新加坡的普通教育水平很差,更不用说工程师或科学家了,新加坡如何能发展这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