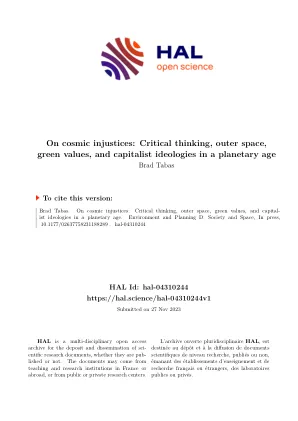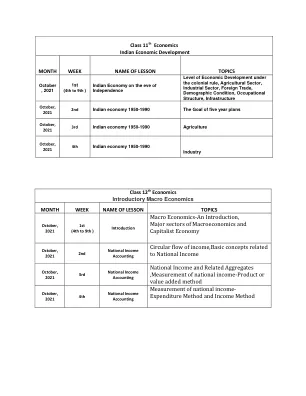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解决资本主义的好工作问题 | 丹尼·罗德里克
摘要 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以教育、培训、累进税制和社会保险为中心,不足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包容性挑战。我们提出了一项直接针对经济生产领域的战略,旨在增加“好工作”的供应。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i)与雇主相关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ii)直接针对创造好工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iii)激励劳动友好型技术的创新政策;(iv)促进维持高国内劳动/社会标准的国际经济政策。这些要素既通过其目标(扩大好工作的数量)联系在一起,也通过一种新的监管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是协作和迭代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和规定性的。我们强调新的制度安排的重要性,这些安排使政府和企业之间能够进行战略性的长期信息交流和合作。关键词:好工作、福利国家、改革资本主义 JEL 分类:D60、F13、H10、H20
模糊性的终结:技术认识论、监控资本主义和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摘要 2022 年,人工智能 (AI) 渗透到人类社会,而理解其某些方面的工作方式却异常困难。有一项运动——可解释人工智能 (XAI)——旨在开发新方法来解释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我们旨在强调 XAI 的一个重要哲学意义——它在消除模糊性方面发挥着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请考虑在被称为监视资本主义的领域中使用人工智能,这已使人类迅速获得了识别和分类大多数使用语言场合的能力。我们表明,这种信息的可知性与某种模糊性理论——认识论——对模糊性的说法是不相容的。我们认为,认识论者应对这一威胁的一种方式是声称这一过程带来了模糊性的终结。然而,我们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认识论是错误的,但还有一种较弱的学说,我们称之为技术认识论,即认为模糊性是由于对语言用法的无知造成的,但这种无知是可以克服的。这个想法是,了解更多相关数据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更自信、更准确地了解单词和句子的语义值。最后,我们认为,除非所涉及的人工智能能够用人类可以理解的术语来解释,否则人类可能不会相信未来的人工智能算法告诉我们关于模糊词语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要接受人工智能可以告诉他们词语含义的明确界限,那么它就必须是可理解人工智能。
宇宙不公正:批判性思维,外太空,绿色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摘要似乎很明显,社会正义的利益应始终与有限地球上的环境正义保持一致。不幸的是,即使在人类世,这在实践中也是如此。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映射,以表明意识形态上充电的过程如何分裂人和星球的兴趣。它对行星保护的争论如何将其变成宽广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倒数)提供了务实,语义和空间分析。因此,它提出了对整体理论的隐性批评。努力展示社会的基本统一和环境风险,整体思维使批评家的关键工具箱无法区分透明的欺诈性绿色洗涤和科学支持但具有意识形态的责任。本文的重点是人类学意识形态的空间维度。它特别着眼于人类世界经济中外太空的不断增长的位置和修辞功能。它说明,至少在与区域外星空间相抵触这种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了外星生长的承诺,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即以行星福祉的名义证明不平等的方法,以及尽管我们越来越多地为我们的行星限制了限制了生长的福音。
气候危机: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的经济计划的时间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为将民主经济计划作为可行的替代愿景而开放认识论空间。认为,对该想法的适当发展必须在对霸权多维意识形态神秘主义及其市场的全面批判性审讯之前进行。利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见解,该文章识别并分析了一些实现认识论封闭的中心意识形态神秘主义。These range from the obfuscation of capitalism's role in creating the climate crisis as an inherently unsustainable system, to the mystification of its non-evolutionary origins, to the obfuscation of the role economic planning play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 ism, to the mystification of markets as ideal spaces of freedom and innovation obfuscating the ever present market-related oppression, exploitation and environ- mental devastation, and to沉默的民主经济规划的具体史典范,例如Project Cybersyn,应该为想象替代秩序的灵感。关键词:气候变化,意识形态神秘,民主经济计划,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 - ISM
算法政府,Incivil Society和监视资本主义:共同生产的抵制
本文旨在介绍“算法政府”,“ Incivil Society”和“监视资本主义”之间的反思性方法,讨论了融合点和概念差异,并提出了通过共同制度生产的制度产生的抵抗可能性。作为一个假设或研究问题,是否可以将技术社会秩序确定为新自由主义合理性的生殖,以及主观生产共同的替代方案?通过讨论和结果,新自由主义力量的产生是通过算法能力的新技术确定的,在传播语言的仪器化过程中,以使符号机构空间的恢复是通过产生共同的替代品来替代主观机构本身作为替代品的。作为一种方法论路径,它被使用了识别当前社会秩序的临界结构,转化为对其矛盾的分析,并通过普通的制度空间提出了抵抗的可能性,并提出了鉴于算法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新数字反思的建议。
科学传播与开放获取:对资本主义学术出版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资本主义不仅在其内部结构动态上是辩证的和对抗的,资本主义还建立在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辩证法之上。分化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结构本身也创造了破坏资本主义的潜力,即解放的潜力。马克思(1857/58, 853)将这些潜力称为“新历史形式的萌芽”。数字资本主义包含超越自身的潜力。在开放获取领域,我们不仅发现资本主义的开放获取,而且还发现替代的、解放的、非营利的、非资本主义的潜力、项目、期刊、书籍、出版商,它们是未来出版、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形式的萌芽。数字资本主义植根于数字资本和数字公共资源之间的对抗。Manfred Knoche 将这种辩证法分析为资本主义开放获取和解放性开放获取之间的对抗。第二类是少数项目,它们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因此往往难以生存。新萌芽不会自动绽放成成熟的花朵。它们通常会枯萎。经济和社会不会自动发展。
中国的城市人工智能:后智能城市的社会控制还是超资本主义发展?
研究和更广泛的社会辩论探索了人工智能在中国扩大社会控制和超资本主义发展中潜在的变革作用。在本文中,我们利用这些辩论来反思中国的城市人工智能实验。关键问题是,与智慧城市的逻辑和想象相比,人工智能是否提供了独特或不同的东西。对上海和杭州城市人工智能管理标志性地点的分析表明:城市人工智能与智能之间的共鸣和不和谐。但它们也展示了城市人工智能实验的独特而复杂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在社会控制和自由市场应用的人工智能视角中并没有被很好地捕捉到。此外,人工智能正在开展的城市实验环境揭示了创建新“数字帝国”的愿望,探索数据权力的新极限和潜在的社会抵抗。本文通过提供一个新框架来比较新兴人工智能应用背景下计算城市管理的逻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本文为中国城市人工智能管理的未来应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并确定了未来的城市研究重点。
中国城市人工智能:后智慧城市的社会控制还是超资本主义发展?
研究和更广泛的社会辩论已经探索了人工智能在中国扩大社会控制和超资本主义发展中潜在的变革作用。在本文中,我们利用这些辩论来反思中国的城市人工智能实验。关键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提供了与智慧城市理念的逻辑和想象相比独特或不同的东西。对上海和杭州城市人工智能管理的标志性地点的分析表明:城市人工智能和智能之间的共鸣和不和谐。但它们也展示了城市人工智能实验的独特而复杂的景观,这在社会控制和自由市场应用的人工智能视角中并没有被很好地捕捉到。此外,人工智能正在开展的城市实验环境揭示了创建新“数字帝国”的愿望,探索数据权力的新极限和潜在的社会抵抗。本文通过提供一个新框架来比较新兴人工智能应用背景下的计算城市管理逻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该论文为中国城市人工智能管理的未来应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并确定了未来城市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