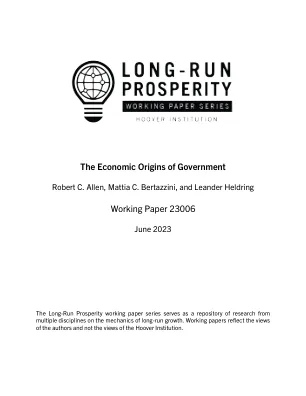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喷气年龄的证据
*第一个版本:2021年2月。自这个项目开始以来,我们感谢克里斯蒂安·海尔维格(Christian Hellwig)的持续支持。我们要感谢Bj�OrnLarsson,他通过与我们分享他的历史飞行时间表来使该项目成为可能。我们感谢Taylor Jaworski和Carl Kitchens与我们共享高速公路数据。本文从Antonin Bergeaud,Davide Cantoni,Thomas Chaney,Fabrice Collard,Ben Faber,Ben Faber,Ruben Gaetani,Victor Gay,Ulrich Hege,Enrico Moretti,Luigi Pascali,Luigi Pascali,Mohamed Saleh,Mark Schankerman,Mark Schankerman,Claudia Steigley,nicemelley,nicemelely,nicemelely,nice nicelely,nice nicelely,nice nicelele,以及伯克利,弗雷伊特,IMF,Insead/coll`欧格·德兰西,山脊增长,rief paris,sed,图卢兹,城市经济协会,是普林斯顿等的众多参加研讨会和会议的参与者。†电子邮件:paulystefan@gmail.com‡奥斯陆大学。通讯作者,电子邮件:fernando.stipanicic@econ.uio.no
吉姆·克劳和奴隶制后的黑人经济进步
* 我们感谢 Leah Boustan、Davide Cantoni、David Card、Raj Chetty、Ellora Derenoncourt、Jeremiah Dittmar、Jonathon Hazell、Richard Hornbeck、Allan Hsiao、Ethan Ilzetzki、Ilyana Kuziemko、Camille Landais、Quan Le、David Lee、Trevon Logan、Ben Moll、Suresh Naidu、Steve Redding、Ricardo Reis、Maarten de Ridder、Bryan Stuart、Chris Walters、Tianyi Wang、Zach Ward 和 Gavin Wright 的深刻评论。我们感谢研讨会和会议参与者分享他们的建议。我们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的三名匿名研究生分享他们的模拟裁判报告。Tre' McMillan、Cynthia Nwankwo 和 Bracklinn Williams 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这项工作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不平等研究计划和工业关系部门的支持。这篇论文之前发表的标题是“奴隶制结束后黑人经济进步的地理”。†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lalthoff@princeton.edu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hareichardt@lse.ac.uk
特刊从教学机器到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机遇与挑战
科学委员会Sanne Akkerman(Utrecht大学)Ottavia Albanese(米兰大学 - 比科卡大学)Susanna Annese(Bari“ Aldo Moro”)Alessandro Antonietti(米兰 - 卡蒂科利亚大学 - 卡特罗斯大学)Pietro Boscolo(Padua) Castelfranchi(ISTC-CNR)Alberto Cattaneo(Sfivet,Lugano)Graziano Cecchinato(帕多亚大学)Carol Chan(香港大学)Cesare Cornoldi(帕多亚大学)Crina Damsa(Oslo)米兰大学 - 比科卡大学)Alberto Fornasari(Bari University of Bari“ Aldo Moro”)Carlo Galimberti(米兰大学 - 卡托利亚大学)Begona Gros(大学巴塞罗那大学 Kai Hakkarainen (赫尔辛基大学) Vincent Hevern (勒莫因学院) Jim Hewitt (多伦多大学) Antonio Iannaccone (纳沙泰尔大学) Liisa Ilomaki (赫尔辛基大学) Sanna Jarvela (奥卢大学) Richard Joiner (巴斯大学) Kristina Kumpulainen (赫尔辛基大学)
黑人死亡之前和之后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我们记录了黑人死亡如何激活政治并导致欧洲的经济差异。在大流行之前,尽管西方的政治分散更大,但东德国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众不同。大流行促成了与政治先前差异相吻合的差异。在大流行,建筑和制造业在东方相对于潜在趋势和西方路径的情况下降了1/3。政治将当地的自治制度化在西方,但不在东方。This divergence is observed across otherwise similar cities along historic borders and foreshadows a subsequent divergence in agriculture Key words: institutions, political economy, structural change, cities, growth JEL: N13, N14, N60, N93, O10, O18, O40, O43, P48 This paper was produced as part of the Centre's Urban and Growth Programmes.经济绩效中心由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我们感谢Beni Atanasov,Jens Aurich,Gavin Greif,Yasmin Le,Erik Paessler,DeníPortl-Ramos,Yannik Sdrenka和Max Willems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帮助。我们感谢Davide Cantoni的讨论以及分享有关城市领土管辖区的证据,Ralf Meisenzahl,Stephane Wolton和Noam Yuchtman发表了有益的评论。Dittmar感谢LSE经济绩效中心的研究支持。
前沿颞前痴呆的早期神经递质变化:一项Genfi研究
Enrico Premi A,1,Martha Pengo B,C,1,Irene Mattili C,Valentina Canton,Youth Dukart和Robert Gasparotti H,Arababella Bouzigues H,David M St. Robert Laforce Jr P,Fermin Moreno。 R. Butler's Pietro, and Johannes Levin a , ai , ai , Markus Otto ak , Isabelle Le Ber an , o , ap , ap , ap , ap , ap , ap , aq , Florence Pasquier , ace , Jonathan D. Rohrer h , Barbara Boronni a , c , * , a Initiative Fronttemporal Genetic (GENFI)
政府工作论文 23006 的经济起源
*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科学学院,萨迪亚特滨海区,阿布扎比,阿联酋。电子邮件:bob.allen@nyu.edu。† 牛津大学经济学系和纳菲尔德学院,10 Manor Road,OX1 3UQ 牛津,英国。电子邮件:mattia.bertazzini@economics.ox.ac.uk。网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mattia-bertazzini ‡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2211 Campus Drive,埃文斯顿,伊利诺伊州 60208,美国。电子邮件:leander.heldring@kellogg.northwestern.edu。网站:www.leanderheldring.com。我们要感谢 Daron Acemoglu、Thilo Albers、Eric Chaney、Davide Cantoni、Steven Cole、Paul Collins、Jonathan Chapman、Joshua Dean、Melissa Dell、James Fenske、Luke Jackson、Noel Johnson、Matthew Lowe、Nathan Nunn、James Robinson、Christopher Roth、Raul Sanchez de la Sierra、Jakob Schneebacher、Andreas Stegmann、Jonathan Weigel、Noam Yuchtman、Roman Andres Zarate 以及 2020 年 ASSA 会议、2022 年 Associazione per La Storia Economica 年会、2022 年巴塞罗那夏季论坛、剑桥 briq 研究所、杜塞尔多夫加拿大高级研究所、格罗宁根经济史协会年会、牛津大学国王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昂、麦吉尔大学、密歇根大学、慕尼黑、西北大学凯洛格分校、巴黎经济学院、蒂尔堡和 2022 年世界经济史研讨会的参与者大会的宝贵意见。我们要感谢 Carrie Hritz 慷慨地与我们分享数据。特别感谢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计划 (CDLI) 的 Jacob Dahl 和 Emilie Page-Perron 在处理 CDLI 数据方面提供的帮助和指导,以及牛津大学东方研究系的 John Melling 在翻译苏美尔语术语方面提供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 Sofia Badini、Adelina Garamow、Dominik Loibner 和 Jaap-Willem Sjoukema 提供的出色研究协助。其余所有错误均由我们自己承担。
太阳能飞机连续飞行的设计(博士论文 - Noth 2008)
这篇论文是我在 Roland Siegwart 教授的自主系统实验室担任研究助理四年的成果。我先是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然后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两所学院是瑞士的两所联邦理工学院。这段时期非常有趣且收获颇丰,我与许多机构进行了合作,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是一种荣幸。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 Roland Siegwart 教授,感谢他给了我撰写这篇论文的绝佳机会,也感谢他的建议、支持和领导,让我们的实验室感觉像一个大家庭。还要感谢论文委员会成员 André Borschberg、Peter Corke 和 Claude Nicollier 对论文的仔细阅读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如果没有 Sky-Sailor 的建造者和飞行员 Walter Engel 的大力帮助,这篇论文不可能完成。我要非常感谢他,因为在这个项目四年的时间里,他教会了我成千上万关于模型飞机的知识。与他一起工作并在艾因西德伦测试我们的飞机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我还要感谢 Samir Bouabdallah,我先是和他一起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然后继续完成博士论文,Daniel Burnier、Janosh Nikolic、Stéphane Michaud、Jean-Christophe Zufferey 以及 EPFL/ETHZ 的 Aero Initiative 的所有人员,感谢他们在飞行机器人和电子设备方面与我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对于他们在控制方面的帮助,我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