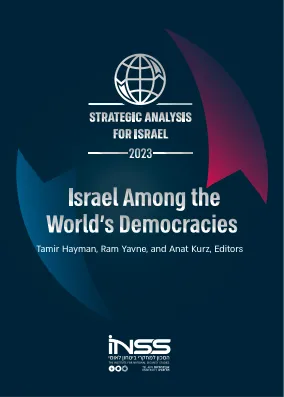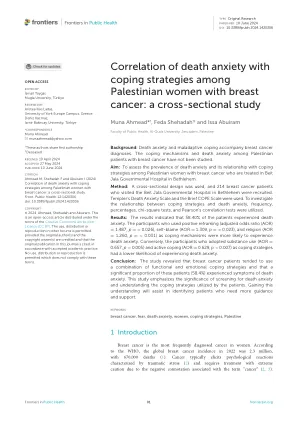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不愿疫苗,心理健康,对covid ...
抽象目的 - 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健康在抑郁,焦虑,压力,对19009的恐惧以及生活质量(QOL)对不愿意在居住在巴勒斯坦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成年人中接种疫苗的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影响。设计/方法/方法 - 作者招募了同意参加该研究的1,122名巴勒斯坦成年人; 722是女性,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0.83(SD 8.8)。抑郁症,焦虑和压力量表(DASS),世界卫生组织QOL-BREF,FCOV-19和不愿疫苗量表;将分层回归分析用于测试疫苗不情愿作为因变量,心理健康,对COVID-19和QOL的恐惧和QOL作为自变量。这项研究假设此类变量对疫苗选择的影响,由于参与者的地理位置而造成差异。发现 - 调查结果显示出心理健康的作用,尤其是抑郁症,质量和恐惧对疫苗不情愿的恐惧,西岸和加沙的抑郁症和对共同的恐惧,而在以色列,QOL在疫苗接种选择中发挥了作用。研究局限性/含义 - 在疫苗犹豫不决以及心理困扰,QoL和对Covid-19的恐惧中,未来需要更彻底地理解未来,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突变和波动。在线招聘可能不允许该研究包括巴勒斯坦人口中最弱势的条纹。社会含义 - 巴勒斯坦医疗保健系统的崩溃加剧了人口中的恐惧感,使他们不太可能接种疫苗。实际意义 - 必须在公共卫生和公共心理健康政策中考虑人权观点,以确保在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的巴勒斯坦人口的质量和福祉。COVID-19的大流行式传播促使全球社区的呼吁积极倡导紧急重新建立公平,自治权和持久性,在被占领地区的医疗基础设施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同等权利。
Tamir Hayman、Ram Yavne 和 Anat Kurz,编辑 - INSS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PA) 继续衰弱,在当地失去控制,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没有明显的继任者或有序移交权力的机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内的真空,加上缺乏政治前景,导致了分散的恐怖袭击浪潮和狮子窝等暴力当地组织的崛起。这反过来又迫使以色列国防军加强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地区的行动,并大大增加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继续快速进行,以色列逐渐滑向事实上的一国现实。这排除了任何未来协议的选择,并挑战了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身份。在以色列新政府的领导下,这些进程中固有的危险可能会加剧,新政府明确主张扩大以色列在整个领土的存在,甚至吞并这些领土。
Tamir Hayman、Ram Yavne 和 Anat Kurz,编辑 - INSS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继续衰弱,在当地失去控制,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没有明显的继任者或有序移交权力的机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的真空,加上缺乏政治前景,导致恐怖袭击浪潮分散,狮子窝等暴力当地组织的崛起。这反过来又迫使以色列国防军加强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地区的行动,并大大增加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继续快速进行,以色列逐渐滑向事实上的一国现实。这排除了任何未来协议的选择,并挑战了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身份。在以色列新政府的领导下,这些进程中固有的危险可能会加剧,新政府明确主张扩大以色列在整个领土的存在,甚至吞并这些领土。
Tamir Hayman、Ram Yavne 和 Anat Kurz,编辑 - INSS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继续衰弱,在当地失去控制,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没有明显的继任者或有序移交权力的机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的真空,加上缺乏政治前景,导致恐怖袭击浪潮分散,狮子窝等暴力当地组织的崛起。这反过来又迫使以色列国防军加强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地区的行动,并大大增加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继续快速进行,以色列逐渐滑向事实上的一国现实。这排除了任何未来协议的选择,并挑战了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身份。在以色列新政府的领导下,这些进程中固有的危险可能会加剧,新政府明确主张扩大以色列在整个领土的存在,甚至吞并这些领土。
Tamir Hayman、Ram Yavne 和 Anat Kurz,编辑 - INSS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继续衰弱,在当地失去控制,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没有明显的继任者或有序移交权力的机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的真空,加上缺乏政治前景,导致恐怖袭击浪潮分散,狮子窝等暴力当地组织的崛起。这反过来又迫使以色列国防军加强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地区的行动,并大大增加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继续快速进行,以色列逐渐滑向事实上的一国现实。这排除了任何未来协议的选择,并挑战了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身份。在以色列新政府的领导下,这些进程中固有的危险可能会加剧,新政府明确主张扩大以色列在整个领土的存在,甚至吞并这些领土。
Tamir Hayman、Ram Yavne 和 Anat Kurz,编辑 - INSS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继续衰弱,在当地失去控制,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没有明显的继任者或有序移交权力的机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的真空,加上缺乏政治前景,导致恐怖袭击浪潮分散,狮子窝等暴力当地组织的崛起。这反过来又迫使以色列国防军加强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地区的行动,并大大增加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继续快速进行,以色列逐渐滑向事实上的一国现实。这排除了任何未来协议的选择,并挑战了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身份。在以色列新政府的领导下,这些进程中固有的危险可能会加剧,新政府明确主张扩大以色列在整个领土的存在,甚至吞并这些领土。
前哨 - GE2P2 Global
一周在审查中,高度选择性地捕获了战略发展,研究,评论,分析和公告,涵盖人权行动,人道主义反应,健康,教育,发展,遗产管理,和平冲突。在这些广泛的主题中实现平衡是一个挑战,我们感谢您在这方面的观察和想法。:::::::::::::::::: Gaza/opt International社会必须继续推动永久停火,努力努力加沙的重建,秘书长告诉巴勒斯坦权利委员会发言人说,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委员会敦促成员国敦促完全支持UN PALESTINE ANDICE机构的重要工作,以下是ISRAERIS的重要工作。联合国酋长今天对巴勒斯坦权利委员会表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推动永久停火并致力于重建加沙,并在此过程中强调了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局在此过程中的巴勒斯坦难民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讲,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是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人类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些权利的实现稳步下降了,因为世界目击者“令人震惊,有系统的非人性化和整个人民的妖魔化”。位移,饥饿和疾病后的位移使整个一代人无家可归并受到创伤。据报道,近50,000人(其中70%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加沙的大多数平民基础设施 - 医院,学校和水设施 - 已被销毁。“我们不能恢复更多的死亡和破坏,”他断言,并补充说,联合国正在全天候工作,以吸引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并扩大支持。需要快速,安全,不受阻碍,扩大和持续的人道主义访问权限,呼吁成员国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充分的资金并支持UNRWA的重要工作。在寻求解决方案时,至关重要的是要忠于国际法的基础,并避免任何形式的种族清洗,并补充说,可行的,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家与以色列的和平与安全并肩生活是“中东稳定性的唯一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与之相关的是,他对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以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的西岸的其他违法行为表示严重关注。“暴力必须停止,”他敦促尊重国际法,包括国际法院命令……:::::::::::::::::::::::
kff敦促在家谨慎对待“无火”斋月
开罗,3月4日,(库纳):他殿下的代表阿米尔·谢赫·艾哈迈德·阿尔·贾伯·贾伯·萨巴(Amir Sheikh Meshal al-Jaber al-Sabah),他的殿下是谢赫·萨巴·萨巴·萨巴·哈拉德·哈马德·萨巴(Al-Haled al-Hamad al-Sabah)王子,于周二到达埃及的开罗,并在周二的阿拉伯派遣派委员会上登上了阿拉伯派发。他的殿下是埃及人青年和体育部长阿什拉夫·索比(Ashraf Sobhi)和科威特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尔·耶亚(Abdullah al-yahya),外交部长助理外交部长贝勒·萨利赫(Bader Saleh al-Taneeb)的助理外交部长萨利赫·萨利布(Bader Saleh al-Taneeb)阿拉伯国家大使塔拉尔·穆特里(Talal al-Mutairi)。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总统顾问穆罕默德·哈巴什(Mohammad al-Habbash)周一表示,巴勒斯坦的愿景将在开罗的非凡阿拉伯峰会上进行讨论,必须对加沙地带和西岸进行统一。与Kuna交谈时,Al-Habbash博士认为,对巴勒斯坦的未来保持统一的愿景的重要性,这应该终止占领并赋予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参与了巴勒斯坦的参与
死亡焦虑与巴勒斯坦妇女患有乳腺癌的应对策略的相关性:一项横断面研究
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患者经历了深刻的心理反应,包括即将死亡的感觉。结果,死亡焦虑被广泛认为是影响癌症管理影响的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死亡焦虑是个人遇到与死亡有关的负面思想时表现出的情感反应(4)。它会损害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可能导致精神障碍并降低整体生活质量(5,6)。此外,死亡焦虑对癌症治疗和消除具有显着影响(7)。癌症患者报告了中度的死亡焦虑症,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妇女报告较高水平(8)。根据Masror Roudsary等。的(9)在伊朗的研究中,有79%的乳腺癌患者担心死亡。 此外,在巴基斯坦对80例乳腺癌患者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表明,13.8%,51.2%,27.5%和7.5%的患者分别患有低,中等,中,高和非常高的死亡焦虑症(10)。 对人之间的死亡的恐惧源于各种原因,包括身份丧失,对死亡后的生活焦虑,痛苦和困扰以及亲人的幸福。 对死亡的恐惧影响患者的预后,导致治疗怀疑或中断(11)。 许多研究探索了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对死亡的恐惧(3,12-15)。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早期患者在担心死亡方面经历了哪些经历,因为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侧重于绝症(16)。 Shakeri等。的(9)在伊朗的研究中,有79%的乳腺癌患者担心死亡。此外,在巴基斯坦对80例乳腺癌患者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表明,13.8%,51.2%,27.5%和7.5%的患者分别患有低,中等,中,高和非常高的死亡焦虑症(10)。对人之间的死亡的恐惧源于各种原因,包括身份丧失,对死亡后的生活焦虑,痛苦和困扰以及亲人的幸福。对死亡的恐惧影响患者的预后,导致治疗怀疑或中断(11)。许多研究探索了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对死亡的恐惧(3,12-15)。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早期患者在担心死亡方面经历了哪些经历,因为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侧重于绝症(16)。Shakeri等。(3)发现乳腺癌患者的死亡焦虑评分为67.5%。妇女怀有对死亡率,加剧病,未来的丧失以及对他人的依赖的忧虑(3)。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妇女采用应对策略来应对新生活环境的心理,社会和精神方面引起的复杂而多方面的挑战(17)。他们必须适应每天发生的变化,以减轻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18)。应对是在癌症并发症期间采取的心态和行动(19)。研究人员发现,使用应对机制的严重和绝症患者的寿命更长并提高了生活满意度(20)。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能够管理强烈的情绪,而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解决了困扰的根源(21)。癌症患者通常会诉诸拒绝,酒精或药物,排泄,自我分心和行为脱离接触;这些策略使它们的适应性降低(17)。诊断出癌症时,这些应对策略会增加抑郁症的风险和自尊心下降(22)。基于宗教的解决问题和应对方法更适应性,并减少抑郁症状(23)。但是,缺乏定量研究,可以评估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巴勒斯坦妇女的应对策略。根据一项定性研究,巴勒斯坦乳腺癌妇女通常依靠社会支持和宗教作为应对策略(24)。预先存在的应对方式以及与他人的支持关系,对个人有效应对疾病的能力有影响。此外,对癌症作为威胁的看法似乎促进了主动应对行为(2)。相反,将其疾病视为长期,情感繁重且具有更多负面后果的癌症患者更有可能采用被动应对策略(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