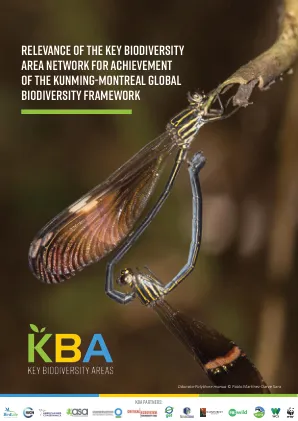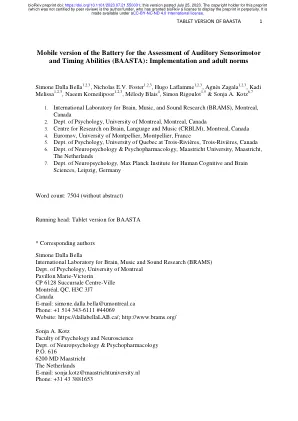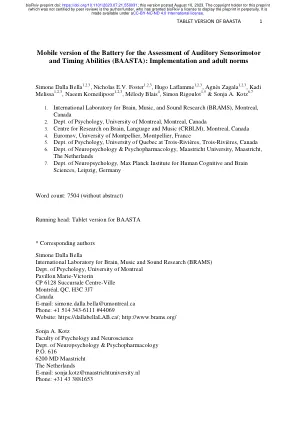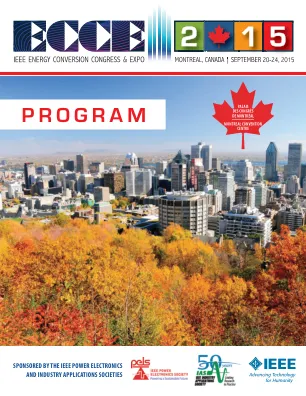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心脏发育的心内膜调节
1心血管遗传学,库氏圣司机研究中心,蒙特利尔,QC H3T 1C5,加拿大; lara.michele.feulner@umontreal.ca(l.f.); patrick.van.vliet.hsj@ssss.gouv.qc.ca(p.p.v.v.)2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分子生物学系,QC H3T 1J4,加拿大3 LIA(国际相关实验室)Chu Sainte-Justine,蒙特利尔,QC H3T 1C5,加拿大; Michel.puceat@inserm.fr 4 LIA(国际相关实验室)Inserm,13885,法国Marseille 5 Inserm U-1251,Marseille Medical Genetics,Aix-Marseille University,Aix-Marseille University,13885 Marseille,France 6 Marseille,6 Intreal,Montreal,Montreal,QC H3 Trestrics 1J4生物化学和分子医学系,生物化学和分子医学系蒙特利尔,QC H3T 1J4,加拿大8蒙特利尔大学生物化学系,蒙特利尔大学,QC H3T 1J4,加拿大 *通信:Gregor.andelfinger.med@ssssss.gouv.qc.qc.qc.ca
关键生物多样性领域网络的相关性对于昆明 -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现
确保并启用,到2030年至少30%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海洋和沿海地区,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特别重要的领域,通过生态代表性,良好的,良好的领域和其他有效的定义衡量标准,有效地保守和管理,并通过生态代表性地进行了良好的代表性,并具有良好的领域,并具有有效的定义性,并构成了有效的衡量标准。更广阔的景观,海景和海洋,同时确保在此类地区适当的任何可持续用途都与保护结果完全一致,认可和尊重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包括传统领土。
独特的全脑细胞类型预测13个神经退行性条件下的组织损伤模式
隶属关系:1神经和神经外科系,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加拿大2麦康奈尔脑成像中心,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3号,加拿大魁北克3卢德默神经信息和精神健康中心,加拿大QUEBEC,QUEBEC,QUEBER,QUEBER,QUEBER,QUEBER,QUEBER,QUEBER,QUEBER,QUEDER,CANACANE 5 Biomedical Engineering,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Quebec, Canada 6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Quebec, Canada 7 Mila – Quebe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Montreal, Quebec, Canada 8 The Douglas Research Center, Montreal, Quebec, Canada * Correspondence to: Yasser Iturria-Medina, 3801 University Street, room NW312,蒙特利尔神经学院和医院,麦吉尔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H3A 2B4。yasser.iturriadina@mcgill.ca。orcid:https://orcid.org/0000-0000- 0002-9345-0347
研究文章 使用魁北克卫生管理数据预测自杀风险的可解释人工智能模型
1 加拿大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智力与知识研究所 (IID)、2 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省国立公共卫生研究所 (INSPQ)、3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大学精神病学和成瘾学系、4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所研究中心、5 加拿大渥太华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健康促进和慢性疾病预防处监测和应用研究中心、6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与预防医学系、7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心理健康大学研究所研究中心、8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达尔豪西大学医学院社区健康和流行病学系
加拿大音乐老师
董事会半年会议:2025年2月1日,通过Zoom年度会议管理委员会的虚拟会议:7月2日至2025年7月2日至2025年,蒙特利尔/Zoom年度大会的混合会议:2025年7月2日,2025年7月2日,蒙特利尔(Montreal)的混合会议,请在蒙特利尔(Montreal)进行命令:当前的问题:总裁-Heather Fyffe,秘书半年会议:2025年2月1日,通过Zoom年度会议管理委员会的虚拟会议:7月2日至2025年7月2日至2025年,蒙特利尔/Zoom年度大会的混合会议:2025年7月2日,2025年7月2日,蒙特利尔(Montreal)的混合会议,请在蒙特利尔(Montreal)进行命令:当前的问题:总裁-Heather Fyffe,秘书
量子通过光子晶体纤维中的自我诱导的透明度挤压
1。国际大脑,音乐和声音研究实验室(BRAMS),加拿大蒙特利尔2。部门心理学,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3。 大脑,语言和音乐研究中心(CRBLM),加拿大蒙特利尔4。 欧洲群岛,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5。 部门 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Canada 6。 部门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马斯特里奇大学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7。 部门 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心理学,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3。大脑,语言和音乐研究中心(CRBLM),加拿大蒙特利尔4。欧洲群岛,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5。 部门 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Canada 6。 部门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马斯特里奇大学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7。 部门 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欧洲群岛,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5。部门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Canada 6。部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马斯特里奇大学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7。部门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
电池的移动版本,用于评估听觉感觉运动能力和时机能力(Baasta):实施和成人规范
1。国际大脑,音乐和声音研究实验室(BRAMS),加拿大蒙特利尔2。部门心理学,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3。 大脑,语言和音乐研究中心(CRBLM),加拿大蒙特利尔4。 华沙经济学与人类科学大学,波兰,波兰5。 欧罗马夫,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6。 部门 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加拿大7。 部门 Maastricht University,Maastricht,Maastricht,Maastricht的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8. 部门 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心理学,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3。大脑,语言和音乐研究中心(CRBLM),加拿大蒙特利尔4。华沙经济学与人类科学大学,波兰,波兰5。欧罗马夫,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6。部门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加拿大7。部门Maastricht University,Maastricht,Maastricht,Maastricht的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8. 部门 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Maastricht University,Maastricht,Maastricht,Maastricht的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8.部门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
电池的移动版本,用于评估听觉感觉运动能力和时机能力(Baasta):实施和成人规范
1。国际大脑,音乐和声音研究实验室(BRAMS),加拿大蒙特利尔2。部门心理学,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3。 大脑,语言和音乐研究中心(CRBLM),加拿大蒙特利尔4。 欧洲群岛,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5。 部门 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Canada 6。 部门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马斯特里奇大学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7。 部门 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心理学,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3。大脑,语言和音乐研究中心(CRBLM),加拿大蒙特利尔4。欧洲群岛,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5。 部门 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Canada 6。 部门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马斯特里奇大学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7。 部门 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欧洲群岛,蒙彼利埃大学,蒙彼利埃,法国5。部门心理学,魁北克大学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Canada 6。部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马斯特里奇大学神经心理学与心理药理学7。部门神经心理学,麦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
通过磁共振成像和机器学习来识别REM睡眠行为障碍
1解剖系,魁北克大学,QC,QC的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Trois-Rivières,加拿大QC 2加拿大QC蒙特利尔高级技术学院蒙特利尔高级技术学院5蒙特利尔综合医院神经病学系,加拿大QC蒙特利尔6蒙特利尔6蒙特利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QC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QC 7 QC,加拿大9个临床神经科学,放射学的居民和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大学的霍奇基斯脑研究所,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10号,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魁北克大学心理学系10,加拿大QC,QC,加拿大,加拿大 *这些作者为这项工作做出了同样的贡献。#这些作者分享了高级作者身份。†电流隶属关系:1。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安大略省西安大略大学的大脑和思维学院。2。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安大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联系信息:魁北克大学心理学系Jean-FrançoisGagnon博士8888吸。蒙特利尔市区(魁北克),H3C 3P8,加拿大电子邮件:gagnon.jean.jean-francois.2@uqam.ca Word Count:3698运行标题:使用机器学习冲突的RBD识别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资金来源:加拿大卫生研究所(CIHR),魁北克研究基金 - 健康(FRQ-S),魁北克大学(RISUQ)的部门卫生研究网络(RISUQ),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大学(Neurooqam)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QUEBEC,NEUROQAM(NEUROQAM),PARKINFIFFEFFEDD,WEARD FIELD,WEARFIELD,WEARFIELD,WEARFIELD,WEARFIELD和WEARFIELD,WEARFIELD和WEAR。
项目 - IEEE-ECCE 2023
蒙特利尔是欧洲魅力与北美活力的完美结合,是一座全球性大都市,不仅以其国际水准的文化、历史、娱乐、美食和购物而闻名,而且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制造、能源、信息和金融等行业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ECCE 2015 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蒙特利尔会议中心举行,该中心以其超现代的设施和卓越的可持续能源性能而闻名,同时也是连接蒙特利尔国际区与历史悠久的蒙特利尔老城区和唐人街的枢纽。蒙特利尔这座国际大都市安全、友好且交通便利,将为 ECCE 2015 的与会者提供热情的欢迎、美丽的秋色、充满活力的社区和独特的文化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