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名称:
¥ 54.0
两年前,由于一系列奇怪的巧合,我参加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花园派对。我有点不自在。并不是说其他客人不友好,组织派对的格雷姆神父也是一位亲切而迷人的主人。但我感觉有点不自在。有一次,格雷姆神父插话说,附近喷泉旁边有个人我一定想见见。原来她是一位身材苗条、衣着考究的年轻女子,他解释说她是一名律师——“但更像激进分子。她在一家为伦敦反贫困组织提供法律支持的基金会工作。你们可能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的工作。我告诉她,我多年来一直参与全球正义运动——媒体通常称之为“反全球化运动”。她很好奇:她当然读过很多关于西雅图、热那亚、催泪瓦斯和街头战斗的文章,但是……好吧,我们真的通过所有这些取得了什么成就吗?“实际上,”我说,“我认为我们在最初几年里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David Graeber - 债务:前 5000 年 (PDF)







![塔塔行为准则 [PDF]](/simg/4/46d9b710d708a5030c8085493cf83310eea342f3.webp)
![[PDF] 创新与创业](/simg/a/a64bf7d84ec9ebdee9d29d806db8eb42a605a26e.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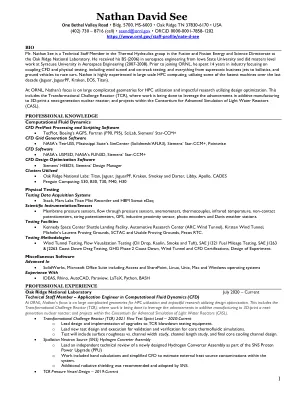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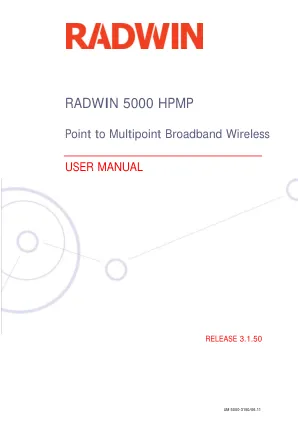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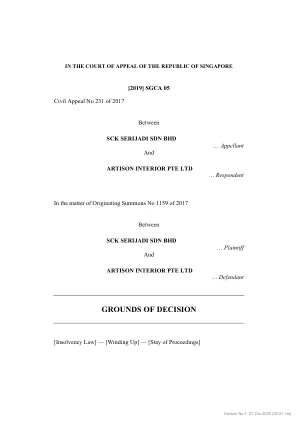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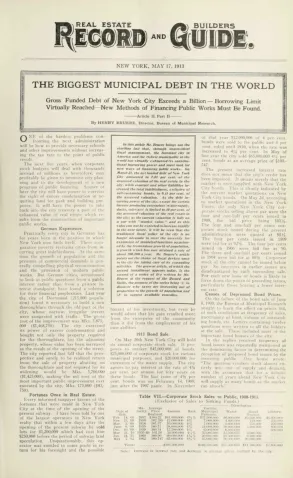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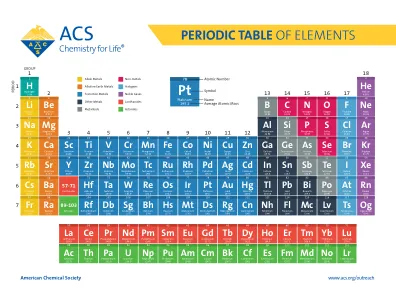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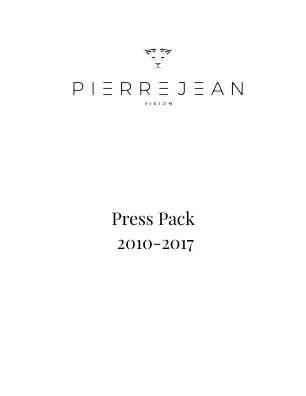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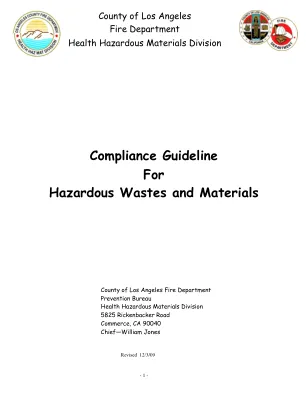
![[PDF] 气候变化 - 世界银行文件](/simg/c/c16cf2ffeba4181b5acb8103fe302dc839f6b7f6.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