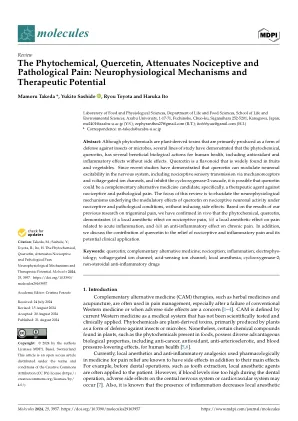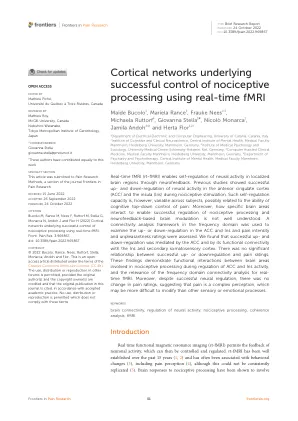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多动物模型研究揭示了神经可塑性和伤害性基因的突变与饮酒过量有关
结果:我们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是,除了引起翻译变化的变体外,与饮酒前的饮酒相关的主要遗传变化也称为“沉默突变”和3'未翻译区域(3'UTR)中的突变。这些都没有改变所翻译的氨基酸序列,而是影响基因转录的速率和构象,包括改变基因疗效的稳定性和翻译后事件。这一发现提倡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重新聚焦基因效能感的变化。在确定的关键本体论中是“疼痛的伤害感受或感觉感知”,它不仅包含伤害感受(ARRB1,CCL3,EPHB1),而且还伴有钠(SCN1A,SCN1A,SCN2A,SCN2B,SCN2B,SCN3A,SCN3A,SCN7A,SCN7A),SCN7A),SCN99A(SCN9A9A)(kc N9aa)(KC)和POTASS(kc)。
Bayliss -Starling奖演讲:脊髓和皮质伤害性电路的发育生理学
■关于科学和数学中违反直觉概念的推理被认为需要抑制幼稚的理论,先验知识或通过抑制性控制误导感知线索。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在违反直觉推理过程中,PFC区域募集了,这被解释为抑制性控制过程的证据。ever的结果不一致,并且尚未与行为或大脑活动直接进行比较。在这项FMRI研究中,有34名青少年(11 - 15岁)回答了科学和数学问题,并完全抑制了抑制任务(简单而复杂的GO/NO- GO)和一个干扰控制任务(数值Stroop)。与对照
负责将持续的伤害性输入转化为主观疼痛体验的神经过程
追踪和预测伤害性输入的时间结构对于促进生存至关重要,因为适当和立即的反应对于避免实际或潜在的身体伤害必不可少。不同时间结构的伤害性刺激所引起的神经活动已有描述,但将伤害性刺激转化为疼痛感知的神经过程尚未完全阐明。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了 48 名健康参与者的脑电信号,这些参与者接受了 3 种不同持续时间和 2 种不同强度的热伤害性刺激。我们观察到疼痛感知和几种大脑反应受到刺激持续时间和强度的调节。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确定了 2 种与疼痛感知出现相关的持续大脑反应:来自岛叶和前扣带皮质的低频成分 (LFC,< 1 Hz) 和来自感觉运动皮质的 α 波段事件相关去同步 (α-ERD,8–13 Hz)。这两种持续的大脑反应是高度耦合的,α 振荡幅度随 LFC 相位波动。此外,刺激持续时间转化为疼痛感知的过程由 α -ERD 和 LFC 连续介导。本研究揭示了伤害性刺激引起的大脑反应如何反映伤害性信息转化为疼痛感知过程中发生的复杂过程。
神经刺激植入后的精确康复,用于伤害性机械慢性下腰痛的多动物功能障碍
没有指示手术。正确选择符合特定标准的患者(基于从随机对照试验中的史学结果),他们努力地遵守植入物的使用情况并预先实施神经肌肉康复,改善功能恢复显着的成功成功,以及减少止痛药物。接受植入多卵形神经刺激的伤害性机械CLBP患者已受到医生和康复专家的治疗,他们磨练了从事多纤维神经刺激的经验。他们已经合作制定了共识和证据驱动的指南,以提高质量外,并在遇到此设备患者时协助提供者。医师和物理治疗师一起提供精确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管理,并具有优质的神经肌肉康复,以鼓励患者成为其植入物的专家和优质的脊柱运动,以帮助覆盖长期以来与CLBP相关的长期多发性功能障碍。©2024作者。由Elsevier Inc.代表美国康复医学大会出版。这是CC BY-NC-ND许可证(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下的开放访问文章。
植物化学,槲皮素,减轻伤害性和病理疼痛:神经生理机制和治疗潜力
摘要:尽管植物化学物质是植物来源的毒素,主要是针对昆虫或微生物的一种防御形式,但几项研究表明,植物化学的槲皮素对人类健康具有多种有益的生物学作用,包括抗氧化剂和炎症作用,而无需副作用。槲皮素是一种类黄酮,在水果和蔬菜中广泛发现。最近的研究表明,槲皮素可以调节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兴奋性,包括通过机械感受器和电压门控离子通道的伤害感受性感觉传播,并抑制环氧酶-2-cascade,因此槲皮素可能是一种互补的替代药物候选者;具体而言,一种针对伤害性和病理疼痛的治疗剂。本综述的重点是阐明槲皮素在伤害感受和病理条件下对槲皮素对伤害性神经元活性的调节作用的基础的神经生理机制,而没有诱导副作用。基于我们先前关于三叉病疼痛的研究的结果,我们在体内证实,植物化学的槲皮素表明(i)(i)局部麻醉对伤害性疼痛的作用,(ii)局部麻醉对与急性炎症和(iii)抗炎疼痛有关的疼痛作用。此外,我们讨论了槲皮素对减轻伤害性和炎症性疼痛的贡献及其潜在的临床应用。
开发针对急性和慢性疼痛的伤害感受器选择性治疗方法
什么是疼痛? 尽管我们用“疼痛”一个词来描述包括酸痛、不适和不快等一系列不愉快的感觉,但疼痛本身很复杂,可能由多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引起。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种疼痛情况都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干预(1、2)。疼痛有一些方面确实是生理性的,例如,我们能够察觉到潜在的破坏性外部刺激:极热或极冷、过度的机械力和化学刺激物。这构成了伤害性疼痛,它是由高阈值伤害性感受器感觉神经元的激活驱动的,这些神经元适合于将这些有害刺激转化为进入中枢神经系统(CNS)的感觉输入。伤害性感受器通过激活伤害性回路引起的急性疼痛有助于我们学会避开环境危险(3-6)。疼痛具有高度适应性,在我们与外界的日常互动中,它对于防止损伤至关重要。缺乏这种损伤预警系统的人,比如因电压门控钠通道 1.7 (Nav 1.7) 或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 A (TRKA) 受体功能丧失突变而先天性对疼痛不敏感的人,通常会在进食时损伤舌头和嘴唇,在走路时损伤脚趾,在探索物体时损伤手指,并且在骨折或患阑尾炎时没有任何警示,从而缩短寿命 (7,8)。因此,保留伤害性疼痛至关重要,除了手术期间或之后或重大创伤后立即发生。另一种适应性疼痛是组织损伤或由于病原体侵入或病理性炎症引起炎症时发生的炎症疼痛。随之而来的免疫系统激活导致产生炎症介质,这些介质作用于痛觉感受器,既直接激活(9-11),又使其敏感(12、13)。因此,它们的激活阈值下降,因此低强度刺激(如轻触或关节运动)现在会激活敏感的痛觉感受器,无害刺激会变成疼痛。这种疼痛,至少在急性情况下,是
在愤怒、慢性疼痛和大脑的交汇处
慢性疼痛仍然是世界上最持久的医疗保健挑战之一。为了推进疼痛治疗,专家们最近根据提出的潜在机制引入了研究驱动的慢性疼痛亚型。伤害性疼痛(例如非特异性慢性腰痛或纤维肌痛)就是这样一种亚型,其可能与大脑可塑性、生活压力和创伤引起的痛苦情绪以及不健康的情绪调节有更大的病因作用。特别是,相关和行为数据将愤怒以及愤怒的调节方式与伤害性疼痛的存在和严重程度联系起来。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研究还表明,伤害性疼痛和健康的愤怒调节在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中表现出相反的活动模式;因此,改善愤怒调节可以使这些区域的活动正常化。在这篇小型评论中,我们总结了这些发现,并提出了一个统一的生物行为模型,称为愤怒、大脑和痛觉刺激性疼痛 (AB-NP) 模型,该模型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测试,并可能通过提供针对愤怒、愤怒调节和痛觉刺激性疼痛的大脑可塑性的新治疗方法来促进疼痛护理。
使用实时 fMRI 成功控制伤害感受处理的皮质网络
实时 fMRI (rt-fMRI) 能够通过神经反馈自我调节局部大脑区域的神经活动。先前的研究表明,在伤害性刺激期间,前扣带皮层 (ACC) 和岛叶 (Ins) 的神经活动可以成功上调和下调。然而,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在受试者中是不同的,可能与自上而下的认知疼痛控制能力有关。此外,特定大脑区域如何相互作用以成功调节伤害性处理和基于神经反馈的大脑调节尚不清楚。使用频域连接分析框架检查 ACC 和 Ins 的上调或下调,并评估疼痛强度和不愉快程度。我们发现成功的上调和下调是由 ACC 及其与 Ins 和次级体感皮层的功能连接介导的。成功的上调或下调与疼痛评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这些发现表明,在调节 ACC 和 Ins 活动期间,参与伤害性处理的大脑区域之间存在功能相互作用,并且频域连接分析与实时 fMRI 的相关性也很高。此外,尽管神经调节成功,但疼痛评级没有变化,这表明疼痛是一种复杂的感知,可能比其他感觉或情绪过程更难改变。
OBM 综合和补充医学
摘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催眠可以有效调节急性和慢性疼痛状态下的痛觉。在神经生理学方面,最近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催眠缓解疼痛的奥秘。催眠镇痛暗示很可能能够在中枢神经系统 (CNS) 的多个水平和部位调节疼痛处理。在外周水平,催眠可能通过下调 A delta 和 C 纤维的刺激以及减少交感神经唤起来调节伤害性输入。在脊髓水平,已证明催眠期间发生的感觉镇痛与伤害性屈曲 (RIII) 反射(一种多突触脊髓反射)的减少呈线性相关。在脊髓上皮层水平,神经影像学和电生理学研究表明,镇痛的催眠暗示可以直接调节疼痛知觉的感觉和情感维度,并且情感维度的减少比感觉维度更显著。此外,催眠易感性高的受试者比催眠易感性低的受试者具有更强的注意力过滤能力;前者的认知灵活性更强,可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将注意力从伤害性刺激上转移,并更好地忽略环境中的无关刺激。认知控制过程与“监督注意力系统”有关,该系统涉及额颞边缘皮层。
阿片类药物诱导的痛觉过敏和公差是由HCN离子通道驱动的
长时间暴露于阿片类药物会引起对疼痛刺激的敏感性(阿片类药物诱导的痛觉过敏,OIH),并且需要增加阿片类药物剂量以维持镇痛(阿片类药物诱导的耐受性,OIT),但是这两个过程的基础机制仍然保持模糊。我们发现,雄性小鼠原发性伤害性神经元中HCN2离子通道的药理阻滞或遗传缺失完全消除了OIH,但对OIT没有影响。相反,对中央HCN通道的药理抑制可缓解OIT,但对OIH没有影响。C-FOS的表达是神经元活性的标志物,通过诱导OIH的二阶神经元增加了C-FOS的表达,并且通过HCN2的外围阻滞或HCN2的遗传缺失来预防增加的HCN2,但HCN通道的脊柱障碍块对C-FOS的脊柱块对C-FOS的表达没有影响。总体而言,这些观察结果表明,OIH是由外围伤害感受器中的HCN2离子通道驱动的,而OIT则由位于CNS中的HCN家族的成员驱动。诱导OIH增加了伤害性神经元的cAMP,因此HCN2激活曲线的转移导致伤害感受器的增加。 HCN2的移位是由组成型活性μ-阿片受体(MOR)表达引起的,并被MOR拮抗剂逆转。 我们将阿片类药物诱导的MOR识别为六跨膜剪接变体,我们表明它通过组成型与G s的耦合而增加了cAMP。 因此, HCN2离子通道驱动OIH,可能是OIT,并且可能是成瘾治疗的新型治疗靶标。诱导OIH增加了伤害性神经元的cAMP,因此HCN2激活曲线的转移导致伤害感受器的增加。HCN2的移位是由组成型活性μ-阿片受体(MOR)表达引起的,并被MOR拮抗剂逆转。我们将阿片类药物诱导的MOR识别为六跨膜剪接变体,我们表明它通过组成型与G s的耦合而增加了cAMP。HCN2离子通道驱动OIH,可能是OIT,并且可能是成瘾治疗的新型治疗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