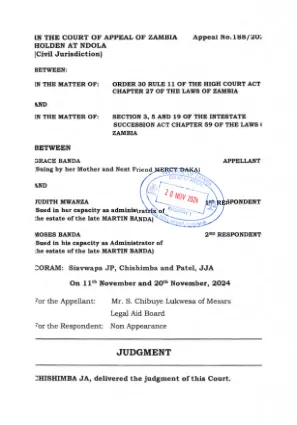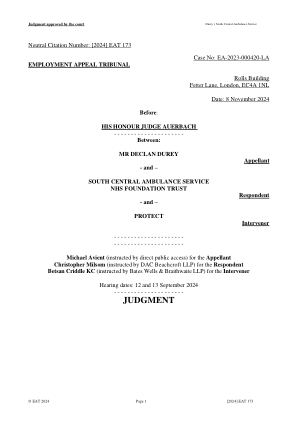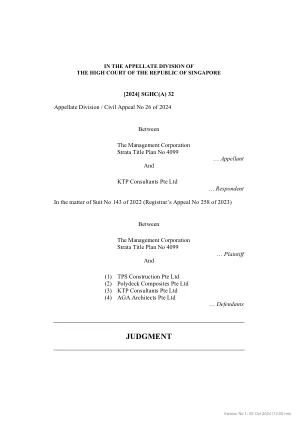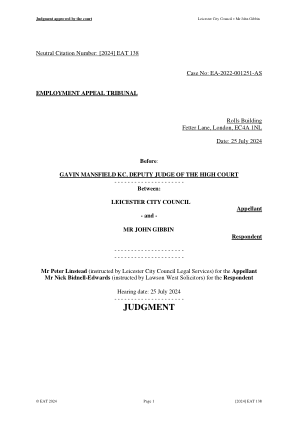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评估用于生成和判断编程反馈
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各种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在计算教育研究(CER)领域,LLM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在学习过程中。在CER中,LLM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应用和评估专有模型方面进行了努力。在本文中,我们评估了开源LLMS在为编程作业生成高质量反馈和判断编程反馈质量的高质量反馈方面的效率,并将结果与专有模型进行了对比。我们对学生的介绍性python编程练习的数据集进行评估表明,最先进的开源LLM与生成和评估编程反馈的过程中与亲密模型几乎相当。此外,我们证明了较小的LLM在这些任务中的效率,并向教育者和从业者突出了可访问的广泛的LLM,即使是免费的。
评估用于生成和判断编程反馈
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各种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在计算教育研究(CER)领域,LLM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在学习过程中。在CER中,LLM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应用和评估专有模型方面进行了努力。在本文中,我们评估了开源LLMS在为编程作业生成高质量反馈和判断编程反馈质量的高质量反馈方面的效率,并将结果与专有模型进行了对比。我们对学生的介绍性python编程练习的数据集进行评估表明,最先进的开源LLM与生成和评估编程反馈的过程中与亲密模型几乎相当。此外,我们证明了较小的LLM在这些任务中的效率,并向教育者和从业者突出了可访问的广泛的LLM,即使是免费的。
判断
“9. 2015 年 7 月,OBU 和被告同意对 FdSc 课程进行修改,这意味着学生在学习课程的学术部分、住院实习以及为被告工作至少 225 小时期间将被授予超编人员身份。超编人员小时数从 750 小时减少。10. OBU 向 HCPC 负责 FdSc 的实施,OBU 对 FdSc 的任何修改均需报告。微小修改可在 OBU 的年度报告中报告,重大修改需在重大修改表中尽早报告。OBU 并不认为这是重大修改。11. 2015 年 7 月 30 日,原告课程的学生被邀请参加与 Catterall 先生和被告经理的会议,在会上,学生被告知 FdSc 课程已发生变更。学生们被告知,课程的变更意味着一线额外培训小时数将从 750 小时减少到最低 225 小时。原告询问 HCPC 是否已批准变更。答复称,OBU 的立场是,课程这方面的任何变更都可以事后通知 HCPC。原告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这些变更将意味着学生无法安全执业。Catterall 先生告诉原告,HCPC 会提供指导,无需征得他们同意即可进行变更。12. 2015 年 8 月 12 日,原告写信给大学和实践教育团队经理 Caroline Robertson 女士,询问减少额外实习救护车小时数的问题。Robertson 女士将信件副本转发给了 Catterall 先生,他们同意 Catterall 先生会回复原告的担忧。 Catterall 先生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回复了申诉人。在信中,Catterall 先生试图向申诉人保证,“内部评估的结论是,由于学生在注册护理人员的指导下的总实习时长仍为 750 小时,因此我们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实习时长是受监督还是额外时长,这不会影响学生是否符合 HCPC SET 的要求以及毕业生注册成为护理人员的资格。” 13. 2015 年 8 月 19 日,Robertson 女士向高级运营经理及其团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该邮件被转发给其他人,包括临床导师和团队负责人。电子邮件内容如下:
2024年APL 308中的判断...
在:1。北方邦电力公司有限公司通过其董事总经理(电力购买协议),14楼,Shakti Bhawan Extension,14-Ashok Marg,Lucknow,Uttar Pradesh - 226 001。…上诉人号1 2。Paschimanchal Vidyut Vitran Nigam Limited通过其董事总经理Urja Bhawan,Victoria Park,Meerut,Meerut,北方邦 - 250 001。…上诉人号2 3。Purvanchal Vidyut Vitran Nigam通过其董事总经理DLW Bhikaripur,Varanasi,北方邦 - 221004。…上诉人第3号4。Madhyanchal Vidyut Vitran Nigam通过其董事总经理,4-A,Gokhale Marg,I Block I,Gokhale Vihar,Butler Colony,Butler Colony,Lucknow,Uttar Pradesh - 226001。…上诉人号4对1。北方邦电力监管委员会通过其秘书
集体判断形成协作研究联盟
集体判断形成提议者日将在 Microsoft Teams 上以虚拟方式举行。活动将于 2024 年 9 月 4 日美国东部时间 11:00 至 13:00 举行。日期或时间的任何更改都将在 grants.gov 和 SAM.gov 上发布。需要注册才能参加。要注册,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jf-cra-baa@army.mil,主题为:“CJF 提议者日注册”。在您的电子邮件中包括每个参与者的全名、大学/组织和电子邮件地址。每位指定参与者都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参加现场活动的链接。有关此 BAA 的问题可以在提议者日之前提交。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jf-cra-baa@army.mil,主题为:“CJF 提议者问题”。问题不会收到单独的电子邮件回复。相反,这些问题将在会议期间得到解答,并发布到 grants.gov 和 SAM.gov 上的问答部分。参与者可以在活动期间通过 Teams 的聊天功能提交问题。(部分结束)
判断
出现在诉讼中,《1978 年国家豁免法》第 1(2) 条。关于雇佣索赔,《国家豁免法》第 4 条规定,“4 雇佣合同。 (1) 如果合同是在英国签订的,或工作全部或部分在英国进行,国家在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雇佣合同有关的诉讼中不享有豁免。 (2) 除下文第 (3) 和 (4) 款另有规定外,本节不适用,如果 - (a) 在提起诉讼时,个人是有关国家的国民;或 (b) 有关国家是《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的缔约国,并且]在签订合同时,个人既不是英国国民,也不在英国惯常居住;或 (c) 合同双方另有书面约定。 (3)如果该工作是为该国为商业目的而设立的办事处、机构或机构而进行的,上述(2)款(a)和(b)项不排除本节的适用,除非该个人在签订合同时惯常居住在该国。
判断
原告是 1995 年 3 月 31 日(根据《1993 年司法养老金和退休法案》(JUPRA)规定为“指定日”)之后任命的巡回法官。他们之前是付费兼职书记员(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之前被任命),在被任命为巡回法官时,他们被强制加入 JUPRA 养老金计划,并且无法享受对他们来说更有利的《1981 年司法养老金法案》(JPA)养老金计划。他们的比较对象是 1995 年 3 月 31 日之前任命的巡回法官,根据 JUPRA,他们在该日期之后可以继续享受 JPA 计划的待遇,而原告则不在此限。在 O'Brien 诉讼之后(O'Brien v. Ministry of Justice (Nos. 1 and 2) [2012] ICR 995; [2013] ICR 499; [2017] ICR 1101; [2019] ICR 505),原告已根据 JPA 条款获得与其担任书记员有关的养老金。仲裁庭有权裁定书记员和巡回法官的职务不同,尽管巡回法官和书记员在司法工作中从事基本相同的活动。仲裁庭不受欧洲联盟法院在 O'Brien v. Ministry of Justice [2012] ICR 995 一案中裁定巡回法官和书记员的职务相同推理的约束。仲裁庭在考虑当时的国内立法时并未犯错。仲裁庭有权裁定,索赔人在被任命为巡回法官后被拒绝享受 JPA 计划条款,而他们的参照人(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之前被任命为受薪巡回法官)在 JUPRA 颁布后被允许继续享受 JPA 计划条款,其有效和主要原因不是索赔人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之前和之后都曾兼职担任书记员;而是索赔人是 1995 年 3 月 31 日之后为养老金目的被任命为不同合格司法职位的一批法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