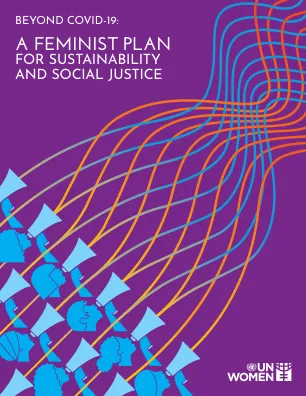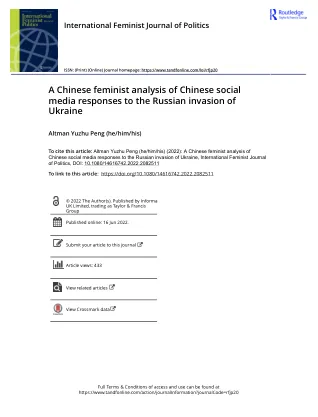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赋予妇女权力
但全球化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深化贸易联系,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和威胁的能力,我们可能会看到集团内贸易的增加。全球化性质的变化可能会对妇女赋权产生影响。
妇女权利与数字技术、公民空间、数据和隐私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
文本摘要:开放、安全、负担得起且高质量的互联网接入为妇女和女孩(包括具有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特征的妇女和女孩)提供了空间,使她们能够通过新渠道参与影响公共辩论和决策。然而,妇女和女孩仍然特别容易受到网络空间的威胁和攻击,尤其是那些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这些规范为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提供了正当理由。特别是,就女权主义问题发声的女性人权捍卫者、女记者和政客,或来自种族、民族、宗教或少数群体的女性,遭受虐待的比例和方式都高于男性。监控技术(如 Pegasus 间谍软件)和其他能够系统监控线上和线下公共空间的工具,促进了政府、私人行为者和个人进行大规模和有针对性的监控,对女性人权捍卫者、活动家以及暴力和虐待受害者的言论自由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鉴于私人信息和通信经常被用来攻击女性,监控对女性来说尤其重要。女性私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容易受到多种形式的监视,从家庭暴力到性客体化和生殖。除了监视之外,女性和性别不合规范的人还面临审查。社交媒体公司和平台的在线内容审核涉及人工审核和算法的混合。据报道,女性(尤其是少数群体的女性)制作的内容和图像被删除。主要建议: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女权主义计划
阿巴斯医师(Abbas),AWID;联合国妇女署的拉娜·阿卡(Lana Ackar)芭芭拉·亚当斯(Barbara Adams),新学院;劳拉·阿尔弗斯(Laura Alfers),WIEGO;致电康考迪亚大学的 Akbulut;福特基金会的莫妮卡·德曼; Phelogene Anumo,AWID; ONE 女子组的吉内特·阿斯科纳 (Ginette Azcona);伊莎贝拉·巴克,约克大学;拉迪卡·巴拉克里希南 (Radhika Balakrishnan),罗格斯大学; Elisenda Crossbow,国际IDEA公司;联合国妇女署朱莉·巴林顿;汉娜·巴加维(Hannah Bargawi),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阿默斯特学院的 Amrita Basu;弗拉维亚·比罗利 (Flavia Biroli),巴西利亚大学;艾丽莎·布劳斯坦 (Elissa Braunstein),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索马里樱桃,独立;迪普塔·乔普拉 (Deepta Chopra),发展研究所;雷切尔·科埃略 (Rachel Coello),ONE Women;莎拉·库克(Sarah Cook),新南威尔士大学;菲律宾能源、生态与发展中心的 Avril de Torres;联合国妇女署的马马杜·博博·迪亚洛;维多利亚·迪亚兹-加西亚(ONE Women)萨拉·杜埃尔托-瓦莱罗(ONE Women)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的米尼翁·达菲 (Mignon Duffy);杰萨明·因卡西尼申(Jessamyn Incarnation),ONE Women;南希·福尔布雷 (Nancy Folbre),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女权主义镜头下的团结经济:批判性和可能的分析
手工艺品,制造,财务,社会和护理服务。这些实践使人们对团结的追求(在工人和生产者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位置之间以及生成之间)的追求优于个人(或集团)的谋求和租金行为(Eme&Laville,2006;Guérin等人,2011; eme&Laville,2006;Guérin等人,2011; servet,2007; servet,2007; servet ,, 2007;或多或少的成功 - 团结经济(SE)实践旨在(重新)发明非资本主义和非家庭社会关系。从允许工人能够适当(或重新适当)生产和建立(或重新激活)社会动态的手段的管理形式开始,它们会以“所有人的能力和所有生活质量”的方式组织社会复制的可能性(Coraggio,2009年)。se的做法还旨在为辩论提供空间,从而将民主和经济联系起来,并带来新的质疑机构以及公共和发展政策的方式。这两个维度的不可分割性(经济和政治)与其他提案(例如“社会经济””,“包容性经济”,“社会企业”或“社会业务”(Laville等,2020)区别于其他建议。长期以来被忽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SE的做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巴西,SE在自我管理方面已被概念化,与工资劳动和小型非正式企业区分开来(Singer,2000;另见:Lemaitre,2009年)。在这里,作者也强调了演员的多种策略和创造力(Hull&James,2012年),他们对保护的需求(Cook等人在拉丁美洲,对SE的兴趣一直是“大众经济”概念的更广泛的范式转变的一部分,从正式/非正式的经济辩论中,人们将注意力从正式/非正式的经济辩论中移开,以考虑各种形式的工作,无论是否受到监管,从他们对生命的贡献的贡献的角度来看(Coraggio,1994年,1994年,2006年;FrançaFilhofilho; nu; nu; nu; Calcagni,1989年; Sarria&Tiriba,2006年)。在安第斯国家,已讨论了有关“社区经济”和“良好生活”模型(Buen Vivir)的讨论,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潜在替代方法(Hillenkamp&Wanderley,2015; Ruiz-Rivera,2019)。这种范式的转变与对贫困社区和社区的地方经济的生计方法的新兴趣相呼应了(Hillenkamp等,2013)。2008; Kabeer 2010)和安全性(Krishnaraj,2007; Shiva,1996)。 虽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系的问题(Gaiger,2003; Singer,2000)和内部竞争机制2008; Kabeer 2010)和安全性(Krishnaraj,2007; Shiva,1996)。虽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系的问题(Gaiger,2003; Singer,2000)和内部竞争机制
中国女权主义者对中国社交媒体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的分析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从北、东、南三面对其西南邻国乌克兰发动了入侵,标志着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灾难性升级。此次入侵立即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玛丽亚·雷普尼科娃 (Maria Repnikova) 和温迪·周 (Wendy Zhou) (2022) 等政治学家迅速指出,俄罗斯方面似乎得到了中国官方和民众的支持。然而,尽管中国政府的沟通方式含糊不清,但中国社交媒体却更加公开地支持俄罗斯。作为一名密切关注中国当前政治气氛的中国女权主义研究者,我理解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挑战美国领导的联盟的情绪化评价,这既是承认中国唯一的主要盟友是俄罗斯,也是通过口语化和挑衅性的帖子来规避官方的审查和监视。然而,最让我震惊的是我的同胞的亲俄评论甚至亲乌克兰回应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性质,这些评论不断出现在我的个人社交媒体上。为了保护亲人,我选择不干预或参与这些揭示中国男性民族主义者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身体的凝视的社交媒体对话。相反,我在这篇对话文章中只提供了一种想象中的回应,通过性别来看待这种数字厌女症和种族主义。
从承诺到行动:捐助者对护理经济和女权主义规划的投资
非洲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的这个项目由 GrOW 东非倡议资助,旨在寻找一种可扩展的儿童保育模式,以提高肯尼亚低收入社区妇女的经济成果。特别是,它将评估“中心辐射”早期儿童发展模式(即 Kidogo 模式)作为可扩展模式的潜力,以提高低收入社区妇女的经济成果。这项研究将在肯尼亚纳库鲁县的纳库鲁镇西分县进行,那里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非正规住区。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将有助于建立具有成本效益的儿童保育模式的证据,并对贫困城市环境中妇女的劳动成果产生影响,并可以推广到该国其他地区和东非地区。
人工智能、机器人、性别、女权主义、性爱机器人、爱情机器人、教育机器人、娱乐机器人、安全机器人、助理机器人、印度、南亚、陪伴机器人、性旅游
1.Shailendra Kumar (博士、工商管理硕士、商学硕士(金牌获得者)、PGDCA) 锡金中央大学教员 印度锡金甘托克 电子邮件:theskumar7@gmail.com 2.Sanghamitra Choudhury(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高级研究员,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查尔斯华莱士研究员,联合国国际法研究员(荷兰海牙学院),尼赫鲁大学初级和高级研究员。(新德里),印度锡金大学教员。通讯作者的电子邮件:schoudhury.oxon@gmail.com
激进关怀女权主义和酷儿激进主义策展
我们非常高兴地推出维也纳美术学院出版物系列的最新一期。该系列与我们高度敬业的合作伙伴 Sternberg Press 合作出版,致力于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思想的核心主题。这些卷包括维也纳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文化研究、艺术史和研究的讨论重点,代表了各自领域的国际研究和讨论的精髓。每卷都以选集的形式出版,由学院的工作人员编辑。我们邀请享有国际声誉的作者就各自的重点领域做出贡献。国际会议、讲座系列、学院特定的研究重点或研究项目等研究活动是各卷的出发点。
通过参与数字初创企业赋予妇女权力
1 OECD。2018 年。《弥合数字性别鸿沟:包容、提升技能、创新》。报告。网址:http://www.oecd.org/internet/bridging-the-digital-gender-divide.pdf,2019 年 9 月 17 日访问。 2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updated-estimates-impact-covid-19-global-poverty-looking-back-2020-and- outlook-2021 3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covid-19-and-gender-equality-countering-the-regressive- effects
女权主义在自己旁边
Bill Readings的死是在将来编辑的女权主义。 ,尽管他的作品在这里没有出现,但与比尔一起思考这本书成为可能。 最初,比尔的无形存在似乎太个人化了,太普遍了,但是当这种存在成为真正的缺席时,它就不再不像了。 我们永远不会事先理解比尔在1994年10月31日发生飞机失事中死亡意味着什么。 现在似乎太明显了,有时责任和义务有时会在事件发生前预见。 莱维纳斯所说的正如莱维纳斯所说的绝对令人惊讶的未来,包括死亡的可能性 - 标记和言论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无法预先计算的另一个人的永久义务。 在没有计算的情况下,通过将思想置于自身旁边,可以通过共同思考来实现。 ,虽然我们将永远无法再次与比尔思考,但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他旁边,共同思考女权主义的未来。Bill Readings的死是在将来编辑的女权主义。,尽管他的作品在这里没有出现,但与比尔一起思考这本书成为可能。最初,比尔的无形存在似乎太个人化了,太普遍了,但是当这种存在成为真正的缺席时,它就不再不像了。我们永远不会事先理解比尔在1994年10月31日发生飞机失事中死亡意味着什么。现在似乎太明显了,有时责任和义务有时会在事件发生前预见。莱维纳斯所说的正如莱维纳斯所说的绝对令人惊讶的未来,包括死亡的可能性 - 标记和言论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无法预先计算的另一个人的永久义务。在没有计算的情况下,通过将思想置于自身旁边,可以通过共同思考来实现。,虽然我们将永远无法再次与比尔思考,但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他旁边,共同思考女权主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