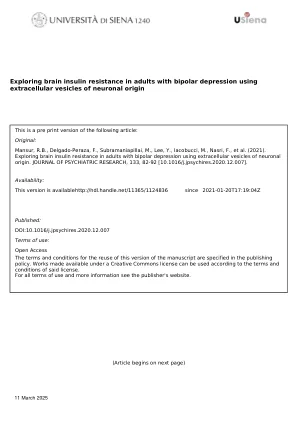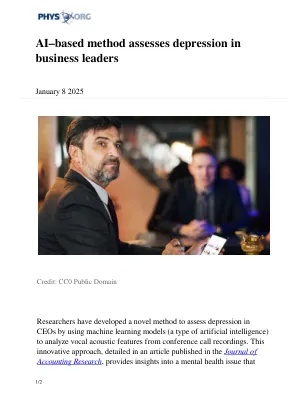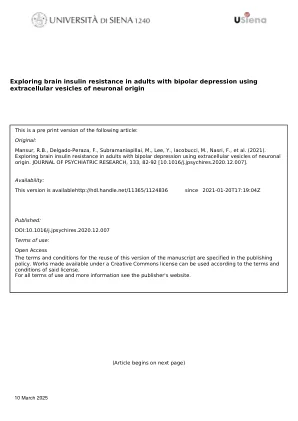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抑郁症和冠心病:机制,干预和治疗
冠心病(CHD)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构成重大威胁的心血管疾病,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然而,与常规的危险因素相比,抑郁症成为冠心病的新型和独立的危险因素。这种情况会影响冠心病的发作和进展,并提高已经受CHD影响的人的不良心血管预后事件的风险。结果,抑郁症引起了全球关注的越来越多。尽管人们的意识越来越不断提高,但抑郁症促进冠心病发展的特定机制仍不清楚。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epression primarily in fl uences the in fl ammatory response, Hypothalamic- 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 (HPA) an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 dysfunction, platelet activation,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lipid metabolism disorders, and genetics, all of which play pivotal roles in CHD development.此外,抗抑郁病患者抗抑郁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及其对冠心病患者预后的潜在影响已成为有争议的受试者。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解决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引用li l-j,mo y,shi z-m,huang x-b,ning y-p,wu h-w,yang x-h和Zheng W(2024)psilocybin用于重度抑郁症:系统评价
主要的抑郁症(MDD)在社会(1)中是一种高度普遍的状况,其特征是严重,持久,不易抑郁症,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和内gui(2)。MDD可以导致残疾,并且与死亡率的增加有关(3)。MDD最常见的药理学治疗方法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以及其他选择性靶向神经递质的相关药物(4)。对MDD成年人的21种常见抗抑郁药的荟萃分析发现,所有这些都比安慰剂在改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方面更有效,但效果大小很小(5)。这些药物的作用延迟,需要数周到几个月的治疗,高副作用率,高复发率和慢性剂量(6)。因此,需要更有效且需要更快地改善抑郁症状的新疗法。新型的药理学干预措施,例如氯胺酮/埃斯酮胺(7)或psilocybin(8),在治疗MDD患者方面表现出积极的结果,并有可能提供更好的保护。用单一或多个输注氯胺酮治疗抑郁症是安全有效的(9,10)。此外,多次输注氯胺酮具有累积和持续的抗抑郁作用(9)。最近的系统评价发现,埃斯酮胺和psilocybin可有效减轻抑郁症状,克服了一些局限性,可以认为是可能的新型抗抑郁药(11)。与psilocybin相比,氯胺酮具有更高的成瘾和毒性作用的潜力(12、13),例如溃疡性膀胱炎(14)。psilocybin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精神活性生物碱,是许多血清素能受体的无可选择激动剂,尤其是5-羟色胺2A(5-HT 2A)(5-HT 2A)(15)。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psilocybin可以有效治疗情绪障碍并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16)。然而,psilocybin的RCT(8、17-20)的发现,检查了MDD患者的psilocybin的效率和耐受性。先前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检查了psilocybin对MDD患者的效率和耐受性。其中一些评论包括原发性抑郁症和继发性抑郁症(21-23),而其他一些评论仅专注于继发性抑郁症,例如生命 -
蓝色的光明面:抑郁作为分析复杂问题的适应性。
抑郁症是寻求帮助的主要情绪状况。沮丧的人经常报告持续的反省,这涉及分析和生活中复杂的社会问题。分析通常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有用方法,但是它需要缓慢,持续的处理,因此破坏会干扰解决问题。The analytical rumination hypothesis proposes that depression is an evolved response to complex problems, whose function is to minimize disruption and sustain analysis of those problems by (a) giving the triggering problem prioritized access to processing resources, (b) reducing the desire to engage in distracting activities (anhedonia), and (c) producing psychomotor changes that reduce exposure to distracting stimuli.由于处理资源是有限的,对触发问题的持续分析会降低专注于其他事物的能力。该假设得到了许多层次的证据,例如基因,神经递质及其受体,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神经术,药理学,药理学,认知,行为和治疗功效。此外,该假设为抑郁症文献中令人困惑的发现提供了解释,这挑战了抑郁症中5-羟色胺传播较低的信念,并且对治疗有影响。
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目标设定和目标实现:S
摘要目的:对目标设定和目标达到缩放的过程的叙述性回顾,因为在患有严重抑郁症(MDD)的人们的常规护理中,实用的方法来操作和实施共享决策制定原则(SDM)。方法:我们使用与MDD和目标设定或目标达到标准的关键术语搜索了以英文发表的临床研究的电子数据库。详细考虑了MDD中目标设定的两项临床研究,以说明目标设定方法的实用性。结果:尽管对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的SDM被广泛建议,但人们普遍认为,迄今为止,它已被多样地实施。在其他医学领域,目标设定的主体是吸引患者,促进动机并协助恢复过程的既定方法。对于患有MDD的人来说,目标设定的概念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很少的研究评估了其临床实用性。对MDD的Vortioxetine进行的两项临床研究表明,目标达到缩放的实用性是评估功能改善对患者的功能改善的适当结果。结论:目标设定是将SDM原理转变为临床实践的现实的一种务实方法,并与恢复原则保持一致,该原则涵盖了自我饮食,自我管理,个人成长,赋权和选择的概念。积累证据端口将目标达到缩放作为适当的个性化结果指标,以用于临床试验。
使用神经元起源的细胞外囊泡探索躁郁症抑郁症的成年人脑胰岛素抵抗
通讯作者:Dimitrios Kapogiannis,医学博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老化研究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51 Bayview Blvd,Ste 8C228,Baltimore,MD 21224,Kapogiannisnisd@mail.nih.nih.nih.nih.gov。*这些作者共享第一作者。±这些作者分享了高级作者资格作者声明Drs。Mansur和Kapogiannis可以完全访问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并负责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分析的准确性。Concept and design: Mansur, Lee, Rosenblat, Brietzke, Suppes, McIntyre, Kapogiannis Acquisition,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 of clinical data: Mansur, Subramaniapillai, Lee, Iacobucci, Rodrigues, Cosgrove, Kramer, Suppes, McIntyre Acquisition,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 of biomarker data: Mansur, Delgado-Peraza, Chawla, Nogueras-Ortiz, McIntyre, Kapogiannis Drafting of the manuscript: Mansur, Delgado-Peraza, McIntyre, Kapogiannis Critical revision of the manuscript for important intellectual content: Rosenblat, Brietzke, Suppes, Raison, Fagiolini, Rasg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ansur Obtained funding: Mansur,McIntyre,Kapogiannis行政,技术或物质支持:Subramaniaiaiapillai,Lee,Cosgrove,McIntyre,Kapogiannis,Kapogiannis监督:McIntyre,Kapogiannis
基于AI的方法评估业务领导者的抑郁
研究人员研究了首席执行官抑郁症与职业成果,薪酬和激励措施的关系。他们的发现表明,抑郁症较高的首席执行官往往会获得更大的补偿套餐,而更多的薪酬与绩效有关。此外,抑郁症与CEO离开对绩效结果的敏感性更强。
使用神经元起源的细胞外囊泡探索躁郁症抑郁症的成年人脑胰岛素抵抗
通讯作者:Dimitrios Kapogiannis,医学博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老化研究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51 Bayview Blvd,Ste 8C228,Baltimore,MD 21224,Kapogiannisnisd@mail.nih.nih.nih.nih.gov。*这些作者共享第一作者。±这些作者分享了高级作者资格作者声明Drs。Mansur和Kapogiannis可以完全访问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并负责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分析的准确性。Concept and design: Mansur, Lee, Rosenblat, Brietzke, Suppes, McIntyre, Kapogiannis Acquisition,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 of clinical data: Mansur, Subramaniapillai, Lee, Iacobucci, Rodrigues, Cosgrove, Kramer, Suppes, McIntyre Acquisition,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 of biomarker data: Mansur, Delgado-Peraza, Chawla, Nogueras-Ortiz, McIntyre, Kapogiannis Drafting of the manuscript: Mansur, Delgado-Peraza, McIntyre, Kapogiannis Critical revision of the manuscript for important intellectual content: Rosenblat, Brietzke, Suppes, Raison, Fagiolini, Rasg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ansur Obtained funding: Mansur,McIntyre,Kapogiannis行政,技术或物质支持:Subramaniaiaiapillai,Lee,Cosgrove,McIntyre,Kapogiannis,Kapogiannis监督:McIntyre,Kapogiannis
评估大脑和肠道认知电生理学的效用,以早期预测主要抑郁症的治疗结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全球约有5%的成年人患有临床抑郁症,在印度,大约是4.5%的人。 口服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常见治疗方法。 但是,在第一次试验中,有一半以上的治疗方法对药理治疗策略没有响应,可能需要使用其他药物进行切换或增强。 在更快的时间表中,需要精确模型来达到个性化的治疗策略。 使用临床信息以及脑电图(EEG)数据显示出一些早期模型,显示出良好的表现,可以预测抑郁症的早期治疗结果。 然而,这些研究所确定的关键特征,包括抑郁症患者的差异额叶theta功率和额叶α不对称的存在,由于可解释性和稳健性的矛盾,近期挑战:当theta和alpha频率信号被嘲笑时,与他们的周期性成分相关,并不是在其质量成分的情况下,估计的估计并不是在其periodigic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许多早期研究已经报道了抑郁症的肠道异常,但尚未用于抑郁症的预测或预后。 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双重的:首先确定可以早期预测治疗结果的特征,并为不同的患者亚组解释它们,其次是了解纵向数据收集和肠脑相互作用的实用性,以预测治疗结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全球约有5%的成年人患有临床抑郁症,在印度,大约是4.5%的人。口服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常见治疗方法。 但是,在第一次试验中,有一半以上的治疗方法对药理治疗策略没有响应,可能需要使用其他药物进行切换或增强。 在更快的时间表中,需要精确模型来达到个性化的治疗策略。 使用临床信息以及脑电图(EEG)数据显示出一些早期模型,显示出良好的表现,可以预测抑郁症的早期治疗结果。 然而,这些研究所确定的关键特征,包括抑郁症患者的差异额叶theta功率和额叶α不对称的存在,由于可解释性和稳健性的矛盾,近期挑战:当theta和alpha频率信号被嘲笑时,与他们的周期性成分相关,并不是在其质量成分的情况下,估计的估计并不是在其periodigic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许多早期研究已经报道了抑郁症的肠道异常,但尚未用于抑郁症的预测或预后。 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双重的:首先确定可以早期预测治疗结果的特征,并为不同的患者亚组解释它们,其次是了解纵向数据收集和肠脑相互作用的实用性,以预测治疗结果。口服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常见治疗方法。但是,在第一次试验中,有一半以上的治疗方法对药理治疗策略没有响应,可能需要使用其他药物进行切换或增强。在更快的时间表中,需要精确模型来达到个性化的治疗策略。使用临床信息以及脑电图(EEG)数据显示出一些早期模型,显示出良好的表现,可以预测抑郁症的早期治疗结果。然而,这些研究所确定的关键特征,包括抑郁症患者的差异额叶theta功率和额叶α不对称的存在,由于可解释性和稳健性的矛盾,近期挑战:当theta和alpha频率信号被嘲笑时,与他们的周期性成分相关,并不是在其质量成分的情况下,估计的估计并不是在其periodigic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许多早期研究已经报道了抑郁症的肠道异常,但尚未用于抑郁症的预测或预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双重的:首先确定可以早期预测治疗结果的特征,并为不同的患者亚组解释它们,其次是了解纵向数据收集和肠脑相互作用的实用性,以预测治疗结果。大约有161名参与者(幼稚的患者= 99)注册了我们的纵向研究,涵盖了三次访问,我们的目的是调查访问1(基线)和访问2(7-10天内)是否可以预测3(30天后)中的抗抑郁治疗结果。在消耗后,在访问2(患者= 42)中收集了来自89名参与者的脑电图和电视画学数据,在访问中收集61个参与者(患者= 21)。我们在大脑和肠道中使用电生理特征以及临床数据来训练简单的预测模型,并且能够可靠地预测特异性为78%和灵敏度为84%的抑郁药物的无反应。对治疗结果的重要特征进行了排名,完全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可扩展的全身认知工具,用于指导其药物策略。
消费多巴胺受体1激动剂SKF-38393可在C57BL/6J小鼠中以性别特异性方式降低恒定光诱导的多动症,抑郁状和类似焦虑的行为
夜间的人造光暴露,包括恒定光(LL),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环境发生,与人类和动物模型的情绪和认知障碍受损有关。多巴胺和多巴胺1受体众所周知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和情绪。这项研究研究了LL对男性和雌性C57BL/6J小鼠的焦虑状,抑郁样和认知行为的影响,并评估了SKF-38393的消耗是否可以缓解这些负面行为抗果。小鼠暴露于LL或标准的12:12光:暗周期(LD)6周,亚组接受SKF-38393或水。所有小鼠的昼夜节律都不断监测,并被置于行为测试中,这些测试测定了它们的焦虑,抑郁症,学习和记忆行为。行为分析表明,LL的多动症和焦虑行为会增加,这两种性别的SKF-38393消费均可减轻这种行为。此外,雄性小鼠在LL下表现出Anhedonia,这是SKF-38393减轻的,而雌性小鼠对LL诱导的Anhedonia具有抵抗力。性别差异在流体消耗中出现,独立于照明条件,女性消耗了更多的SKF-38393,以及对DA的反应行为,包括新颖的对象识别和探索。这些结果表明,多巴胺1受体激动剂的低剂量口服消耗可以改善LL暴露的某些负面行为影响。这项研究强调了影响情绪和行为的慢性光,多巴胺和性别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这表明多巴胺1受体激动剂在调节行为结果中的潜在调节作用。
o r i g i g i n a l r e s a r c h准备出院,出院质量,外科手术患者的出院质量,焦虑和抑郁症
目的:这项定量研究旨在确定出院教学,焦虑,抑郁以及各种人口统计学和疾病相关的因素是否可以预测中国西部地区宫颈癌手术患者的出院准备。方法: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5月,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来对新疆的高等级A专业医院的宫颈癌手术患者进行调查表。调查包括一份患者一般信息问卷,出院教学量表(QDTS),广义焦虑症7-项目量表(GAD-7),一份调查表评估了在增强的康复(ARAS)模型恢复(ARAS)模型和PHENAIRE-9(PHQ-9)(恢复后的康复(ARAS)中,妇科恶性肿瘤肿瘤手术患者的准备就绪。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用于识别影响排放准备就绪的因素。结果:总共参加了180名宫颈癌手术患者,在ERAS模型下的妇科恶性肿瘤排出就绪问卷中的平均得分为190.46±25.36。多个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教育水平,慢性疾病,药物使用,出院教学质量和抑郁情绪是宫颈癌手术患者出院准备的重要预测指标。结论:发现宫颈癌手术患者的总体排出准备状态处于中等状态。护士应优先考虑具有较低教育水平,慢性病,抑郁症和需要药物治疗后的患者。应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出院教学的质量,从而提高患者的出院准备。关键词:宫颈癌,手术,出院准备,出院指令的质量,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