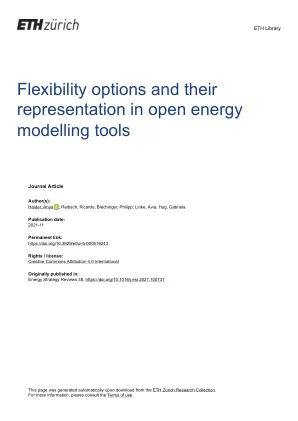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灵活性选项及其在开放式能源建模工具中的表示
为了实现气候目标,未来的能源系统必须严重依赖风能和光伏 (PV) 等可变可再生能源 (VRES)。随着 VRES 份额的增加,灵活性以及不同灵活性选项的智能相互作用等主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分析灵活性选项和增强未来能源系统设计的一种方法是使用能源系统建模工具。尽管存在各种可公开访问的模型,但并没有明确的评估来评估这些工具中如何体现灵活性。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本文提取了灵活性表示的关键因素,并引入了灵活性和影响因素的新分类。为了评估当前的建模状况,我们向开放能源建模工具的开发人员发送了一份调查问卷,并使用新推出的开放 ESM 灵活性评估工具 (OpFEl) 进行分析,这是一种开源评估算法,用于评估工具中不同灵活性选项的表示。结果显示,各种不同的工具涵盖了灵活性的大多数方面。可以看出,出现了包括部门耦合元素的趋势。然而,当前模型中仍未充分体现储能和网络类型灵活性以及涉及系统运行的方面,应更详细地纳入其中。没有一个模型能够高度涵盖所有类别的灵活性选项,但通过软耦合将不同模型组合起来可以作为整体灵活性评估的基础。这反过来又可以基于 VRES 对能源系统进行详细评估。
太阳能和电网灵活性对马来西亚未来的电力可负担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
马来西亚半岛占该国电力需求的 74%,其每日需求曲线呈现“双峰”特征,即白天下午 4 点和晚上 8 点。马来西亚拥有大量未开发的太阳能资源,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利用太阳能满足白天高峰期的需求,而水电和电池储能等其他选择可以补充太阳能,满足晚间高峰期的需求。到 2023 年,太阳能和水电合计占白天高峰期发电量的 10%,而水电为满足晚间高峰期贡献了 7%。在储能系统必不可少之前,马来西亚半岛的电网可以容纳约 2.4 吉瓦的太阳能(高达电网渗透率的 20%)。
某些药植物的抗糖尿病活性
从人类的创造中,很有可能会影响疾病,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开始使用各种成分以及植物,动物,昆虫或自然资源来治愈不同的疾病。可以预期,数千年前的植物意识到植物的重要性。植物用于自然方式改善健康。植物不仅用于治疗疾病,而且还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改善生活,例如改善收入和愉快的生活方式。今天疾病正在传播。糖尿病通常是目前的综合症,它以令人恐惧的速度上升,并且已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疾病之一。1是一种内分泌结构的疾病,由于胰岛素排放,成就或共同的全部或相对不足,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疾病。糖尿病正在影响世界各地数百万的人,影响糖尿病的人数日益增加。控制这一越来越多的人数已成为一个挑战。由于发达国家数百万人死亡,这对健康而言越来越造成问题,并且在许多崛起和最近工业化的国家中构成威胁。在不同的国家,其导致死亡的比率不同。糖尿病将是2030年的第七名死亡来源。
清洁灵活性是管理清洁电力系统的大脑
是最需要的,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由于锂电池变得更容易生产,其成本大幅下降●快速创新意味着新的电池技术,如LFP(消除了对镍和钴的需求)和钠离子(消除了对锂的需求)正在迅速进入市场,带来成本和性能的巨大改进●模块化技术,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在电网规模(高达几吉瓦)以及较小规模(几千瓦)的住宅或商业建筑中部署,以增强现场生产的能源消耗
活性混合等离子材料材料
1。H. T. Chen,J。Padilla,J。M. O. Zide,A。C. Gossard,A。J. J. J. J. J. 2。 Express 17(2),819–827(2009)。 3。 H. T. Chen,J。F。O'Hara,Azad,A。J. J. 光子学2(5),295–298(2008)。 4。 W. J. J. Patilla,A。J。Jt.Strete,M。Lee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96(10),107401(2006)。 5。 N.-H. Shen,M。Massauti,M。Gokkavas,J.-M。 Manceau,E。Ozbay,M。Kafesaki,T. 修订版 Lett。 106(3),037403(2011)。 6。 Z. Tian,R。 Singh,J。Ha,J。Gu,Q. Xing,J。Wu和W. Zhang, Lett。 35(21),3586–3588(2010)。 7。 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H. T. Chen,J。Padilla,J。M. O. Zide,A。C. Gossard,A。J. J. J. J. J.2。Express 17(2),819–827(2009)。3。H. T. Chen,J。F。O'Hara,Azad,A。J. J. 光子学2(5),295–298(2008)。 4。 W. J. J. Patilla,A。J。Jt.Strete,M。Lee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96(10),107401(2006)。 5。 N.-H. Shen,M。Massauti,M。Gokkavas,J.-M。 Manceau,E。Ozbay,M。Kafesaki,T. 修订版 Lett。 106(3),037403(2011)。 6。 Z. Tian,R。 Singh,J。Ha,J。Gu,Q. Xing,J。Wu和W. Zhang, Lett。 35(21),3586–3588(2010)。 7。 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H. T. Chen,J。F。O'Hara,Azad,A。J. J.光子学2(5),295–298(2008)。4。W. J. J. Patilla,A。J。Jt.Strete,M。Lee和R. D. Averitt,修订版Lett。 96(10),107401(2006)。 5。 N.-H. Shen,M。Massauti,M。Gokkavas,J.-M。 Manceau,E。Ozbay,M。Kafesaki,T. 修订版 Lett。 106(3),037403(2011)。 6。 Z. Tian,R。 Singh,J。Ha,J。Gu,Q. Xing,J。Wu和W. Zhang, Lett。 35(21),3586–3588(2010)。 7。 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Lett。96(10),107401(2006)。5。N.-H. Shen,M。Massauti,M。Gokkavas,J.-M。 Manceau,E。Ozbay,M。Kafesaki,T. 修订版 Lett。 106(3),037403(2011)。 6。 Z. Tian,R。 Singh,J。Ha,J。Gu,Q. Xing,J。Wu和W. Zhang, Lett。 35(21),3586–3588(2010)。 7。 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N.-H. Shen,M。Massauti,M。Gokkavas,J.-M。 Manceau,E。Ozbay,M。Kafesaki,T.修订版Lett。 106(3),037403(2011)。 6。 Z. Tian,R。 Singh,J。Ha,J。Gu,Q. Xing,J。Wu和W. Zhang, Lett。 35(21),3586–3588(2010)。 7。 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Lett。106(3),037403(2011)。6。Z. Tian,R。 Singh,J。Ha,J。Gu,Q. Xing,J。Wu和W. Zhang, Lett。 35(21),3586–3588(2010)。 7。 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Z. Tian,R。 Singh,J。Ha,J。Gu,Q. Xing,J。Wu和W. Zhang,Lett。 35(21),3586–3588(2010)。 7。 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 修订版 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Lett。35(21),3586–3588(2010)。7。H. Tao,A。C. Strait,K。Fan,W。J. Patilla,X。Zhang和R. D. Averitt,修订版Lett。 103(14),147401(2009)。 8。 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Lett。103(14),147401(2009)。8。Express 18(13),13425–13430(2010)。R. Singh,E。Plum,W。Zhang和N. I. 9。 T. Driscoll,H.-T。 Kim,B.-G。 Chae,B.-J。 Kim,Y.-W。 Lee,N。M. Jokerst,S。Palit,D。R. Smith,M。Di Ventra和D. N. Basov,“记忆超材料”,《科学》 325(5947),1518-1521(2009)。 10。 J. Han和A. Lakhtakia,“可热可调的Terahertz超植物的半导体拆分谐振器”,J。Mod。 选择。 56(4),554–557(2009)。 11。 J. Gu,R。Singh,Z。Tian,W。Cao,Q. Xing,M。He,J。W。Zhang,J。Han,H.-T。 Chen和W. Zhang,“ Terahertz超导体超材料”,Appl。 物理。 Lett。 97(7),071102(2010)。 12。 R. Singh,I。 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 物理。 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R. Singh,E。Plum,W。Zhang和N. I.9。T. Driscoll,H.-T。 Kim,B.-G。 Chae,B.-J。 Kim,Y.-W。 Lee,N。M. Jokerst,S。Palit,D。R. Smith,M。Di Ventra和D. N. Basov,“记忆超材料”,《科学》 325(5947),1518-1521(2009)。 10。 J. Han和A. Lakhtakia,“可热可调的Terahertz超植物的半导体拆分谐振器”,J。Mod。 选择。 56(4),554–557(2009)。 11。 J. Gu,R。Singh,Z。Tian,W。Cao,Q. Xing,M。He,J。W。Zhang,J。Han,H.-T。 Chen和W. Zhang,“ Terahertz超导体超材料”,Appl。 物理。 Lett。 97(7),071102(2010)。 12。 R. Singh,I。 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 物理。 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T. Driscoll,H.-T。 Kim,B.-G。 Chae,B.-J。Kim,Y.-W。 Lee,N。M. Jokerst,S。Palit,D。R. Smith,M。Di Ventra和D. N. Basov,“记忆超材料”,《科学》 325(5947),1518-1521(2009)。 10。 J. Han和A. Lakhtakia,“可热可调的Terahertz超植物的半导体拆分谐振器”,J。Mod。 选择。 56(4),554–557(2009)。 11。 J. Gu,R。Singh,Z。Tian,W。Cao,Q. Xing,M。He,J。W。Zhang,J。Han,H.-T。 Chen和W. Zhang,“ Terahertz超导体超材料”,Appl。 物理。 Lett。 97(7),071102(2010)。 12。 R. Singh,I。 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 物理。 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Kim,Y.-W。 Lee,N。M. Jokerst,S。Palit,D。R. Smith,M。Di Ventra和D. N. Basov,“记忆超材料”,《科学》 325(5947),1518-1521(2009)。10。J. Han和A. Lakhtakia,“可热可调的Terahertz超植物的半导体拆分谐振器”,J。Mod。选择。56(4),554–557(2009)。 11。 J. Gu,R。Singh,Z。Tian,W。Cao,Q. Xing,M。He,J。W。Zhang,J。Han,H.-T。 Chen和W. Zhang,“ Terahertz超导体超材料”,Appl。 物理。 Lett。 97(7),071102(2010)。 12。 R. Singh,I。 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 物理。 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56(4),554–557(2009)。11。J. Gu,R。Singh,Z。Tian,W。Cao,Q. Xing,M。He,J。W。Zhang,J。Han,H.-T。 Chen和W. Zhang,“ Terahertz超导体超材料”,Appl。 物理。 Lett。 97(7),071102(2010)。 12。 R. Singh,I。 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 物理。 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J. Gu,R。Singh,Z。Tian,W。Cao,Q. Xing,M。He,J。W。Zhang,J。Han,H.-T。 Chen和W. Zhang,“ Terahertz超导体超材料”,Appl。物理。Lett。 97(7),071102(2010)。 12。 R. Singh,I。 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 物理。 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Lett。97(7),071102(2010)。12。R. Singh,I。 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 物理。 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R. Singh,I。A. I. Al-Naib,Y. Yang,D。RoyChowdhury,W。Cao,C。Rockstuhl,T。Ozaki,R。Morandotti和W.物理。Lett。 99(20),201107(2011)。 13。 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 修订版 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Lett。99(20),201107(2011)。13。H. T. Chen,H。Yang,R。Singh,J。F. O'Hara,A。K. Azad,S。A. Trugman,Q。X. Jia和A. J. Taylor,“调整高温超导向超过的共鸣Terahertz Metamatametials中的共鸣,”修订版Lett。 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Lett。105(24),247402(2010)。 14。 B. 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105(24),247402(2010)。14。B.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 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 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B. Jin,C。H。Zhang,S。Engelbrecht,A。Pimenov,J.B. Wu,Q. Y. Xu,C。H. Cao,J。Chen,W。W. Xu,L。Kang和P. H. Wu,“低损失和磁场可触及的超导超导Terahertz-Metamaterial”,Opt。Express 18(16),17504– 17509(2010)。
植物的植物化学研究和抗氧化活性。 ... 第一章:书目研究
figuren°3:正常细胞对癌细胞对活性氧的敏感性的模型………………………………………………………………………
头颈squa中PHT-427抑制剂的聚合物纳米颗粒的体内抗肿瘤活性
关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肿瘤发生的摘要最近的研究揭示了几种分子途径失调。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信号传导途径经常在HNSCC中激活,使其成为疗法的有吸引力的靶标。PHT-427是PI3K的双重抑制剂,也是AKT/PDK1的哺乳动物靶标。这项研究评估了抑制剂PHT-427的抗癌疗效,该抑制剂基于肿瘤内注射中施用α-TOS(NP-427)中的聚合物纳米粒子(NP)(NP),该抗癌器的疗效(NP-427),该抑制剂纳米粒子(NP-427)的抗癌纳米颗粒(NP-427)施加到肿瘤内注射中的抗癌纳米粒子(NP-427)。合成了基于N-乙烯基吡咯烷酮(VP)的块共聚物和α-TOS(MTOS)的甲基丙烯酸衍生物(MTOS)的纳米载体系统,并将PHT-427加载到递送系统中。首先,我们通过测量肿瘤的体积,小鼠体重,存活以及肿瘤溃疡和坏死的发展来评估NP-427对肿瘤生长的影响。此外,我们测量了PI3KCA/AKT/PDK1基因表达,PI3KCA/AKT/PDK1蛋白水平,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肿瘤组织中的血管生成。PHT-427封装提高了药物功效和安全性,如肿瘤体积减少,PI3K/AKT/PDK1途径的降低所证明,并改善了小鼠异种移植模型中的抗肿瘤活性和坏死诱导。EGFR和血管生成标记物(因子VIII)表达显着降低。在肿瘤部位施用封装的PHT-427证明有望用于HNSCC治疗。
循环生物活性 - 细菌-DNA-IS相关 - 与...
引言公共可变免疫效率(CVID),最普遍的症状性原发免疫剂效应,其特征是低水平的血清IgG,IgA和/或IgM,并且缺乏特定抗体的产生(1-3)。与其他原发性免疫缺陷一样,CVID患者易于反复发生严重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50%的CVID患者会产生额外的炎性互补(4,5)。 这些非感染性表现包括自身免疫性,间质性肺部疾病,肠道,肝脏结节再生增生,全身性肉芽肿性疾病,淋巴样增生和淋巴样恶性肿瘤(4-7)。 这些并发症是一个主要的临床挑战,因为标准IgG替代疗法并未大大改善它们。 整体上,炎症状况导致CVID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估计增加了11倍(5)。 最近的研究已经鉴定出遗传缺陷导致20%–25%的个体中B细胞发育丧失和免疫调节中的其他缺陷,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CVID中炎性复杂性的发病机理仍然无法解释(8,9)。 我们先前证明了通过mRNA转录pro填充的这些个体中IFN相关途径的明显上调(10)。 这个IFN签名还区分了具有炎症条件的CVID的个体与其他具有CVID和健康对照的个人。 但是,这些免疫反应的刺激尚不清楚。 菌群特异性IgG已在小鼠中检测到,健康与其他原发性免疫缺陷一样,CVID患者易于反复发生严重感染。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50%的CVID患者会产生额外的炎性互补(4,5)。这些非感染性表现包括自身免疫性,间质性肺部疾病,肠道,肝脏结节再生增生,全身性肉芽肿性疾病,淋巴样增生和淋巴样恶性肿瘤(4-7)。这些并发症是一个主要的临床挑战,因为标准IgG替代疗法并未大大改善它们。整体上,炎症状况导致CVID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估计增加了11倍(5)。最近的研究已经鉴定出遗传缺陷导致20%–25%的个体中B细胞发育丧失和免疫调节中的其他缺陷,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CVID中炎性复杂性的发病机理仍然无法解释(8,9)。我们先前证明了通过mRNA转录pro填充的这些个体中IFN相关途径的明显上调(10)。这个IFN签名还区分了具有炎症条件的CVID的个体与其他具有CVID和健康对照的个人。但是,这些免疫反应的刺激尚不清楚。菌群特异性IgG已在小鼠中检测到,健康为了确定这种病理IFN签名的起源,我们使用了质量细胞仪,发现在外周血和胃肠道和胃肠道患者中,IFN-γ,IL-17A和IL-22呈阳性的先天淋巴样细胞(ILCS)呈阳性,患有CVID的患者呈伴有cVID的患者(11)。ilcs通常在宿主 - 常识稳态中起重要作用(12),它们的过度活性和/或增殖似乎有助于CVID中的系统性和器官特异性炎症。体液免疫有助于在实验动物模型中对共生生物的解剖遏制(13)。在小鼠中,已显示分泌的IgA和IgM限制了来自粘膜室的细菌易位(14-17)。
胶原蛋白羟化酶在培养的成纤维细胞中的无活性前体的免疫学证据
摘要在正常生长过程中,在培养的小鼠成纤维细胞(L-929细胞)中,在培养的小鼠成纤维细胞(L-929细胞)中,在其他条件下以及导致酶活性增加的培养小鼠成纤维细胞(L-929细胞)中,已使用一种对大鼠胶原蛋白羟化酶的特异性抗体。胶原蛋白羟化酶活性每毫克细胞蛋白的活性增加了24倍,因为细胞通过对数发展到生长的固定阶段,而免疫反应性蛋白的细胞融合仅略有变化。在早期对数阶段的细胞中获得了相似的结果,其中通过细胞浓度或乳酸处理刺激酶活性,而没有相应的细胞抗原变化。还显示,这些成纤维细胞中的酶无活性抗原有效地竞争了具有部分纯化酶的抗体结合位点。可以得出结论,早期含量的成纤维细胞包含一种胶原蛋白脯氨酸羟化酶的非活性形式,这可能是功能性酶的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