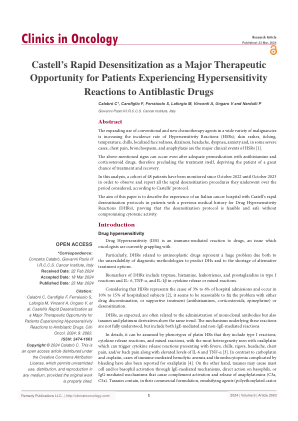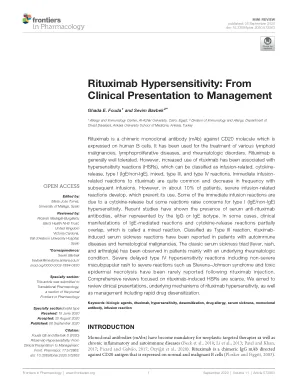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卡斯特尔的快速脱敏法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
具体而言,根据铂类 HR 的表型可推测其包括 I 型反应、细胞因子释放反应和混合反应,其中奥沙利铂的异质性最高,可引发细胞因子释放反应,表现为发烧、发冷、寒战、头痛、胸痛和/或背痛,同时伴有 IL-6 和 TNF-α 水平升高 [3]。与卡铂和顺铂不同,奥沙利铂还报道了免疫介导的溶血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并发出血的病例 [4]。另一方面,紫杉烷可能通过 IgE 介导的机制、对嗜碱性粒细胞的直接作用或 IgG 介导的机制引起肥大细胞和/或嗜碱性粒细胞活化,从而导致补体活化和过敏毒素 (C3a、C5a) 的释放。紫杉烷在其商业制剂中含有乳化剂(聚乙氧基化蓖麻油
AR+、HRAS/PIK3CA 共突变涎管癌病例系列的靶向治疗
结果:从 MTB 中确定了 4 名具有 AR+ HRAS / PIK3CA 共突变 SDC 和临床随访数据的患者。从文献中确定了另外 9 名具有临床随访的患者。除了 AR 过表达和 HRAS 和 PIK3CA 变异之外,还确定了 PD-L1 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 > 每兆碱基 10 个突变作为其他潜在可靶向变异。在可评估的患者中,7 名患者开始接受雄激素剥夺疗法 (ADT)(1 名部分缓解 (PR)、2 名稳定疾病 (SD)、3 名进展性疾病 (PD)、2 名不可评估),6 名患者开始接受替比法尼治疗(1 名 PR、4 名 SD、1 名 PD)。各有一名患者接受了免疫检查点抑制(混合反应)以及替比法尼和 ADT(SD)以及阿哌沙布和 ADT(PR)的联合疗法治疗。
精准肿瘤学的变革性工具
肿瘤免疫疗法 (IO) 已显著改善多种癌症的治疗效果,从而导致其在各种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此类治疗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 细胞、免疫细胞因子以及溶瘤病毒,所有这些治疗都从本质上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更有效地靶向恶性肿瘤。然而,IO 通常会导致非典型反应模式,而这些模式无法通过传统的基于大小的成像反应标准(如 RECIST(实体肿瘤反应评估标准)[1])有效捕捉。这些现象总体上使治疗效果的评估变得复杂,可能包括假进展(肿瘤大小最初增加,随后最终出现反应)、混合反应(一些病变缩小而另一些病变生长)、超进展(治疗后肿瘤快速生长)和远隔效应(一个病变的局部治疗导致远处转移消退)。新的响应和进展模式强调需要更加量身定制
免疫疗法监测的MRI技术
摘要MRI是用于癌症诊断和治疗监测的广泛可用的临床工具。MRI使用多种对比机制提供出色的软组织成像,并且可以非侵入性检测组织代谢产物。这些方法可用于将癌症与正常组织区分开,以分层肿瘤的侵袭性,并确定肿瘤及其微环境内的变化,以应对治疗。在这篇综述中,将讨论MRI在免疫疗法监测中的作用,以及将来如何利用它来解决免疫疗法引起的一些独特的临床问题。例如,MRI可以在鉴定伪雌性,混合反应,T细胞浸润,细胞跟踪以及与这些药物相关的某些特征性免疫相关事件中发挥作用。将审查开发MRI成像生物标志物进行免疫疗法时要考虑的因素。最后,将讨论每种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将来临床转化为常规临床护理的挑战。鉴于在广泛的癌症中使用免疫疗法的使用越来越多,并且MRI检测与成功反应免疫疗法相关的微观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能力,该技术在将来对这些应用中有很大的广泛和常规利用具有很大的潜力。
利妥昔单抗超敏反应:从临床表现到管理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针对在人B细胞上表达的CD20分子的嵌合单克隆抗体(MAB)。它已用于治疗各种淋巴恶性肿瘤,淋巴增生性疾病和风湿病。利妥昔单抗通常耐受性良好。然而,利妥昔单抗的使用增加与超敏反应(HSR)有关,可以将其分类为输注相关,细胞因子释放,I型(IGE/非IgE),混合,III型和IV型反应。对利妥昔单抗的直接输注反应非常普遍,随后输注频率下降。然而,在约10%的患者中,出现了严重的输注反应,从而阻止了其使用。某些直接输注反应是由于细胞因子释放引起的,但某些反应引起了对I型(IgE/非IgE)超敏反应的关注。最近的研究表明,以IgG或IgE同型为代表的血清抗利妥昔单抗抗体存在。在某些情况下,IgE介导的反应和细胞因子释放反应的临床表现部分重叠,这称为混合反应。分类为III型反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血液学恶性肿瘤患者中已经报道了利妥昔单抗诱导的血清疾病反应。在主要具有潜在的风湿病状态的患者中,已经观察到经典的血清疾病三合会(发烧,皮疹和关节痛)。涉及利妥昔单抗引起的HSR的全面评论很少。严重的延迟IV型超敏反应,包括对史蒂文斯(Stevens)等严重反应的非严重性皮疹 - 约翰逊综合征和有毒的表皮坏死术后,rituximab注射后很少报道。我们旨在审查利妥昔单抗超敏反应的临床表现,潜在的机制以及包括快速药物脱敏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