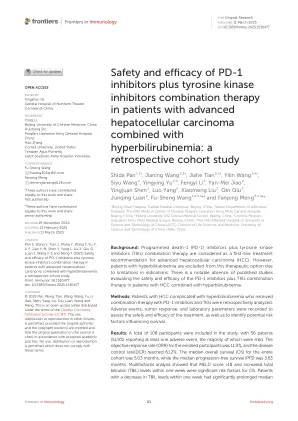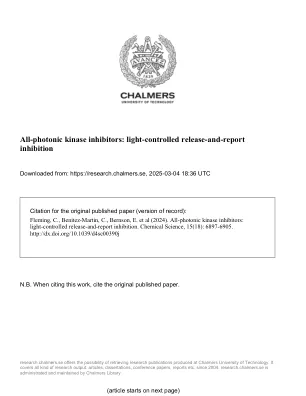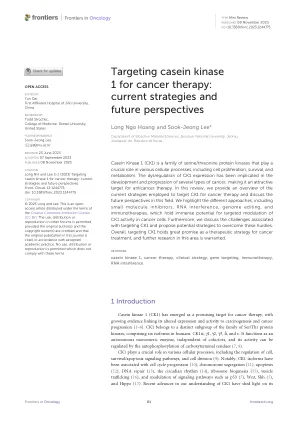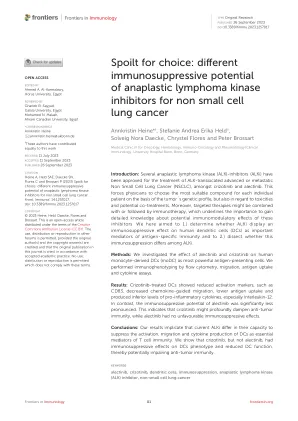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拷贝数畸变驱动激酶重新布线,导致癌症的遗传脆弱性
体细胞DNA拷贝数变化(CNV)在癌症中很普遍,并且可以驱动癌症进展,尽管在改变细胞信号状态下通常具有未表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整合了5,598个肿瘤样品的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学数据,以鉴定导致异常信号转导的CNV。由此产生的关联概括了已知的激酶 - 基底关系,并进一步的网络分析优先考虑可能因果基因。在癌细胞系中复制了43%,包括在多种肿瘤类型中鉴定出的44种强大的基因磷材料。实验验证了几个预测的河马信号调节剂。使用RNAi,CRISPR和药物筛选数据,我们发现癌细胞系中激酶成瘾的证据,确定靶向激酶依赖性细胞系的抑制剂。我们建议基因的拷贝数状态,作为激酶抑制差异影响的有用预测指标,这是一种抗癌疗法的策略。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的克隆进化
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感染会导致人类致命的肺部炎症性疾病。相反,骆驼和蝙蝠是主要的储层宿主,耐受的MERS-COV复制而不患有临床疾病。在这里,我们从MERS-COV康复的骆驼中分离了宫颈淋巴结(LN)细胞,并用两种不同的病毒菌株(进化枝B和C)脉冲它们。病毒复制,但安装了细胞免疫反应。让人联想的Th1反应(IFN-G,IL-2,IL-12),并伴随着抗病毒反应的明显且短暂的峰值(I型IFNS,IFNS,IFN-L 3,ISGS,ISGS,PRRS和TFS)。重要的是,炎症细胞因子(TNF-A,IL-1 B,IL-6,IL-8)的表达或膨胀成分(NLRP3,CASP1,Pycard)的表达被抑制。讨论了IFN-L 3在骆驼物种中对平衡量弹性过程以及桥接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的作用。我们的发现阐明了有关在没有临床疾病的情况下如何控制MERS-COV的关键机制。
胰岛素调节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激酶(MEK),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和酪蛋白激酶在细胞核中:Possibl
在大鼠大脑皮层中研究了腺苷酸环化酶和鸟嘌呤核苷酸结合蛋白(G蛋白)在锂对脑功能的慢性作用中的可能作用。发现,用锂(具有治疗相关的血清水平为1 mm)对大鼠的慢性治疗增加了mRNA和蛋白质的水平,用于钙调蛋白敏感(1型)和钙调蛋白敏感(2型)形式的腺苷酸环化酶和抑制蛋白质的mRNA和蛋白质水平降低,用于抑制性gja2 gja2 gja2 gja2 gja2 gja2。慢性锂不会改变其他G-蛋白亚基的水平,包括GA,GSA和GJF。在短期锂治疗(最终血清水平为-1 mM)或以较低剂量的锂(血清水平为-0.5 mm)下,h含腺苷酸环化酶和GIA的锂调节均未观察到短期锂治疗(最终血清水平为-1 mm)。结果表明,腺苷酸环化酶的上调和GJA的下调可能代表了分子机制的一部分,锂可以改变脑功能并在治疗情感障碍的治疗中发挥其临床作用。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 PD-1 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肝细胞癌 (HCC) 是一种高发癌症,在全球癌症死亡原因中位居第三 ( 1 )。尽管 HCC 监测方案不断进步,但由于缺乏早期临床表现,大约 80% 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是中期或晚期,从而错过了根治性切除的机会。尽管如此,HCC 有多种治疗方法,具体取决于患者的临床情况、肿瘤分期和保留的肝功能 ( 2 )。经动脉化疗栓塞术 (TACE) 是针对中期和晚期 HCC 的推荐局部治疗 ( 3 )。TACE 不仅可以与化疗相结合,还可以与肝脏肥大诱导方法相结合 ( 4 )。然而,TACE 的有效性随着手术次数的增加而降低,每次手术后都会观察到更高的疾病进展率 ( 1、3、5、6 )。这种现象被称为“ TACE 难治性”,是由日本肝病学会和日本肝癌研究组于 2014 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 7 , 8 )。从那时起,它作为晚期 TACE 难治性肝细胞癌的治疗选择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了提高 TACE 的疗效,人们尝试了各种联合肝脏治疗和全身治疗,例如消融、放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和免疫疗法 ( 9 )。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是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治疗药物,但其生存获益有限 ( 10 )。针对程序性死亡-1 (PD-1) 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CI) 在 CheckMate040 和 KEYNOTE-224 等 I/II 期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 11, 12 )。然而,在 CheckMate 459 和 KEYNOTE-240 两项 III 期试验中,抗 PD-1 疗法并未显示出优于标准治疗 ( 13 , 14 )。最近的研究推荐将抗 PD-(L)1 药物与抗 VEGF 抗体或 TKI 联合治疗作为晚期 HCC 的一线治疗,因为它具有良好的疗效。TACE 诱导的肿瘤组织坏死引起的肿瘤抗原释放可能会增强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此外,TACE 后的缺氧反应可以进一步刺激肿瘤血管生成 ( 15 )。考虑到这些因素,将 TACE 与 TKI 和 PD-1 抑制剂联合使用有望在 TACE 难治性晚期 HCC 病例中取得积极成果 ( 16 )。上述因素表明,将 TACE 与 TKI 以及 PD-1 抑制剂联合使用可在 TACE 难治性晚期 HCC 病例中取得良好效果。结合 TACE、TKI 和 PD-1 抑制剂的治疗方法可能会在治疗晚期
PD-1抑制剂和酪氨酸激酶的安全性和功效...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最广泛,最致命的恶性肿瘤之一(1)。这是全球第五个最常见的癌症,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率的第三主要原因(2,3)。大多数患者由于诊断出晚期HCC而失去了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4),这也导致总生存率有限(OS)和未经改进的预后(5)。对于这些患者,多种治疗选择,包括手术切除,经皮消融和放射疗法,已显示出潜在的好处。然而,关于特定患者人群的效率和适用性存在重大局限性(6)。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例如编程死亡-1/编程死亡配体1(PD-1/PD-L1)抑制剂或细胞毒性T型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抑制剂,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相结合,已在HepATIN中与酪氨酸酶抑制剂(TKIS)相结合。表现出有希望的治疗潜力(7,8)。目前,阿托佐珠单抗与贝伐单抗的组合是晚期HCC的首选第一线治疗方案,将患者的中值总生存率(MOS)延长至19.2个月,伴随着目标响应(ORR)的增加,伴随着27.3%(7)。喜马拉雅阶段III期临床研究表明,与索拉非尼相比,用tremelimumab加杜瓦卢马布治疗的患者死亡的风险降低了22%(8)。但是,由于担心不良事件(AES)可能导致肝衰竭,因此PD-1抑制剂加TKIS组合疗法受肝功能受到限制(8)。根据PD-1抑制剂(9-11)和NCCN临床实践指南(12)的指示,不建议将中度至重度肝损伤或与高胆红素血症合并的患者与ICI与TKIS结合治疗。胆红素总升高(TBIL)的患者过去被认为不适合联合治疗。因此,以前的研究尚未招募这些患者。
全球激酶抑制剂:光控制释放与...
激酶抑制的外部控制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实现了激酶抑制作用的可逆和可抗光的光活化。4 - 12光定位一直是一种流行的方法,从而从战略上引入了一个光值保护部分,以防止与其靶酶相互作用。抑制活性仅在暴露于活性化合物的光和同时解放后才能恢复。迄今为止报告的大多数光刻片激酶抑制剂都依赖于紫外线来实现光激活,从而限制了它们在细胞环境中的使用。4 - 9虽然使用表现出的肾上腺笼中的使用 - 在破坏时进行了诊断变化,以监测细胞环境中笼子底物的光松益,13 - 17
针对酪蛋白激酶 1 进行癌症治疗
酪蛋白激酶 1 (CK1) 是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家族,在细胞增殖、存活和代谢等各种细胞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K1 表达失调与多种癌症的发展和进展有关,因此成为抗癌治疗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靶点。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概述了目前用于靶向 CK1 进行癌症治疗的策略,并讨论了该领域的未来前景。我们重点介绍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小分子抑制剂、RNA 干扰、基因组编辑和免疫疗法,这些方法在靶向调节癌细胞中的 CK1 活性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此外,我们讨论了与靶向 CK1 相关的挑战,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障碍的潜在策略。总体而言,靶向 CK1 作为癌症治疗的治疗策略具有巨大的前景,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一领域。
选择的选择:对非小细胞肺癌的变性淋巴瘤激酶抑制剂的不同免疫抑制潜力
简介:在克里唑替尼和alectinib中,已批准了几种肿瘤淋巴瘤激酶(ALK) - 抑制剂(ALKI)(ALKI)用于治疗ALK转移的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这迫使医生根据肿瘤的遗传学作用选择最合适的化合物,但也要在毒性和潜在的辅助处理方面选择。可能将靶向疗法与免疫疗法结合或之后,这强调了获得有关这些抑制剂潜在免疫调节作用的详细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1。)确定ALKI是否对人类树突细胞(DC)表现出免疫抑制作用,作为抗原特异性免疫的重要介体和2。)剖析这种免疫抑制在ALKI之间是否有所不同。
胃肠道癌中AXL受体酪氨酸激酶的表达改变:有希望的治疗靶
胃肠道(GI)癌症包括所有消化道器官的癌症,通常与肥胖,缺乏运动,吸烟,饮食不佳和大量酒精消耗有关。GI癌的治疗通常涉及手术,然后进行化学疗法和/或放射线。不幸的是,对这些疗法的内在或获得性抗性强调了对其他恶性肿瘤证明的更有效的靶向疗法的需求。GI癌的侵略性特征具有不同的信号通路,这些信号通路通过AXL受体酪氨酸激酶的过表达和激活相互连接。最近已经进行了一些涉及抗AXL抗体和小分子AXL激酶抑制剂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以测试其在包括GI癌症在内的实体瘤中的效率。因此,AXL可能是克服GI癌中标准疗法缺点的有前途的治疗靶标。
多激酶抑制剂在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治疗中:当前的临床应用和分子机械
高级肝细胞癌(HCC)是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具有有限的治疗方法。Axitinib是一种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性第二代抑制剂,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1、2和3的有效的第二代抑制剂。这种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包括晚期HCC在内的各种实体瘤中具有有希望的活性。目前,尚无相关评论文章总结了Axitinib在高级HCC中的确切作用。在这篇综述中,包括24项合格研究(临床研究中的7项研究,八项实验研究和9项临床试验)进行进一步评估。随机或单臂II期试验表明,与安慰剂治疗晚期HCC相比,Axitinib不能延长总体存活率,但是观察到了无进展生存期和肿瘤进展的时间的改善。实验研究表明,HCC中Axitinib的生化作用可能受其相关基因和影响的信号级联的调节(例如VEGFR2/PAK1,CYP1A2,CAMKII/ERK,AKT/MTOR和MIR-509-3P/PDGFRA)。FDA批准的索拉非尼与Nivolumab(PD-1/PD-L1的抑制剂)合并为治疗晚期HCC的第一线方案。由于Axitinib和Sorafenib都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以及VEGFR抑制剂,因此与抗PDL-1/PD-1抗体结合的Axitinib在抗肿瘤效应的高级HCC中也可能具有巨大的潜力。当前的评论突出了晚期HCC中轴替尼的当前临床应用和分子机制。通过结合Axitinib和先进的HCC中的其他治疗方法来朝着临床应用迈进,在不久的将来仍有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