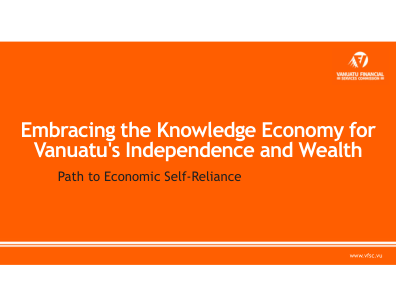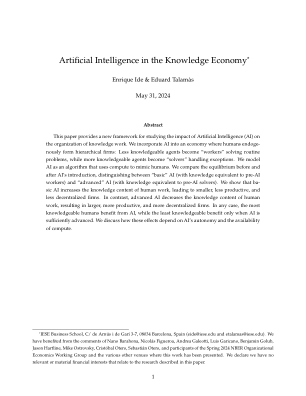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知识经济下的专业化
∗ 我非常感谢我的顾问 Jeremy Greenwood、Harold L. Cole、Hanming Fang 和 Emin Dinlersoz 的持续支持。我还要感谢 Salome Baslandze、Gorkem Bostanci、Murat Alp Celik、Simon Fuchs、Pengfei Han、Joachim Hubmer、Xian Jiang、Dirk Krueger、Veronika Penciakova、Jose- Victor Rios-Rull、Baxter Robinson、John L. Turner 以及芝加哥联储新秀会议、圣路易斯联储研讨会、亚特兰大联储研讨会、人口普查局研讨会、WEAI 年度会议、宾夕法尼亚大学宏观研讨会的与会者提出的有益建议。所表达的任何观点均为作者观点,而不代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观点。人口普查局的披露审查委员会和披露避免官员已审查了此信息产品是否存在未经授权披露机密信息的情况,并已批准对此新闻稿采用的披露避免做法。本研究由联邦统计研究数据中心根据 FSRDC 项目编号 2125 进行(CBDRB-FY21-P2125-R8940;CBDRB-FY21-P2125-R9239;CBDRB-FY22-P2125-R9822;CBDRB-FY23-P2125-R10582)。† 隶属关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电子邮件:yueyuanma@ucsb.edu。
瓦努阿图拥抱知识经济......
• 加强本地培训:投资升级本地教育和培训,以缩小技能差距。 • 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简化商务旅客的签证流程,将他们视为游客,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 • 简化工作许可:使高技能外国工人的工作许可流程快速、简单,最好是免费的。 引入数字游民签证:专门为希望在瓦努阿图为海外雇主远程工作的外国工人提供签证。
知识经济中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AI) 的兴起有可能通过自动化认知、不可编码的工作重塑知识经济。本文介绍了一个分析这种转变的框架,将人工智能纳入人类组成等级制公司以高效利用时间和知识的经济中:知识较少的人成为从事常规知识工作的“工人”,而知识较多的人成为协助工人解决特殊问题的“解决者”。我们将人工智能建模为一种将计算能力转化为“人工智能代理”的技术,这些代理可以自主运行(作为同事或解决者/副驾驶),也可以非自主运行(仅作为副驾驶)。我们表明,基本的自主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去解决复杂的问题,从而导致公司规模更小、生产力更低、分散性更低。相比之下,高级自主人工智能将人类重新分配到常规知识工作中,从而产生规模更大、生产力更高、分散性更强的公司。虽然自主人工智能主要使知识最丰富的人受益,但非自主人工智能却使知识最少的人受益。然而,自主人工智能实现了更高的总体产出。这些发现调和了看似矛盾的经验证据,并揭示了监管人工智能自主性所涉及的关键权衡。
韩国迈向知识经济
过去三十年来,韩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然而,自 1997 年以来,韩国一直经历着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破坏。为了克服这场危机并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韩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一直试图找出其弱点的根源。在众多因素中,缺乏核心知识资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1 世纪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发展依赖于知识及其应用。事实上,当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都是知识型国家。创造和商业化新知识创造了数百万个与知识相关的工作岗位,并从创新中创造了新的财富 [1]。韩国经济正试图从传统的资源型经济转向知识型经济。知识现在被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视为韩国加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韩国政府增加了对研究的支持,韩国企业已将知识管理引入其业务流程,包括对研发进行大量投资。重点在于创造新知识和技术,而不是获取或改造发达国家已有的知识。本文的目的是确定知识型经济的重要性和特点,并研究韩国经济在向知识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现状。第二部分概述了知识型经济的基本概念。第三部分描述了知识创造和转移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第四部分探讨了为什么从传统的资源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变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重要。第五部分通过提供衡量知识投入和产出的指标来分析韩国经济的现状。第六部分讨论了政府为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而制定的政策。
知识经济:印度的视角
摘要 印度形式的知识和智慧涉及生活的生理、心理和哲学方面。知识被视为指引成功和失败之路的光。它照亮和揭示了虚无的世界,是过上道德和伦理上美好生活的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知识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谈论知识的物质方面,同时,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已经开始,以从中创造价值,以便人类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以及质量和数量的增长。知识经济创造了一种团队合作的环境,以提高各个机构的能力。知识经济的共同和基本需要之一是拥有更好、更称职的学术研究和开发劳动力,这进一步为任何个人、团体、社区、机构、州和国家的发展创造价值。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解决问题、团队合作、监督和领导以及参与持续学习的能力只是称职劳动力必须具备的职场能力的几个例子。本文将从印度知识经济的角度探讨跨学科学术研究与开发的价值。此外,本文还将借助二手数据探讨新的“职场能力”成为规范的程度。
知识经济、KAM 方法论和……
摘要 本文强调了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它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即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本文还介绍了知识经济框架,该框架认为,对教育、创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持续投资以及有利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将导致经济生产中知识的使用和创造增加,从而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了帮助那些试图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国家,我们开发了知识评估方法 (KAM)。它旨在对各国对知识经济的准备情况进行基本评估,并确定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更多关注或未来投资的部门或特定领域。KAM 目前在世界银行内部和外部被广泛使用,并经常促进与客户国政府官员的接触和政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