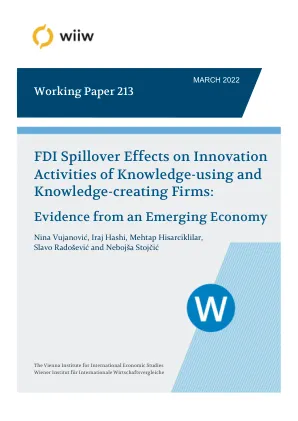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知识经济:新的研究议程
NGT 提出了一代具有一些基本相似性的模型,特别是对无形资产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关注。非物质资源最终与知识的生产和积累有关,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与某些关键活动(研发)和教育系统一起,是内生增长的关键。对“长期生产率增长的外生解释”的不满促使“构建了一类关键决定因素为模型内生因素的增长模型”。Barro 和 Sala-i-Martin 将 Romer、Lucas 和 Rebelo 的第一波贡献与 Romer 发起的第二阶段研究区分开来,前者侧重于投资的非递减收益,后者由 Grossman 和 Helpman 以及 Aghion 和 Howitt 进行,将研发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增长框架 [4-8]。
Tulchynska So,Solosich OS知识经济作为...
本文致力于分析在业务结构层面和相关国家政策方法中充分提供经济流程智力化的问题,以在确保经济安全的背景下发展智力经济。首先,分析了世界进步国家智力化过程的主要定量指标的动态。证实了经济发展智力发展过程与确保商业部门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证实,这涉及直接参与知识经济的工具支持,以消除现有的安全挑战和威胁。已经确定了在一般经济问题方面组织经济体系智力化有效过程的关键问题,以及在战时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后果。智力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组成部分,包括智力潜力,信息,知识,技术和创造性潜力,已被定义并进行了扩展描述。描述了有效产生,实际实施,扩散和进一步开发已确定的资源成分的特征。给出了企业家实体内部管理活动的关键领域的详细描述,以使主要经济过程进行智能化。最后,已经形成了加速经济体系智力化的国家监管政策的优先指导,涵盖了机构和法律规范,发展过程,信息政策,知识基础设施的形成,适当的组织和协调支持的最具影响力的方面。
韩国向知识经济转型期间的就业机会
本文分析了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韩国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期间的就业创造情况。在此期间,服务业与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比例增加,知识密集型产业增长,就业创造在地理上集中在首尔周围。2010 年代,这种变化放缓,整体就业增长减弱。为了分析这一时期以知识密集型可贸易服务业为主的就业创造驱动行业对当地服务业就业创造的影响,我使用了 Moretti (2010) 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修改版本。我分析了机构普查数据集中 237 个西郡区 1995-2005 年和 2006-2016 年的就业变化。我发现,一个制造业岗位创造了 0.5 个本地服务业岗位,一个可贸易服务业岗位在大都市的区内创造了 1.1 个岗位,在西郡地区创造了 2.3 个岗位。这一时期贸易类服务业与本地服务业的就业创造关系没有发生变化,随着向知识经济转型,贸易类服务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体而言就业创造仍然活跃,反之亦然。
FDI对知识经济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
创新活动对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贡献已在文献中得到充分证实(Polder 等,2009;Hashi 和 Stojčić,2013;Roud,2018)。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强调了发达经济体企业创新机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 (EME) 企业创新机制之间的差异,前者由研发投资或知识创造驱动,后者主要由机械设备投资(即非研发投资)或知识使用驱动(Cirera 和 Maloney,2017)。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Radošević,2016,第 130 页)证实了这一趋势,背景是发达的北欧欧盟国家和欧盟的中欧和东欧新兴经济体。报告显示,欧盟北部成员国发达地区近 72% 的创新支出用于研发支出,而欧盟中欧和东欧成员国这一比例为 39%。机械设备支出的情况则相反,这两组国家的创新支出分别占19%和54%。
人力资本和知识经济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挑战
摘要。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它不仅成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是智力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不仅是经济的条件,而且是整个文明进步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根本上不同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正在发展,与社会和劳动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就业形式中。现代世界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与以下事实有关:一方面,人类创建了最新的系统,包括技术,技术知识,高科技生产过程,市场机会,需要能够胜任和全面管理。另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胜任地管理这些过程,而且要不断改进这些过程,从而发展专业组成部分,以确保公司或州的竞争力和战略可持续性。
知识经济在群体内级别的聚类
3尽管危机和危机后的时期在经济,社会和领土影响方面取决于空间环境,从经济角度来看,西班牙的危机时期发生在2008年至2012年2013年10月2014年。在这三年中,该国见证了经济复苏的缓慢(如宏观经济数据所示,例如GDP,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然而,重要的挑战仍有待解决,例如降低风险保费,公共债务和社会空间不平等(由临时工作的数量,高失业水平和相当大的驱逐率证明)。4,10,000名居民的门槛用于区分农村和城市城市。
将墨西哥移民的贡献与美国知识经济联系起来
如今,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它创造了无限创意的良性循环(Cortright 2001)。人员流动促进了科学创新的循环,因为它允许高技能人才通过在能够找到合适的经济、社会和政策资源的国家工作,将自己的知识与他人的知识相结合(van der Wende 2015)。因此,知识和创新与人员流动和移民之间似乎存在着内在关系。Aboites 和 Díaz 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是由知识流动支持的”(2018,1443)。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十年中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发达经济体经历了人才短缺,而人力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变得与金融资本一样重要(Ryan and Silvanto 2021)。这一假设得到了实地事实的支持。在过去二十年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比例每年以一般移民比例的 1.5 倍增长(Delgado Wise、Chávez Elorza 和 Gaspar Olvera 2021)。在发达经济体中,高技能移民的到来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专利潜力(Dennis 2020;Gaspar Olvera 2021)。正如 Peri (2016) 所说,高技能工人向创新极点的流动促进了全球科学,从而促进了长期的全球增长。同样,Bernstein 等人 (2019) 发现,移民发明家促进了思想和技术的引进,并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在这方面,Gaspar Olvera (2021) 研究了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集中了 70% 的所有高技能移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其中美国拥有 50% 的所有高技能移民。那么,什么是高技能移民?这一群体包括学生、大学教授、研究人员、专业人士、首席执行官和技术人员等(Tuirán 和 Ávila 2013),他们寻找的环境支持创新发展、知识和生产力溢出效应的国家(Ryan 和 Silvanto 2021),有利于创建技术集群、创新中心、研究型大学和需要他们技能的知识型产业(Clarke、Li 和 Xu 2013;Dickmann 和 Cerdin 2014)。与知识经济相关的一些常见领域包括健康、数学、计算机、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工程。此外,移民通过创业或发明活动或与本国本土工人的合作推动输出国和接收国的创新(Harnoss 等人 2021)。因此,Duleep、Jaeger 和 Reget (2012) 认为,移民是灵活的经济行为者,他们可能更愿意参与颠覆性的商业模式。Kautto (2019) 补充道,在发达国家,移民企业家创立了 40% 以上的财富 500 强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促进知识经济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在
弥合知识经济需求与教育系统成果之间的差距:评估模型
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基于智力能力和无形资产的经济可以使国家的经济多样化(Schwalje,2013年),并增加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Lange等,2018)。该报告是由区域教育计划中心(RCEP)委托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地区的需求,以跟踪和支持持续过渡到知识经济体的努力。与全球趋势一致,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州增加了专门针对知识经济增长的教育领域的倡议,以作为中长期政策作为发展议程。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许多组织和政府使用区域和国际指数和模型来跟踪国家的知识绩效。这些经常采用跨部门“支柱”或组成部分来评估能够形成和扩展知识经济体的领域。
知识经济在管理基于需求的环境Kuznets曲线中的作用
平衡时的总需求或供应通常用作经济宏观经济活动的代表,从而汇总需求表示个人和家庭的行为。但是,总需求也会通过总生产的变化直接影响环境恶化。这项研究试图探索这种关系,称为基于需求的环境Kuznets曲线(需求EKC)和不同知识经济指标的作用。知识经济指标提议影响消耗模式,改变了经验研究所研究的需求EKC。为此,从2008年到2018年收集了147个国家的二级数据,也将其分类为开发。这项研究发现,总需求显着影响碳排放。使用完全修改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长期结果。控制因素,例如可再生能源消耗,人口密度和财务发展显着影响样本国家的碳排放。本研究纳入了基于知识的经济的四个支柱,结果表明,这些指标有助于减少与消费相关的CO 2排放。2023中国地球科学大学(北京)和北京大学。由Elsevier B.V.代表中国地球科学大学(北京)出版。这是CC BY-NC-ND许可证(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下的开放访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