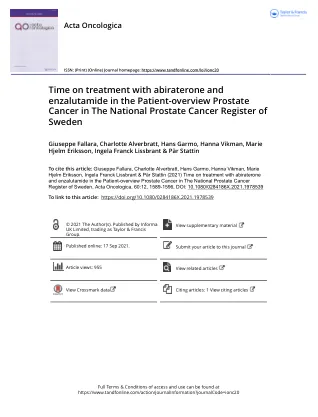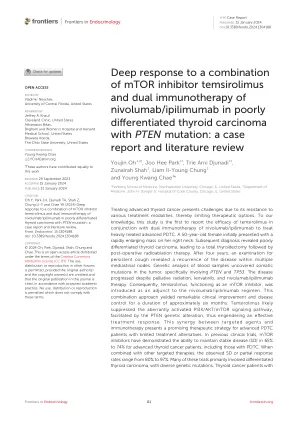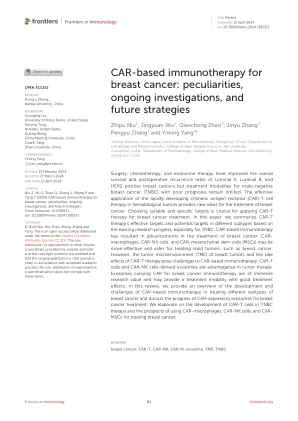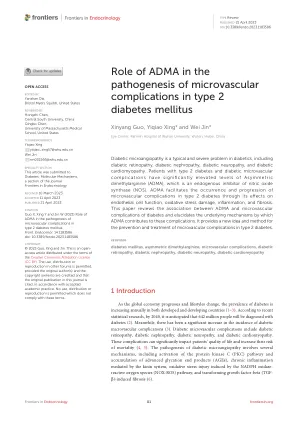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神经内分泌前列腺癌的免疫基因组景观
利益冲突H.B.曾担任Janssen,Astellas,Merck,Pfizer,Foundation Medicine,Blue Earth Diagnostics,Amgen,Amger,Bayer,Oncorus,Loxo,Daicchi Sankyo,Daicchi Sankyo,Sanofi,Sanofi,Curie Therapeutics,Novartis,Novartis,Astra Zeneca; H.B.已获得Janssen,Abbvie/Stemcentrx,Eli Lilly,Astellas,Millennium,Bristol Myers Squibb,Circle Pharma,Daicchi Sankyo,Novartis的研究资金。O.E. 得到Janssen,J&J,Astra-Zeneca,Volastra和Eli Lilly Research Grants的支持; O.E. 是Freenome,Owkin,Pionyr Immunothapeics,Volastra Therapeutics和一名三个生物技术的科学顾问和股权持有人,也是Champions肿瘤学的付费科学顾问; V.C. 曾担任Janssen,Astellas,Merck,Astrazeneca,Amgen和Bayer的顾问/顾问委员会成员; V.C. 已获得Astellas,Janssen,Ipsen,Bayer和Bristol的演讲者Honoraria或旅行支持。O.E.得到Janssen,J&J,Astra-Zeneca,Volastra和Eli Lilly Research Grants的支持; O.E.是Freenome,Owkin,Pionyr Immunothapeics,Volastra Therapeutics和一名三个生物技术的科学顾问和股权持有人,也是Champions肿瘤学的付费科学顾问; V.C.曾担任Janssen,Astellas,Merck,Astrazeneca,Amgen和Bayer的顾问/顾问委员会成员; V.C.已获得Astellas,Janssen,Ipsen,Bayer和Bristol的演讲者Honoraria或旅行支持。
JAK2/STAT3信号通路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潜在治疗靶点
三阴性乳腺癌 (TNBC) 因其易转移和预后不良而带来了巨大的临床挑战。TNBC 通过各种机制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攻击,包括 Janus 激酶 2 (JAK2)/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 3 (STAT3) 信号通路。该通路的特点是在许多实体瘤中活性增强,在特定的 TNBC 亚型中表现出明显的激活。因此,针对 JAK2/STAT3 信号通路成为一种有前途的精准 TNBC 治疗策略。JAK2/STAT3 通路的信号转导级联主要涉及受体酪氨酸激酶、酪氨酸激酶 JAK2 和转录因子 STAT3。正在进行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正在积极研究该通路作为 TNBC 治疗的潜在治疗靶点。本文全面回顾了使用小分子化合物靶向 JAK2/STAT3 信号通路治疗 TNBC 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本综述探讨了 JAK2/STAT3 通路在 TNBC 治疗中的作用,评估了活性抑制剂和靶向蛋白水解的嵌合体在 TNBC 治疗中的益处和局限性。目的是促进有效靶向 TNBC 的新型小分子化合物的开发。最终,这项工作旨在为提高 TNBC 患者的治疗效果做出贡献。
研究乳腺癌的肿瘤免疫原性
免疫细胞与恶性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根除乳腺癌的重要篇章。这种广泛分布且种类繁多的癌症对全世界的女性构成了重大威胁。乳腺癌的发病率与多种风险因素有关,特别是遗传易感性和家族史。尽管从手术和化疗到放疗和靶向治疗,治疗方式取得了进展,但持续的高复发率、转移率和治疗耐药性凸显了对新治疗方法的迫切需求。免疫疗法在乳腺癌治疗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它利用了肿瘤微环境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之间的这种动态相互作用已成为免疫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探讨了各种癌症标志物(如新抗原和免疫调节基因)在乳腺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作用。此外,它还探索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治疗有效药物的未来潜力,以及阻碍其疗效的挑战,特别是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和实现肿瘤特异性的困难。
在乳腺癌免疫疗法中研究三级淋巴结构的进展
作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乳腺癌表现出不同亚型的复杂和异质性病理特征。三阴性乳腺癌(TNBC)和HER2阳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的两个常见和高度侵入性的亚型。乳房菌群的稳定性与免疫环境紧密相互交织,免疫疗法是治疗乳腺癌的常见方法。前淋巴结结构(TLSS)最近发现,最近发现的围绕乳腺癌的免疫细胞聚集物,与次生淋巴机构(SLOS)相似,与免疫疗法有关,与一些乳腺癌相关。机器学习是一种人工智能的一种形式,越来越多地用于检测生物标志物和构建肿瘤预后模型。本文系统地回顾了乳腺癌中TLSS的最新研究进度以及机器学习在检测TLSS中的应用以及乳腺癌预后的研究。提供的见解为进一步探索乳腺癌不同亚型的生物学差异并制定个性化治疗策略的生物学差异有助于有价值的观点。
美国前列腺癌患者接受阿比特龙和恩杂鲁胺治疗的时间
摘要背景:关于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mCRPC) 男性使用雄激素受体靶向药物 (ART) 阿比特龙和恩杂鲁胺治疗时间的临床实践数据很少且不一致。我们评估了 ART 治疗时间并研究了治疗时间的预测因素。材料和方法:使用 Kaplan - Meier 图和 Cox 回归评估了瑞典国家前列腺癌登记处 (NPCR) 子登记处患者概览前列腺癌 (PPC) 中 mCRPC 男性的 ART 治疗时间。为了评估 PPC 对治疗时间的代表性,与 NPCR 中在处方药登记处填写 ART 的所有男性进行了比较。结果: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PPC 中的 2038 名男性接受了 ART 治疗。未接受过化疗的男性中位治疗时间为阿比特龙 10.8 个月(95% 置信区间 9.1 – 13.1),恩杂鲁胺 14.1 个月(13.5 – 15.5)。使用多西他赛后,阿比特龙的治疗时间为 8.2 个月(6.5 – 12.4),恩杂鲁胺的治疗时间为 11.1 个月(9.8 – 12.6)。ART 治疗时间长的预测因素包括 ART 前 ADT 持续时间长、ART 开始时血清 PSA 水平低、无内脏转移、体能状态良好以及未曾使用过多西他赛。PPC 捕获了所有已开具 ART 处方的 NPCR 男性中的 2522/6337(40%)。根据处方药登记处填写的信息,PPC 男性接受 ART 治疗的时间中位数与 NPCR 所有男性相比略长,分别为 9.6 (9.1 – 10.3) 个月和 8.6 (6.3 – 9.1) 个月。结论:由于年龄较大、体能状态较差和合并症较多,临床实践中的治疗时间与已发表的 RCT 中的时间相似或更短。
对MTOR抑制剂Temsirolimus和Nivolumab/ipilimumab的双重免疫疗法的深刻反应,甲状腺癌
治疗晚期甲状腺癌由于对各种治疗方式的抵抗而提出了挑战,从而限制了治疗选择。据我们所知,这项研究是第一个报告Temsirolimus与Nivolumab/ipilimumab的双重免疫疗法结合使用以治疗经过严重处理的晚期PDTC的效率。一名50岁的女性最初在她的右脖子上出现了快速扩大的肿块。随后的诊断表明甲状腺癌分化差,导致甲状腺切除术,然后进行术后放射治疗。四年后,对持续性咳嗽的检查显示,多个纵隔节点内这种疾病复发。对血液样本的遗传分析发现了肿瘤中的体细胞突变,涉及PTEN和TP53。尽管姑息放射线,lenvatinib和Nivolumab/ipilimumab治疗,该疾病仍在进行。因此,作为Nivolumab/ipilimumab方案的辅助作用,将Temsirolimus作为MTOR抑制剂发挥作用。这种组合方法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内产生了显着的临床改善和疾病控制。Temsirolimus可能抑制了异常激活的PI3K/AKT/MTOR信号传导途径,这是由PTEN遗传改变促进的,因此产生了有效的治疗反应。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之间的这种协同作用为有限的治疗替代品的晚期PDTC患者提供了有希望的治疗策略。与其他靶向疗法结合使用时,观察到的SD或部分反应率范围为80%至97%。在先前的临床试验中,MTOR抑制剂已经证明了晚期甲状腺癌患者(包括患有PDTC患者)保持稳定疾病(SD)的能力。这些试验中的许多主要涉及分化的甲状腺癌,具有不同的遗传突变。甲状腺癌患者
甲状腺癌靶向治疗及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和个性化治疗的需求,甲状腺癌的靶向治疗和生物标志物研究代表了肿瘤学的一个重要前沿。与甲状腺癌相关的基因变化种类繁多,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阐明分子细节。这项研究具有临床意义,因为它可用于制定个性化治疗计划。靶向治疗提供了一种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它针对某些分子靶点,例如突变的 BRAF 或 RET 蛋白。这种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健康组织的附带伤害,也可能减少不良影响。同时,通过生物标志物探索,可以根据分子特征对患者进行分类,从而可以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效果。靶向治疗和生物标志物研究的好处不仅限于其直接的临床影响,还涵盖了整个癌症领域。了解甲状腺癌的遗传基础有助于创造专门针对异常分子的新疗法。这促进了甲状腺癌的治疗,推动了精准医疗的发展,为治疗其他癌症铺平了道路。简而言之,对甲状腺癌的更多研究有望改善患者护理。本次调查中发现的概念有可能彻底改变护理方式,开启个性化精准医疗的新时代。这种模式转变可以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并为其他癌症类型的进展提供灵感。
ESMO网络研讨会:ESMO指南:现实世界案例 - 转移性乳腺癌2024
RodrigoSánchez-Bayona,医学博士博士医学肿瘤学,Octubre(西班牙马德里)ENSO年轻肿瘤学家委员会成员
基于CAR的乳腺癌免疫疗法
手术、化疗及内分泌治疗提高了Luminal A、Luminal B及HER-2阳性乳腺癌的总生存率和术后复发率,但对于预后不良的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治疗方式仍然有限。迅速发展的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在血液系统肿瘤中的有效应用为乳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选择合适、针对性的靶点是CAR-T疗法应用于乳腺癌治疗的关键。本文在现有的研究进展基础上,总结了CAR-T疗法在不同亚型中的有效靶点和潜在靶点,尤其是针对TNBC。以CAR为基础的免疫疗法使得乳腺癌的治疗取得了进展,CAR-巨噬细胞、CAR-NK细胞和CAR-间充质干细胞(MSCs)可能对治疗乳腺癌等实体肿瘤更有效、更安全。然而乳腺肿瘤的肿瘤微环境(TME)和CAR-T疗法的副作用对CAR免疫治疗提出了挑战。CAR-T细胞和CAR-NK细胞衍生的外泌体在肿瘤治疗中具有优势。携带CAR的外泌体用于乳腺癌免疫治疗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可能提供一种治疗效果良好的治疗方式。在本综述中,我们概述了CAR免疫治疗在治疗不同亚型乳腺癌中的发展和挑战,并讨论了表达CAR的外泌体用于乳腺癌治疗的进展。我们详细阐述了CAR-T细胞在TNBC治疗中的发展以及使用CAR-巨噬细胞,CAR-NK细胞和CAR-MSCs治疗乳腺癌的前景。
ADMA在2型糖尿病中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理中的作用 在前列腺癌中使用PARP抑制剂 在中国卵泡淋巴瘤患者中使用循环肿瘤DNA的预测预测 社论:地下氢存储的微生物学 功能失调的连通性作为意识障碍的神经生理机理:系统评价 三重再摄取抑制剂的影响对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的影响
糖尿病微血管病是糖尿病患者的典型且严重的问题,包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糖尿病性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和糖尿病性心肌病。2型糖尿病和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患者的不对称二甲基精氨酸(ADMA)的水平显着升高,这是一种一氧化氮合酶(NOS)的内源性抑制剂。ADMA通过其对内皮细胞功能,氧化应激损伤,炎症和纤维化的影响,促进了2型糖尿病中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和进展。本文回顾了糖尿病的ADMA和微血管并发症之间的关联,并阐明了ADMA导致这些并发症的潜在机制。它为预防和治疗2型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提供了一种新的想法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