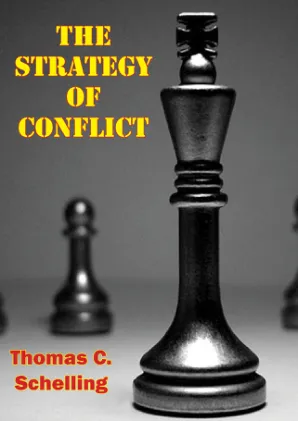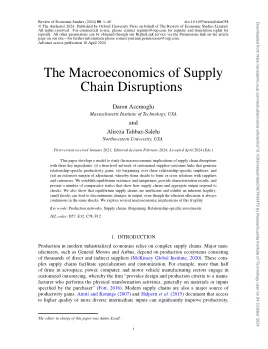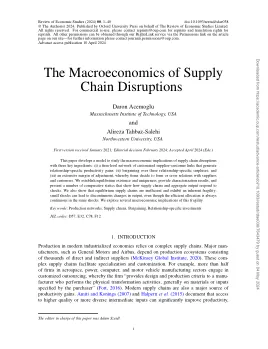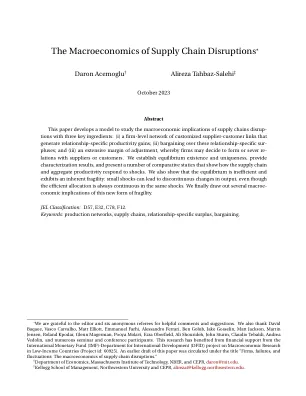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讨价还价技术 - pdf-未来工作中心
但是,如果“技术”并不负责怎么办?毕竟,我们所说的“技术”不是某些外在或外源力所施加的。相反,技术构成了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的综合,使我们能够生产新的商品和服务,并以新的(大概更有效)的方式生产它们。持续不断的知识累积反映了关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实施我们发明的解决方案的故意人类选择。解放人类的选择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以及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使用。我们不生活在终结者电影的世界中,那里的机器正在负责。人类控制技术:但并非所有人类在这些决定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在这种理解中,技术既不是反派,也不是救主。技术如何影响我们,取决于(以及由谁)如何管理和控制谁。
未观察到的报价讨价还价∗ -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
1 关于这些情况的讨价还价和威慑的讨论比比皆是。例如,关于南海,请参阅 Kaplan (2014) 或 Coy (2021);关于俄罗斯,请参阅 Allison (2013) 或 Freedman (2019);关于网络威慑,请参阅 Baliga、Bueno de Mesquita 和 Wolitzky (2020) 及其参考文献。对这些冲突不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观点会认识到双方都有机会宣称领土并发起冲突。在本文中,我考虑了非对称情况(一方是“索赔方”,另一方是“响应方”)和对称情况(双方都扮演两个角色)。2 大量环境经济学文献研究了不完善监控下的激励计划(Shortle 和 Horan,2001)。迄今为止,有关媒体审查的经济学文献强调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Prat 和 Strömberg,2013 年)。3 与我的模型不同,在标准效率工资和政治代理模型(例如 Shapiro 和 Stiglitz,1984 年;Ferejohn,1986 年)中,工人/政客过去行为的收益影响在解雇决定/选举时就已消失,因此,对于雇主/公民来说,各种隐性合同都是可信的。
未观察到的报价讨价还价∗ -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
1 关于这些情况的讨价还价和威慑的讨论比比皆是。例如,关于南海,请参阅 Kaplan (2014) 或 Coy (2021);关于俄罗斯,请参阅 Allison (2013) 或 Freedman (2019);关于网络威慑,请参阅 Baliga、Bueno de Mesquita 和 Wolitzky (2020) 及其参考文献。对这些冲突不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观点会认识到双方都有机会宣称领土并发起冲突。在本文中,我考虑了非对称情况(一方是“索赔方”,另一方是“响应方”)和对称情况(双方都扮演两个角色)。2 大量环境经济学文献研究了不完善监控下的激励计划(Shortle 和 Horan,2001)。迄今为止,有关媒体审查的经济学文献强调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Prat 和 Strömberg,2013 年)。3 与我的模型不同,在标准效率工资和政治代理模型(例如 Shapiro 和 Stiglitz,1984 年;Ferejohn,1986 年)中,工人/政客过去行为的收益影响在解雇决定/选举时就已消失,因此,对于雇主/公民来说,各种隐性合同都是可信的。
vitae dr duncan McHale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全球投资者关系和ESG的高级副总裁沃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
有一致的考虑变化,从讨价还价的收入和商誉损害,其他无形和有形资产以及总非运营结果
推荐引用 推荐引用 C. Anthony Pfaff,《流畅胁迫:21 世纪胁迫语法》(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社,2022 年),https://press.armywarcollege.edu/monographs/952
本专著源于与美国陆军和作战司令部参谋人员的军事规划人员的对话,讨论希望更好地了解战争门槛以下的竞争如何进行以及军队如何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问题的一部分似乎是军事从业者往往没有充分区分击败敌人和胁迫敌人。前者涉及消除敌人的选择,而后者涉及旨在说服敌人选择合作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意味着一方必须将主导地位和主动权让给对方,并进行不体面的操纵以重新获得主导地位和主动权。也许更重要的是,讨价还价违背了军事行动的逻辑和语法。当军队摧毁(或至少中和)敌军的速度比后者摧毁或中和前者的速度更快时,军队就获胜了。当目标不是摧毁敌方军事力量时,军事力量可能仍然有用,但使用它们的逻辑和语法就不那么明确了。本专著旨在阐明胁迫如何发挥作用,以便军事从业者能够更好地调整要求、威慑措施和对合作伙伴的支持,以确保美国的重大利益。
供应链中断的宏观经济学
本文开发了一个模型,以研究供应链破坏的宏观经济含义,并使用三种关键成分:(i)定制供应商 - 客户链接的公司级网络,从而产生关系特异性生产率的增长; (ii)讨价还价,讨价还价; (iii)广泛的调整范围,从而决定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或切断关系。我们建立了平衡的存在和独特性,提供了表征结果,并提供了许多比较静态,这些静态表明供应链和骨料产出如何响应冲击。我们还表明,平衡供应链不具备,并且表现出固有的脆弱性:即使有效的分配始终在相同的冲击中连续,小冲击可能导致输出不连续的变化。我们探索了这种脆弱性的几种宏观经济含义。
Robert L. Bray-凯洛格管理学院
本文开发了一个模型,以研究供应链破坏的宏观经济含义,并使用三种关键成分:(i)定制供应商 - 客户链接的公司级网络,从而产生关系特异性生产率的增长; (ii)讨价还价,讨价还价; (iii)广泛的调整范围,从而决定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或切断关系。我们建立了平衡的存在和独特性,提供了表征结果,并提供了许多比较静态,这些静态表明供应链和骨料产出如何响应冲击。我们还表明,平衡供应链不具备,并且表现出固有的脆弱性:即使有效的分配始终在相同的冲击中连续,小冲击可能导致输出不连续的变化。我们探索了这种脆弱性的几种宏观经济含义。
供应链中断的宏观经济学*
本文开发了一个模型,以研究供应链的宏观经济含义,并使用三种关键要素:(i)定制的供应商客户链路的确定级别网络,从而产生关系特定于关系的生产率提高; (ii)讨价还价,讨价还价; (iii)广泛的调整范围,因此,企业可以决定与供应商或客户结为或切断。我们建立了平衡的存在和独特性,提供了表征结果,并提供了许多比较静态,这些静态表明供应链和汇总生产率如何响应冲击。我们还表明,平衡是不具体的,并且表现出固有的脆弱性:即使有效的分配始终在相同的冲击中连续连续,小冲击可能导致输出不连续的变化。我们最终绘制了这种新形式的脆弱性的几种宏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