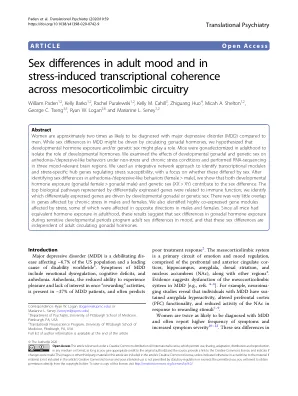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靶向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增强Erastin诱导的铁死亡对EGFR激活突变肺腺癌的治疗效果
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而肺腺癌(LUAD)占所有肺癌的40%(1)。在亚洲,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LUAD最常见的驱动突变,发生率为55%(2-4),其中EGFR激活突变在全球占17.4%,在中国占37.3%(5)。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目前是EGFR突变LUAD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6)。尽管使用EGFR-TKI已为晚期EGFR突变型NSCLC患者带来显著的临床获益和前所未有的生存率提高(7-10),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获得性耐药。继发性EGFR突变,包括EGFR-T790M突变和EGFR结构域内的其他突变、MAPK、PI3K和细胞周期基因的突变以及EGFR或其他致癌基因如MET的扩增,导致LUAD细胞获得性EGFR-TKI耐药(11-13)。但有些患者在缺乏已知耐药机制的情况下获得了EGFR-TKI耐药。因此,内在性EGFR-TKI耐药是临床上的一个挑战。据报道,大约20%-30%的EGFR突变型LUAD对EGFR-TKI具有内在性耐药(14)。因此,如何克服这些获得性和内在性的EGFR-TKI耐药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焦点。
使用诱导的plupotent-stem-cells-in-prug- ...
©2012美国临床药理学和治疗学会;本文未发表在出版商中。引用时,请检查出版商的版本。 ;这不是已发布的版本。请仅引用已发布的版本。
NVX-COV2373诱导的具有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T和B细胞免疫力未能对mRNA和病毒载体SARS做出反应
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大流行已经大大加快了病毒感染和疫苗接种研究的进展。直到2021年11月,有四种SARS-COV-2疫苗已在欧盟获得营销授权,其中两种是基于mRNA的,两个基于病毒矢量技术。多项研究表明,关于预防SARS-COV-2有症状感染和严重的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疾病疗法的mRNA和病毒载体疫苗的良好效率(1-7)。免疫分析提供了针对SARS-COV-2的体液和T细胞反应的证据(8-18)。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某些亚群中,尤其是在因自身免疫性疾病或癌症引起的免疫抑制疗法的患者中,对SARS-COV-2疫苗接种的免疫反应减少甚至缺乏免疫学反应。不幸的是,由于免疫疗法,同一患者有严重的Covid-19疾病病程的风险。免疫抑制治疗用于多发性硬化症(PWMS)的人进行疾病改良。已显示两类MS药物会损害对mRNA和病毒载体疫苗接种的免疫反应。首先,已显示出可预防淋巴结淋巴结淋巴细胞的链球菌1-磷酸受体(S1PR)调节剂,已被证明会损害对SARS-COV-2疫苗接种的体液和T细胞反应(19-21)。第二,单克隆抗CD20抗体的治疗有限的患者能够对SARS-COV-2疫苗进行足够的体液反应能力(22-27)。2021年12月,基于蛋白质的SARS-COV-2疫苗NVX-COV2373在欧盟获得了有条件的营销授权。我们旨在澄清NVX-COV2373是否可以诱导SARS-COV-2特定t-和
tislelizumab诱导的1型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患者患有小细胞肺癌的患者:病例报告
本报告提出了一例71岁的男子,被诊断出患有广泛的小细胞肺癌(ES-SCLC),后者第一次发生了3次tislelizumab加化学疗法后,他开发了1型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DKA)。患者没有糖尿病病史(DM)。根据病史和实验室检查,该病例被明确诊断为Tislelizumab诱导的一种新的1型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这是一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诱导的1型糖尿病(ICI-T1DM)的发生率很少,但ICI-T1DM的发展,尤其是1型糖尿病性酮症酸酸中毒的发展是威胁生命的,没有血糖监测和胰岛素治疗。早期鉴定高血糖和C肽消耗以及ICI治疗期间常规的血糖监测对于避免致命性内分泌免疫相关性不良事件(IRAE)至关重要。
利用辅助诱导的表观遗传调节,以增强疫苗和癌症治疗的免疫力
佐剂在疫苗和癌症疗法中至关重要,通过各种机制增强了治疗效率。在疫苗中,佐剂传统上是值得放大免疫反应的价值,从而确保了对病原体的强大和持久的保护。在癌症治疗中,佐剂可以通过靶向肿瘤抗原来提高化学疗法或免疫疗法的有效性,从而使癌细胞更容易受到治疗。最近的研究发现了佐剂的新分子水平效应,主要是通过表观遗传机制。表观遗传学包括基因表达中的可遗传修饰,这些修饰不会改变DNA序列,影响诸如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表达等过程。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在调节基因活性,影响免疫途径以及调节免疫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疫苗或癌症治疗中,了解佐剂与表观遗传调节剂的相互作用如何为在各种医疗领域开发更精确的细胞靶向疗法提供显着潜力。本综述深入研究了佐剂的不断发展的作用及其与表观遗传机制的相互作用。还研究了利用表观遗传变化以增强辅助效率的潜力,并探讨了在治疗环境中表观遗传抑制剂作为辅助剂的新颖使用。
在2D材料中查看光诱导的量子现象
过去二十年来目睹了对Van-der-Waals(VDW)材料的研究爆炸,这是一类广泛的固体,在该固体中,平面晶体板由VDW部队粘合在一起。通常,这些材料只能将其稀释为几个原子层,甚至可以将其变成单个原子纸,从而意识到其传统散装形式的二维(2D)变体。由于在2000年代初期的单层(1L)的第一次驱动器以来,已经将各种VDW材料隔离并以2D极限进行了隔离和研究,包括金属,宽间隙绝缘子,半导体,半导体,半金属,超级导管,磁性材料,磁性材料,以及更多。[1]中,在这些半金属中,例如石墨烯和2D半导管,通常由VI组VI过渡金属二甲硅烷基(TMDC)代表,在基本凝聚的物理学以及在电子,电子,光电电子技术中以及在基本凝聚的物理学方面创造了令人兴奋的新机会。[2-4]由于光学相互作用和频段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从几层到1L极限的过渡中可能发生,因此在2D Light-Matter相互作用和超级超平均光电设备中证明了2D半导体和半米的独特机会。这值得探索其光诱导的物理学,从而导致新型量子现象。2D材料的关键特性之一是增强的电子 - 电子库仑相互作用,其介电筛选和低维度引起。这些相互作用不仅强烈修改平衡频带结构,而且更改了(照片)激发的带构结构。[5],例如,强烈结合的激子[6](由绑定的电子和孔组成),即使在室温下,也要赋予2D半导体的光学响应。这些摘录显示出各种各样的物种,具有不同的自旋,[7] Monma,[8]和电荷[9]影响其光 - 肌电相互作用的频谱,动力学和应用。2D材料的另一个属性是它们能够将其堆放到其他2D材料和基板上,几乎没有约束。[10]这些结构中的层间相互作用促进了一种独特的手段,用于设计异质结构属性和功能,而不是组成材料的材料。[11,12]这些属性包括动量依赖性层
药物诱导的抗性进化需要较少的侵略性治疗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表明,抗癌和抗菌药物本身可能通过提高可突变性来促进耐药性的获取。成功控制不断发展的人群要求将这种控制的生物学成本识别,量化并包括在进化知情的治疗方案中。在这里,我们确定,表征和利用降低目标人口大小和产生治疗引起的救援突变的盈余之间的权衡。我们表明,在中间剂量下,治愈的可能性最大,低于药物浓度产生最大种群衰减,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较少积极的治疗策略可以大大改善治疗结果。我们还提供了一般性的分析关系,该关系将生长速率,药效学和依赖性突变率与最佳控制定律联系起来。我们的结果强调了基本生态进化成本的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作用。这些成本通常会导致情况,即使治疗的目的是消除而不是遏制,累积药物剂量也可能是可取的。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加剧了对管理侵略性,高剂量疗法的标准做法的持续批评,并激发了对诱变性和其他隐性疗法的其他隐性抵押成本的进一步实验和临床投资。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诱导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预测日本受试者的治疗反应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会导致各种与免疫相关的不良事件(IRAE)。中,甲状腺功能障碍最常在内分泌环境(1)中观察到。在一项队列研究中,有44%的ICI治疗患者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大多数ICI诱导的甲状腺功能障碍是破坏性的甲状腺炎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症(2)。ICI引起的坟墓疾病的频率很低; ICI给药后,约有2%的患者表现出甲状腺毒性(3)。在一项针对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中,接受ICI后出现甲状腺毒性病的患者表现出无效的生存率,但癌症结局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之间没有相关性(4)。我们对川崎医学院医院接受ICI治疗的466例患者进行了一次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并报告了被诊断为内分泌相关IRAE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更高(5)。我们机构中与内分泌相关的IRAE的发生率为25.5%,其中大多数是主要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在日本患者中,在伴有内分泌相关的IRAE的情况下,平均观察期可能更长,但先前的研究不足以评估IRAE患病率与ICI治疗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甲状腺功能障碍程度与ICI治疗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在评估甲状腺功能的ICI治疗患者中。
成人情绪的性别差异以及跨中皮质胶质电路的压力诱导的转录连贯性
与男性相比,抽象女性大约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MDD)的可能性大约是男性的两倍。虽然MDD的性别差异可能是通过循环的性腺激素驱动的,但我们假设发育激素暴露和/或遗传性别可能起作用。小鼠在成年中被赋形切除术,以隔离发育激素的作用。我们研究了发育性性腺和遗传性别对在非压力和慢性应激条件下甲壳虫/抑郁样行为的影响,并在三个与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进行了RNA序列。我们使用了一种集成网络方法来识别调节应力敏感性的转录模块和特定于应力的集线器基因,重点是这些模块是否与性别有所不同。在识别出Anhedonia/抑郁样行为(女性>男性)的性别差异后,我们表明发育激素暴露(性腺女性> Gonadal雄性)和遗传性别(XX> XY)都会导致性别差异。由差异表达基因表示的顶部生物学途径与免疫功能有关。我们确定哪些差异表达的基因是由发育性性腺或遗传性别驱动的。受男性和女性慢性应激影响的基因几乎没有重叠。我们还鉴定了受压力影响的高度共表达的基因模块,其中一些模块在男性和女性的相反方向上受到影响。由于所有小鼠在成年后都有同等的激素暴露,因此这些结果表明,敏感发育期间性腺激素暴露的性别差异计划成人情绪上的性别差异,并且这些性别差异与成人循环的性腺激素无关。
化学治疗药物诱导的指甲变化
ntroduction癌症化学治疗药物与不同的指甲变化有关,这可能是由于以下提出的一种或多种机制所致:(i)对指甲矩阵的损害,导致异常指甲板的生长; (ii)指甲床伤害; (iii)损坏近端指甲折叠; (iv)异常的血液流到指甲床。[1,2] The chemotherapy‑induced nail changes frequently mimic nai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many systemic diseases such as rheumatoid arthritis,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y syndrome, psoriasis, pulmonary embolism, coronary thrombosis, cirrhosis, congestive cardiac failure, renal failure, nephrotic or nephritic综合征,贫血,糖尿病,卟啉症,周围血管疾病,肝病,营养不良,艾迪生氏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获得的免疫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