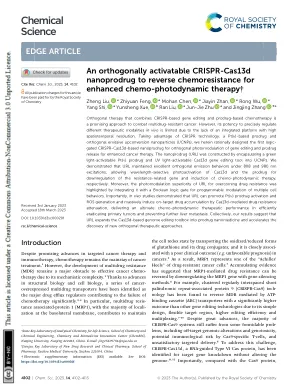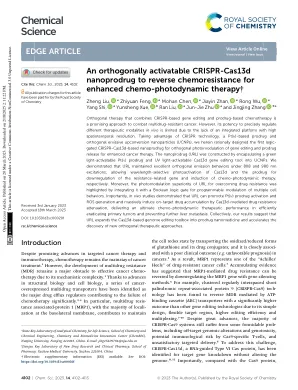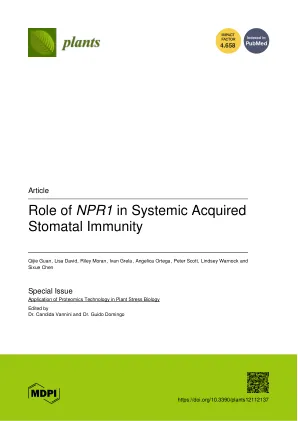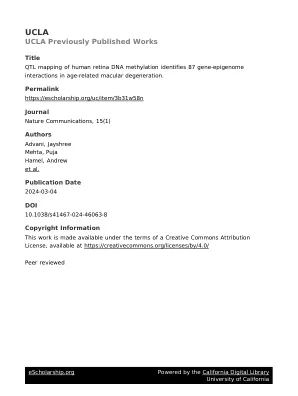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神经病学中新兴治疗的术语
神经病学新疗法的研究和开发正在以非先验的方式扩展。对于临床医生和患者来说,这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医学生物必须根据其作用机制不断更新他们对这些新药的知识。命名法是指导这种探索的路标。国际非专有名称(INN),通常称为通用名称,是药物的唯一标识符。1世界卫生组织(WHO)分配了这些名称,以便清楚地识别药物并促进全球卫生专业人员和科学家之间信息的通信。许多国家都有协调其命名制度的理事会,例如英国批准的姓名,dénoriationsfrançaises,日本接受的姓名和美国采用的姓名(USAN)。2然而,除了极少数例外,由于持续的合作,这些理事会所采用的术语与旅馆相同。传统药物的名称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由小麦卡特公司分配的幻想元素和一个揭示其班级的茎。例如,3-羟基-3-甲基 - 谷胱甘肽A抑制剂(用于高脂血症),共享后缀为“ -Vastatin”,而Beta阻滞剂具有后缀为“ -alol”。一些药物有第二个单词
一种正交激活的 CRISPR-Cas13d 纳米前药,可逆转化学耐药性,从而增强化学光动力疗法
通过运输氧化/还原形式的谷胱甘肽及其药物偶联物来改变细胞的氧化还原状态;并且与癌症的不良临床结果(例如预后不良)密切相关。4因此,MRP1 是耐药癌细胞的“致命弱点”之一。5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过基因沉默方法下调 MRP1 基因可以逆转 MRP1 介导的耐药性。6例如,已发现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相关蛋白 9 (CRISPR-Cas9) 技术可以逆转由 ATP 结合盒 (ABC) 转运蛋白介导的 MDR,由于其设计简单、靶区域灵活、编辑效率更高和多路复用,其结果明显高于其他基因编辑技术。 7 – 10 尽管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大多数 CRISPR-Cas9 系统仍然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包括非靶标基因组改变和基因毒性、Cas9 特异性 T 细胞的潜在免疫风险以及不令人满意的靶向递送。8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RNA 引导的 VI 型 Cas 蛋白 CRISPR-Cas13d 已被证实可在不改变基因组的情况下敲低靶基因。11,12 重要的是,与 Cas9 蛋白相比,
化学科学 - RSC 出版
通过运输氧化/还原形式的谷胱甘肽及其药物偶联物来改变细胞的氧化还原状态;并且与癌症的不良临床结果(例如预后不良)密切相关。4因此,MRP1 是耐药癌细胞的“致命弱点”之一。5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过基因沉默方法下调 MRP1 基因可以逆转 MRP1 介导的耐药性。6例如,已发现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相关蛋白 9 (CRISPR-Cas9) 技术可以逆转由 ATP 结合盒 (ABC) 转运蛋白介导的 MDR,由于其设计简单、靶区域灵活、编辑效率更高和多路复用,其结果明显高于其他基因编辑技术。 7 – 10 尽管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大多数 CRISPR-Cas9 系统仍然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包括非靶标基因组改变和基因毒性、Cas9 特异性 T 细胞的潜在免疫风险以及不令人满意的靶向递送。8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RNA 引导的 VI 型 Cas 蛋白 CRISPR-Cas13d 已被证实可在不改变基因组的情况下敲低靶基因。11,12 重要的是,与 Cas9 蛋白相比,
NPR1在系统性获得的气孔免疫中的作用
摘要:气孔免疫是植物病原体防御系统的主要门。与发病机理相关的非表达1(NPR1)是水杨酸(SA)受体,这对于气孔防御至关重要。sa诱导了气孔闭合,但是NPR1在后卫细胞中的特定作用及其对系统性获得的耐药性(SAR)的贡献仍然很大未知。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比较了野生型拟南芥和NPR1-1基因敲除突变体对病原体攻击的反应,从气孔运动和蛋白质组学变化方面。我们发现NPR1不调节气孔密度,但是在病原体攻击下,NPR1-1突变体未能关闭气孔,导致更多病原体进入叶子。此外,NPR1-1突变体中的ROS水平高于野生型中的ROS水平,并且几种参与碳固化,氧化磷酸化,糖酵解和谷胱甘肽代谢的蛋白质在丰度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发现表明,移动SAR信号通过启动ROS爆发改变了气孔免疫反应,而NPR1-1突变体通过翻译调节具有替代性启动效应。
氧化应激增强呼吸抑制剂对 MYC 驱动淋巴瘤的治疗作用
MYC 是多种肿瘤类型中的关键致癌驱动因素,但同时也使癌细胞具有一系列脆弱性,为有针对性的药物干预提供了机会。例如,抑制线粒体呼吸的药物会选择性地杀死 MYC 过表达的细胞。在这里,我们揭示了这种合成致死相互作用的机制基础,并利用它来提高呼吸复合物 I 抑制剂 IACS- 010759 的抗癌作用。在 B 淋巴细胞系中,异位 MYC 活性和 IACS- 010759 治疗加在一起会诱导氧化应激,从而导致还原谷胱甘肽的消耗和氧化还原稳态的致命破坏。这种效果可以通过抑制通过戊糖磷酸途径产生的 NADPH 或抗坏血酸(维生素 C)来增强,已知抗坏血酸在高剂量时可充当促氧化剂。在这些情况下,抗坏血酸与 IACS- 010759 协同作用,在体外杀死 MYC 过度表达细胞,并增强其对人类 B 细胞淋巴瘤异种移植的治疗作用。因此,复合物 I 抑制剂和高剂量抗坏血酸可能会改善高级别淋巴瘤和其他可能由 MYC 驱动的癌症患者的预后。
在脊髓损伤引起的大鼠中,甲壳虫水凝胶的受控药物输送系统的设计和局部应用是壳聚糖水凝胶的。评估神经组织的抗氧化剂变化
创伤性脊髓损伤(SCI)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伤害之一。氧化应激被认为是SCI继发期的迹象之一。因此,在患有脊髓损伤的大鼠中装有硒纳米颗粒的壳聚糖水凝胶的受控药物输送系统的设计和局部应用也被认为是神经组织中抗氧化剂变化的评估。为此,在60名女性大鼠中造成了实验性脊髓损伤,并将其随机分为三组; 1-对照组; 2-壳聚糖水凝胶组和3-壳聚糖水凝胶,装有硒纳米颗粒组。在受伤后的第3,第7,21和28天测量了脊髓组织中某些抗氧化剂的活性。结果清楚地表明,在治疗组创伤后的第3天和第7天,超氧化物歧化酶,丙二醛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数量的变化显着低于对照组。然而,在治疗组中,与对照组相比,过氧化氢酶活性水平并不显着。在本研究的两个治疗组中,脊髓(损伤部位)中自由基的创伤和产生可能较少。因此,通过减少损伤区域中氧化应激的量,带有硒纳米颗粒的壳聚糖水凝胶可能会对SCI产生积极影响。
使用基于LC-MS的代谢组方法,鉴定酪氨酸激酶抑制剂Pexidartinib的反应性代谢产物
摘要:Pexidartinib(Pex,Turalio)是巨噬细胞刺激性因子1受体的选择性和有效抑制剂,已批准用于治疗弯曲型巨型细胞肿瘤。然而,诊所已经报道了频繁和严重的不良反应,导致PEX对肝损伤的风险发出了盒装警告。与PEX相关的肝毒性(尤其是代谢相关的毒性)的机制仍然未知。在当前研究中,使用谷胱甘肽(GSH)和甲氧基胺(NH 2 OME)研究了人/小鼠肝微粒体(HLM/MLM)和原代人肝细胞(PHH)中PEX的代谢激活。使用基于LC- MS基于LC- MS的代谢组学方法,在HLM/MLM中鉴定了11个PEX-GSH和7个PEX-NH 2 OME加合物。此外,在PHH中检测到4个PEX-GSH加合物。CYP3A4和CYP3A5被确定为负责使用重组人P450和CYP3A化学抑制剂酮康唑形成这些加合物的主要酶。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PEX代谢可以产生由CYP3A介导的反应代谢产物,并且需要进一步研究反应性代谢物与PEX肝毒性的关联。
综述如何操纵抗坏血酸的生物合成、循环和调控途径来提高植物对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
摘要:干旱、盐度和极端温度等非生物胁迫是全球农作物生产力的主要限制因素,预计气候变化将加剧这些因素。活性氧 (ROS) 的过量产生是许多非生物胁迫的常见后果。抗坏血酸,也称为维生素 C,是植物细胞中最丰富的水溶性抗氧化剂,可以直接作为 ROS 清除剂对抗氧化应激,或通过抗坏血酸-谷胱甘肽循环(植物细胞中的主要抗氧化系统)对抗氧化应激。因此,通过工程改造具有增强抗坏血酸浓度的作物有可能促进广泛的非生物胁迫耐受性。已经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策略来增加植物中的抗坏血酸浓度:(i) 增加生物合成,(ii) 增强循环,或 (iii) 调节调节因子。在这里,我们回顾了植物中抗坏血酸生物合成、循环和调节的遗传途径,包括迄今为止用于增加模型和作物物种中抗坏血酸浓度的所有代谢工程策略的总结。然后,我们重点介绍利用基因组编辑工具来增加作物中抗坏血酸浓度的非转基因策略,例如编辑控制 GDP-L-半乳糖磷酸化酶基因翻译的高度保守的上游开放阅读框。
α3β1 整合素靶向聚合物多西紫杉醇作为... - 纯
摘要:多西他赛 (DTX) 广泛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患者,但存在剂量限制性副作用,尤其是神经毒性和骨髓抑制。在此,我们开发了环状 cNGQGEQc 肽导向聚合物囊体多西他赛 (cNGQ-PS-DTX),作为 NSCLC 的靶向多功能制剂。携带 8.1 wt % DTX 的 cNGQ-PS-DTX 尺寸为 93 nm,表面电荷为中性,稳定性高,并具有谷胱甘肽触发的 DTX 释放行为。细胞毒性研究表明,cNGQ-PS-DTX 在过表达 α 3 β 1 整合素的 A549 人肺癌细胞中的抗肿瘤活性明显优于游离 DTX 和非靶向 PS-DTX。cNGQ-PS-DTX 在小鼠中表现出非常高的耐受性(比游离 DTX 好 8 倍以上)和缓慢消除。重要的是,与 PS-DTX 和游离 DTX 对照相比,cNGQ-PS-DTX 表现出显著改善的肿瘤蓄积和更高的皮下和原位 A549 异种移植抑制率。α 3 β 1 整合素靶向聚合物囊泡多西紫杉醇成为治疗 NSCLC 的先进纳米治疗剂。关键词:肺癌、聚合物囊泡、多西紫杉醇、化疗、靶向递送
人类视网膜DNA甲基化的QTL映射鉴定了与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中的87个基因 - 异构组相互作用
DNA甲基化提供了将遗传变异与环境影响联系起来的关键表观遗传标记。我们已经分析了160个人视网膜的基于阵列的DNA甲基化蛋白纤维,具有共同测量的RNA-SEQ和> 800万个遗传变异,在CIS中揭示了遗传调节的位点,在CIS中(37,453个甲基化的定量性状定量特征和12,505表达定量的特性特征)和13,747 DNA甲基化的属性。视网膜特定的三分之一。甲基化和表达定量性状基因座表现出与突触,线粒体和分解代谢有关的生物过程的非随机分布和富集。基于数据的Mendelian ran统治和共定位分析确定了87个靶基因,其中甲基化和基因表达变化可能介导基因型对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的影响。综合途径分析揭示了免疫反应和代谢的表观遗传调节,包括谷胱甘肽途径和糖酵解。我们的研究定义了驱动甲基化变化的遗传变异的关键作用,优先考虑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控制,并提出了通过基因型 - 视网膜环境相互作用来调节黄斑变性病理学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