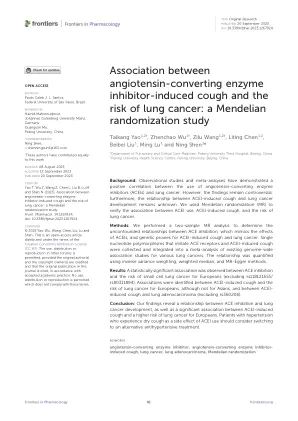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Bradykinin
过敏反应和Ace- ...
过敏反应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生命的多系统过敏反应,对生物触发器,从而从肥大细胞和粒细胞中释放出有效的炎症性介体,并在任何组合中包括皮肤,肺,肺,心脏或胃肠道中至少包括两个器官系统中的症状。一个例外是深度低血压作为孤立的症状。过敏反应有两种类型:免疫学和非免疫学。免疫过敏症将开始启动。如果未经治疗,可能会发生冲击(深度低血压)或窒息(气道阻塞)死亡。非免疫学途径可以在许多方面启动。一种异物可以直接与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脱粒。可以通过过敏毒素C3A和C5A的释放,随后募集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可以通过释放过敏毒素C3A和C5A进行免疫复合激活。最后,高摩尔对比剂会导致血细胞裂解,酶释放和补体激活,从而导致过敏反应(过敏反应)症状。在本报告中,我们强调了在肥大细胞依赖性过敏反应中募集铁丁蛋白形成的级联反应,这是严重低血压或气道妥协的潜在介体(哮喘,喉咙,喉咙水肿)。我们还考虑由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作用而导致内源性心动激肽代谢率降低,这不仅导致喉水肿瘤,而且导致舌头肿胀,并带有分泌物的吸入。
咳嗽的病理生理学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如何解释类内差异?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始终显示出跨多种心血管疾病的范围,包括高血压,冠状动脉疾病,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始终显示出改善的存活率和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ACEI的心脏保护作用抑制了血管紧张素I向血管紧张素II的转化和抑制缓激肽降解。它们的耐受性良好,但可能会导致某些患者的干咳嗽发作。本评论提供了有关与ACEI使用相关的咳嗽的发病率和机制的当前证据,然后考虑如何在临床实践中管理与ACEI相关的咳嗽。由于源数据中的异质性和缺乏适当的控制,ACEI引起的咳嗽的发生率差异很大。的发病率在单个ACEI之间也有所不同,诸如Perindopril等药物(具有较高的组织ACE亲和力),与咳嗽率较低有关。现实世界研究的证据表明,ACEI相关的咳嗽的发生率低于临床试验中报告的率。经历任何干性咳嗽的患者通常会转变为血管紧张素阻滞剂或其他类别的降压药,无论咳嗽严重程度如何。为了避免在临床实践中ACEI的不当中断,持续咳嗽的患者的另一种方法是进行挑战/重新挑战,以确定ACEI的重新引入是否与症状的复发有关。咳嗽的发生率不应被视为ACEI的班级效应,并且患者可能会从一个ACEI转换为另一个ACEI。应尽一切努力使患者继续ACEI治疗,以减少心血管不良后果并提高生存率。
乙酰胆碱引起的冠状动脉血管收缩和...
apptracf。我们研究了外源施用的乙酰胆碱,一氧化氮,ADP,ATP,Bra-Dykinin和PESTS P对分离的新生儿猪心(S4 D)中冠状血管张力的影响(S4 D)。节奏(180 bpm),在恒定的冠状动脉流量mL/min/min/g上具有富含红细胞的溶液(HEMATO-CRIT 0.15-0.20),进行逆行主动脉灌注,与MM Hg的灌注压力相对应。激动剂被注入主动脉根,并评估了基线和左心室压力发育的冠状动脉灌注压力变化。一氧化氮(3 jll),ADP(30 nmol),ATP(30 nmol),Bradykinin(125 ng)和物质P(50 ng)降低了16.9±1.2,25.3±4.4,18.4,18.3±4.4,18.3±1.2,18.9±1.m&1.4,&1.4,和1.4,和1.4,和1.4,和1.4±1.4,和1.4±1.4,和1.4,和1.4,和1.4,和1.4±1.4±1.4±1.4±1.4±1.4。乙酰胆碱(0.5和1.0 nmol)产生适度的灌注压力(血管扩张)4.2±0.8和3.8±0.5 mm Hg,而乙酰胆碱(5、20和100 nmol)(5、20和100 nmol)增加了灌注压力(Vasocococcoccoccoccoccotiancy)。分别为15.1 mm Hg。乙酰胆碱还分别从108.7±5.0降低至69.2±4.6、56.3±6.1和48.2±6.4 mm Hg的乙酰胆碱,分别为5、20和100 nmol剂量。对乙酰胆碱的反应被阿托品(50 nmol)废除。在一组单独的心脏中,吲哚美辛(10-6 m)分别降低了5、20和100 nmol剂量的乙酰胆碱的灌注压力变化,分别降低了87%,66%和48%。(Pediatr Res 32:236-242,1992)在其他心脏中,钙通道拮抗剂Nisoldipine(10-7 m)分别降低了5、20和100 nmol剂量的乙酰胆碱的灌注压力的峰值变化,分别降低了87%,77%和56%。总而言之,乙酰胆碱主要导致新生儿猪心中的冠状动脉血管收缩和负性肌力作用。这两种动作都是毒蕈碱受体介导的。我们的数据还表明,环氧酶产物可能部分参与了这种血管收缩,并且细胞外钙的来源有助于血管收缩过程。
Schmidt_遗传性血管性水肿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孟德尔随机化研究结果_审查后划红线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是一种罕见疾病,每 5 万到 10 万中就有一例发生。[1] 其特征是皮肤和黏膜下组织反复肿胀,这是由于遗传性 C1 抑制剂缺乏导致缓激肽产生抑制不足所致。C1 抑制剂通过抑制几种丝氨酸蛋白酶(包括补体 C1a、C1r、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丝氨酸蛋白酶 1 (MASP-1)、MASP-2、纤溶酶、激肽释放酶和凝血因子 XIa 和 XIIa)来控制补体、纤溶酶、内源性凝血和接触系统。[2] D-二聚体水平通常在血管性水肿发作期间升高(可能是由于纤溶酶生成增强),但血管性水肿发作期间的这种升高与血栓风险增加无关。[3]几篇关于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评论指出,HAE(即使在 D-二聚体水平升高的情况下)也不会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的风险。但是,除了患者和医生的经验之外,没有其他资料可以支持这一说法。但是,最近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检查了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与 C1 抑制剂缺乏症的许多潜在合并症,报告了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与 VTE 之间的关联。[4, 5]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可能会因 VTE 的指征和错误分类而受到混淆。[6] 鉴于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极为罕见,很难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调查这一发现。如果 HAE 确实与 VTE 有关,则可以假设 C1 抑制剂水平不太明显的变化也可能与 VTE 风险有关。孟德尔随机化 (MR) 是一种适合进一步研究 C1 抑制剂水平与 VTE 潜在风险之间潜在因果关系的方法。MR 是一种使用遗传变异作为工具来评估暴露和结果之间潜在因果关系的方法。MR 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受通常困扰观察性研究的混杂和反向因果关系风险的影响要小得多。Davies 等人撰写了一份关于孟德尔随机化工作原理的全面概述。[7] 为了探索较低的 C1 抑制剂水平与静脉血栓栓塞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进行了一项孟德尔随机化研究。
经鼻靶向给药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叙述性综述
目前,神经干预、手术、药物和中枢神经系统 (CNS) 刺激是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主要方法。这些方法用于克服血脑屏障 (BBB),但它们具有局限性,因此需要开发靶向递送方法。因此,最近的研究集中于时空直接和间接靶向递送方法,因为它们可以减少对非靶细胞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作用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治疗剂能够直接穿过 BBB 以促进递送至靶细胞的方法包括使用纳米药物(纳米颗粒和细胞外囊泡)和磁场介导递送。纳米颗粒根据其外壳组成分为有机和无机类型。细胞外囊泡由凋亡小体、微囊泡和外泌体组成。磁场介导的递送方法包括磁场介导的被动/主动辅助导航、趋磁细菌、磁共振导航和磁性纳米机器人——按其发展时间顺序排列。间接方法增加血脑屏障通透性,使治疗剂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化学递送和机械递送(聚焦超声和激光治疗)。化学方法(化学渗透促进剂)包括甘露醇(一种普遍的血脑屏障通透剂)和其他化学物质——缓激肽和 1-O-戊基甘油——以解决甘露醇的局限性。聚焦超声有高强度和低强度两种。激光治疗包括三种类型:激光间质治疗、光动力治疗和光生物调节治疗。直接和间接方法的结合并不像单独使用那样常见,但代表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本综述旨在分析这些方法的优缺点,描述直接和间接递送的联合使用,并提供每种靶向递送方法的未来前景。我们得出结论,最有前途的方法是通过鼻腔到中枢神经系统输送混合纳米药物、有机、无机纳米粒子和外泌体的多种组合,然后通过光生物调节疗法或低强度聚焦超声进行预处理,以此作为将本综述与其他针对中枢神经系统输送的综述区分开来的策略;然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这种方法在更复杂的体内途径中的应用。
COVID-19:自身免疫,多系统炎症和自身免疫性风湿病患者
自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以来,我们已经对疾病的发育,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治疗,病程和外表现有了很多了解(参考文献1、2)。COVID-19的过程包括多个阶段,这也决定了指定的治疗策略(参考文献1-3)。第1阶段是发烧,呼吸道或胃肠道症状和淋巴细胞减少症的早期病毒感染期。阶段2是肺相。它分为两种替代:非甲状体学期2a和低氧阶段2B。最后,第3阶段是多系统炎症性合成(MIS)的阶段,偶尔伴有细胞因子风暴作为致病性(参考文献1-3)。重要的是要注意,仅2%的患者和8-11%的严重患者发生了真正的“细胞因子风暴”(参考4)。COVID-19的晚期阶段还涉及Bradykinin Storm(参考文献5),激活和补体级联反应(参考6),内皮炎,血管泄漏和水肿(参考6),微实性事件(参考4)和中性粒细胞外陷阱(Net)(参考7)。由于这些抗炎药在MIS期间最有效,因此应通过临床,成像和实验室标记来证实这一点(参考文献1,8-10)。作为风湿病学家和免疫学家,我们遇到了许多与自身免疫性以及风湿性和肌肉骨骼疾病(RMD)特别相关的重要问题。(1)COVID-19可能会增加自身抗体生产和自身免疫性的风险(参考文献Laboratory biomarkers, such as C-reactive protein, ferritin, D-dimer, cardiac troponin (cTn), NT-proBNP, lymphopenia,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if available, circulating interleukin 6 (IL-6) level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MIS in Stages 2b-3 and also with the outcome of COVID-19 (Refs 9 - 11)。COVID-19,自身免疫,全身炎症和RMD之间可能存在多种相互作用。12)。(2)自身免疫性炎症RMD可能会增加敏感性急性呼吸综合征2(SARS-COV-2)感染(参考文献13)。(3)现在很明显,在Covid-19的更高级阶段,系统性炎症和MIS,而不是原始的病毒感染可能占主导地位(参考文献3、8、9、14-16)。(4)由于上述结果,成功用于治疗RMD的免疫抑制药物,例如皮质类固醇,生物剂或Janus激酶(JAK)抑制剂,也可能适用于严重的COVID-19和全身性炎症患者(药物重复使用)(药物重复使用)(参考)17-19-19-19-19-19-19-19。(5)在19009年期间如何管理自身免疫性RMD的患者也至关重要(参考文献20-23)。(6)针对SARS-COV-2的RMD患者的疫苗接种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参考文献24,25)。在这里,我们将简要讨论与自身免疫,MIS和RMD患者有关的所有这些问题。
COVID-19:自身免疫、多系统炎症和自身免疫性风湿病患者
自 2019 年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爆发以来,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有关该疾病的发展、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治疗、病程和结果的知识(参考文献 1、2)。COVID-19 的病程包括多个阶段,这也决定了所需的治疗策略(参考文献 1 – 3)。第 1 期是病毒感染早期,伴有发烧、呼吸道或胃肠道症状和淋巴细胞减少。第 2 期是肺部阶段。它分为两个亚期:非缺氧血症第 2a 期和缺氧血症第 2b 期。最后,第 3 期是多系统炎症综合征 (MIS) 的阶段,偶尔伴有细胞因子风暴作为致病特征(参考文献 1 – 3)。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细胞因子风暴”仅发生在 2% 的患者和 8-11% 的重症患者中(参考文献 4)。COVID-19 的晚期阶段还涉及缓激肽风暴(参考文献 5)、凝血和补体级联的激活(参考文献 6)、内皮炎、血管渗漏和水肿(参考文献 6)、微血栓事件(参考文献 4)和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 (NET)(参考文献 7)等机制。由于这些抗炎药物在 MIS 期间最有效,因此应通过临床、影像学和实验室标志物来确认(参考文献 1、8-10)。实验室生物标志物,例如 C 反应蛋白、铁蛋白、D-二聚体、心肌肌钙蛋白 (cTn)、NT-proBNP、淋巴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以及(如果有)循环白细胞介素 6 (IL-6) 水平与 2b-3 期 MIS 以及 COVID-19 的结果有关(参考文献 9 - 11)。作为风湿病学家和免疫学家,我们遇到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自身免疫以及风湿病和肌肉骨骼疾病 (RMD) 特别相关。COVID-19、自身免疫、全身炎症和 RMD 之间可能存在多种相互作用。(1)COVID-19 可能会增加自身抗体产生和自身免疫的风险(参考文献 12)。 (2) 自身免疫炎症性 RMD 可能会增加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SARS-CoV-2) 感染的易感性(参考文献 13)。(3)现已清楚,在 COVID-19 的晚期阶段,全身炎症和 MIS 而不是原始病毒感染可能主导临床表现(参考文献 3、8、9、14-16)。(4)因此,成功用于治疗 RMD 的免疫抑制药物,如皮质类固醇、生物制剂或 Janus 激酶 (JAK) 抑制剂,也可用于治疗严重 COVID-19 和全身炎症患者(药物再利用)(参考文献 17-19)。(5)在 COVID-19 期间如何管理自身免疫性 RMD 患者也至关重要(参考文献 20-23)。 (6) RMD 患者接种 SARS-CoV-2 疫苗也是一个基本问题(参考文献 24、25)。在这里,我们将简要讨论与自身免疫、MIS 和 RMD 患者相关的所有这些问题。
孟德尔随机化
全球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全球有近 12.8 亿患者患有高血压(截至 2019 年)(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协作组织 NCD-RisC,2021 年),6430 万患者患有心力衰竭(截至 2017 年)(Bragazzi 等人,2021 年)。这些疾病造成了沉重的医疗保健和经济负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 抑制剂 (ACEI) 是广泛用于治疗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一线基石药物。ACEI 对治疗高血压具有显著效果(George 等人,2010 年)。然而,ACEI 的副作用仍然存在争议。许多临床研究表明,ACEI 可导致多达 20% 的患者出现干咳(Israili 和 Hall,1992 年;Unger 等人,2020 年)。癌症作为使用 ACEI 的潜在不良事件,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和患者的关注。最近的临床研究表明,肺癌是使用 ACEI 的一个显著不良事件( Hicks 等人,2018 年;Lin 等人,2020 年;Kristensen 等人,2021 年)。本研究作者(Wu 和 Yao)最近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Wu 等人,2023 年)表明,与使用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相比,使用 ACEI 是肺癌的更大风险因素(高达 1.6%),尤其是在亚洲患者中。虽然许多临床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现象,但尚未进行随机对照试验(RCT)来证实 ACEI 使用与肺癌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既往开展的ACEI类药物的RCT仅评估了ACEI类药物对心血管和肾脏终点的影响(The GISEN Group,1997;Fox等,2003),并未纳入癌症的发病率。多种因素导致RCT的实施十分困难,在以往的观察性研究中,潜在混杂因素的干扰可能是造成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此外,验证危险因素与结局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困难,此外,反向因果关系也可能暗示这种关系。在此条件下,孟德尔随机化(MR)作为一种天然的随机对照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利用药物靶点相关的基因变异来模拟药物作用或不良事件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述问题(Gill等,2019)。根据孟德尔遗传定律,父母的等位基因是随机分配给后代的。遗传变异不太可能受到出生后环境、社会经济地位和行为因素的影响。 此外,MR的因果时间序列合理,研究设计最小化了残留混杂因素。 因此,使用基因作为工具变量研究疾病关联性近年来成为流行病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Emdin et al.,2017)。最近的荟萃分析(Wu et al., 2023)显示,亚洲人使用 ACEI 可能患肺癌的风险更高。尽管一些研究人员(Hicks et al., 2018; Borghi et al., 2023)发现 ACEI 引起的咳嗽或致癌作用与 P 物质和缓激肽有关,但没有相关的临床研究支持这一发现。此外,尚不清楚 ACEI 引起的咳嗽是否与肺癌有关。因此,我们旨在通过 MR 分析回答以下问题:ACEI 会导致肺癌吗?不同种族使用 ACEI 患肺癌的风险是多少?ACEI 是否会导致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