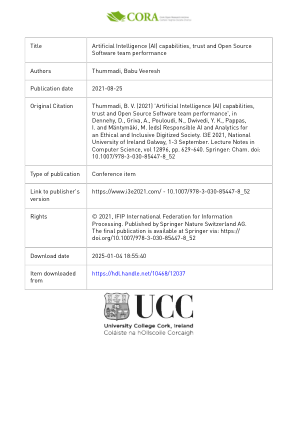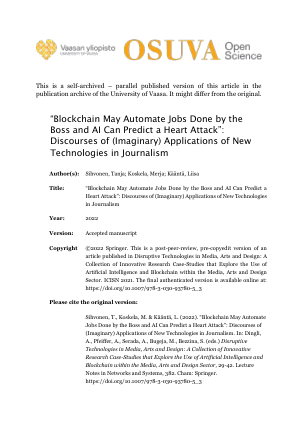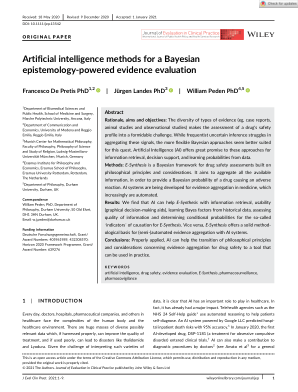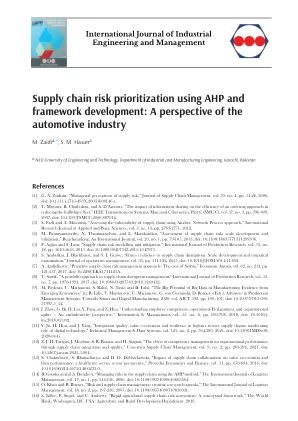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宽恕:我们给予自己的礼物
6. Rippentrop AE、Altmaier EM、Chen JJ、Found EM、Keffala VJ。《宗教/精神信仰与慢性疼痛人群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疼痛之间的关系》。《疼痛》。2005;116(3):311-321。 7. Carson JW、Keefe FJ、Goli V 等人。《宽恕与慢性腰痛:一项初步研究,探讨了宽恕与疼痛、愤怒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疼痛杂志》。2005;6(2):84-91。 8. Lin WF、Mack D、Enright RD、Krahn D、Baskin TW。《宽恕疗法对住院物质依赖患者愤怒、情绪和物质使用脆弱性的影响》。《临床心理学咨询杂志》。2004;72(6):1114-1121。 9. Akhtar S、Barlow J。宽恕疗法对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Trauma Violence Abus。2018;19(1):107-122。10. Toussaint LL、Shields GS、Slavich GM。宽恕、压力和健康:一项为期 5 周的动态平行过程研究。Ann Behav Med。2016;50(5):727-735。11. Peterson SJ、Van Tongeren DR、Womack SD、Hook JN、Davis DE、Griffin BJ。自我宽恕对心理健康的益处:来自相关性和实验研究的证据。J Posit Psychol。2017;12(2):159-168。12. Davis DE、Ho MY、Griffin BJ 等。原谅自己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一项荟萃分析综述。J Couns Psychol。2015;62(2):329-335。13. Cleare S、Gumley A、O'Connor RC。自我同情、自我原谅、自杀意念和自我伤害:一项系统评价。临床心理学心理治疗。2019;26(5):511-530。14. Lee YR、Enright RD。原谅他人与身体健康之间关系的荟萃分析。心理健康。2019;34(5):626-643。15. O'Beirne S、Katsimigos A、Harmon D。宽恕与慢性疼痛:一项系统评价。爱尔兰医学科学杂志。2020;189:1359-1364。 16. Rasmussen KR、Stackhouse M、Boon SD、Comstock K、Ross R。《宽恕与健康之间的元分析联系:宽恕相关区别的调节作用》。《心理健康》。2019;34(5):515-534。17. Enright R、Freedman S、Rique J。《人际宽恕心理学》。收录于:Enright RD、North J 编辑。《探索宽恕》。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8 年。18. Enright RD、Fitzgibbons RP。(2015 年)。《宽恕疗法:化解愤怒和恢复希望的实证指南》。华盛顿特区:美国心理学会。
原始引文 Thummadi, BV (2021) “人工智能 (AI) 能力、信任和开源软件团队绩效”,收录于 Dennehy, D.、Griva, A.、Pouloudi, N.、Dwivedi, YK、Pappas, I. 和 Mäntymäki, M. (eds) 为道德和包容的数字化社会提供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和分析。I3E 2021,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分校,9 月 1-3 日。计算机科学讲义,第 12896 卷,第 629-640 页。Springer:Cham。doi:10.1007/978-3-030-85447-8_52
尽管人工智能在开源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开源软件(OSS)团队绩效的重要问题上,人们所做的研究却很少[2, 5]。人工智能能力可以被认为是开源团队的一个独特特征,可以衡量开源团队寻求人工智能机会和资源的倾向。例如,人工智能可以以机器人的形式作为OSS团队的基础设施,以简化开源流程,如关闭拉取请求、故障排除、迎接新用户等。同时,OSS团队还可以探索人工智能的新商机,以增加项目的吸引力。由于开源社区以多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因此尚不清楚人工智能能力如何影响OSS团队的绩效[4]。因此,我想问:
参考文献 168
Sharffenberg, WA、Fleming, MJ,2010。水文建模系统,HEC-HMS 用户手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水文工程中心 -HEC),美国华盛顿特区。Simon, HA,1981。人工智能科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Simonovic, SP,2009。水资源管理:系统方法和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法国巴黎/英国伦敦。Simpson, J.、Adler, RF、North, GR,1988。拟议的热带降雨测量任务 (TRMM) 卫星。美国气象学会公报 69,278-295。Skaags, RW、Khaleel, R.,1982。渗透,小流域的水文建模。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美国密歇根州圣约瑟夫。 Smith, L., Turcotte, D., Isacks, B., 1998. 使用离散小波变换的河流流量特性和特征检测。《水文过程》12,233-249。 Southgate, D., Whitaker, M., 1994. 经济进步与环境: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 Sprague, RH, Watson, HJ, 1993. 决策支持系统:将理论付诸实践。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ts,NJ Tecle, A., Duckstein, L., 1994. 多准则决策制定概念,载于:Bogardi Janos J.、Hans-Peter, N. (Eds.),《水资源管理中的多准则决策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法国巴黎。 Tian, Y., Peters-Lidard, CD, 2010. 卫星降水测量不确定性全球图。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37,doi:10.1029/2010GL046008。Turban, E.,2007。决策支持和商业智能系统。Pearson Prentice Hall,美国新泽西州 Upper Saddle River。USDA,1986。TR-55:小型流域城市水文学。美国农业部;国家资源保护局 (NCRS),华盛顿。USDA,2004。国家工程手册,第 630 部分:水文学:暴雨直接径流估算。自然资源保护局 (NRCS),美国农业部,华盛顿特区,美国。van Ast, AJ,2000。国际河流流域互动管理;北美和西欧的经验。地球物理学和化学,B 部分:水文学、海洋和大气 25,325-328。 van Dam, AA、Kelderman, P.、Kansiime, F.、Dardona, A.,2007 年。乌干达(东非)维多利亚湖附近纸莎草湿地氮滞留模拟模型。湿地生态与管理 15, 469-480。 van der Knijff, JM, Younis, J., de Roo, APJ, 2010。LISFLOOD:基于 GIS 的流域规模水平衡和洪水模拟分布式模型。国际地理信息科学杂志 24, 189-212。 van Griensven, A., Alvarez-Mieles, M., 2009。Abras de Mantequilla 湿地和影响区域的环境监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HE,荷兰代尔夫特。 van Griensven, A.、Xuan, Y.、Haguma, D.、Niyonzima, W., 2008。使用遥感数据和建模了解河流湿地集水区过程,收录于:Sánchez-Marrè, M.、Béjar, J.、Comas, J.、Rizzoli, AE、Guariso, G. (Eds.),国际环境建模与软件大会。iEMSs,西班牙巴塞罗那,第 462-469 页。Vernimmen, RRE、Hooijer, A.、Mamenun, Aldrian, E.、van Dijk,AIJM,2012 年。印度尼西亚干旱监测卫星降雨数据的评估和偏差校正。水文与地球系统科学杂志 16,133-146。 Villa-Cox, G.、Arias-Hidalgo, M.、Mino, S.、Delgado-Cabrera, L.,2011。情景描述、管理选项和相关指标:Abras de Mantequilla 案例研究情况说明书,WP7。 WETWin 项目,ESPOL 大学,厄瓜多尔瓜亚基尔。
Sihvonen, T.、Koskela, M. 和 Kääntä, L. (2022)。“区块链可以自动化老板的工作,人工智能可以预测心脏病发作”:新技术在新闻业的(想象)应用论述。收录于:Dingli, A.、Pfeiffer, A.、Serada, A.、Bugeja, M. 和 Bezzina, S. (eds.) 媒体、艺术和设计中的颠覆性技术:探索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在媒体、艺术和设计领域应用的创新研究案例研究集,第 29-42 页。网络和系统讲义,第 382 页。Cham:Springer。https://doi.org/10.1007/978-3-030-93780-5_3
摘要。本章探讨了如何在新闻业中形成对新抽象技术潜在用途的共同理解。我们分析了 2015 年至 2020 年的芬兰新闻文本,其中向读者介绍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AI),并对其进行了概念化和讨论。借鉴经典的技术接受模型 (TAM),我们讨论了新闻业如何构建和重新构建这些技术的显着属性,尤其是在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方面。此外,通过将这些推测性含义视为技术或算法想象的反映,我们研究了解释其潜在或想象应用的话语。这项研究很重要,因为技术不是作为具体的设备或程序进入人们的生活,而是最初作为概念、想象和情感实体进入人们的生活。
用于贝叶斯认识论证据评估的人工智能方法
1.Rajkomar A、Oren E、Chen K 等人。利用电子健康记录进行可扩展且准确的深度学习。npj 数字医学。2018;1(1):1 – 10。https://doi.org/10.1038/s41746-018-0029-1。2.Paydar S、Pourahmad S、Azad M 等人。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建立甲状腺结节恶性风险预测模型。《中东癌症杂志》。2016;7(1):47-52。3.Amato F、López A、Peña-Méndez EM、Va ň hara P、Hampl A、Havel J.医学诊断中的人工神经网络。J Appl Biomed。2013; 11(2):47-58。 https://doi.org/10.2478/v10136-012-0031-x。4.莫赫塔尔 AM.未来医院:业务架构视图。马来医学科学杂志。2017;24(5):1-6。 https://doi.org/10.21315/mjms2017.24.5.1。5.Liu X、Faes L、Kale AU 等人。深度学习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医学影像检测疾病方面的表现比较: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柳叶刀数字健康。2019;1(6):e271-e297。https://doi.org/10.1016/s2589-7500 (19)30123-2。6.Nagendran M、Chen Y、Lovejoy CA 等人。人工智能与临床医生:深度学习研究的设计、报告标准和主张的系统回顾。英国医学杂志。2020;368:m689。https://doi.org/10.1136/bmj.m689。7.Panch T、Pearson-Stuttard J、Greaves F、Atun R. 人工智能:公共健康的机遇和风险。柳叶刀数字健康。2019;1 (1):e13-e14。https://doi.org/10.1016/s2589-7500(19)30002-0。8.Landes J、Osimani B、Poellinger R. 药理学中的因果推理的认识论。欧洲哲学杂志。2018;8(1):3-49。 https://doi.org/10。1007/s13194-017-0169-1。9.Abdin AY、Auker-Howlett D、Landes J、Mulla G、Jacob J、Osimani B.审查机械证据评估者 E-synthesis 和 EBM +:阿莫西林和药物反应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全身症状 (DRESS) 的案例研究。当前药学设计。2019;25(16):1866-1880。https://doi.org/10.2174/1381612825666190628160603。10.De Pretis F,Osimani B.药物警戒计算方法的新见解:E-synthesis,一种用于因果评估的贝叶斯框架。国际环境研究公共卫生杂志。11.2019;16(12):1 – 19。https://doi.org/10.3390/ijerph16122221。De Pretis F、Landes J、Osimani B。E-synthesis:药物监测中因果关系评估的贝叶斯框架。Front Pharmacol 。2019;10:1-20。https://doi.org/10.3389/fphar.2019.01317。12。De Pretis F、Peden W、Landes J、Osimani B。药物警戒作为个性化证据。收录于:Beneduce C、Bertolaso M 编辑。个性化医疗正在形成。从生物学到医疗保健的哲学视角。瑞士 Cham:Springer;2021:19 即将出版。13.那不勒斯 RE。学习贝叶斯网络。Prentice Hall 人工智能系列。新泽西州 Upper Saddle River:Pearson Prentice Hall;2004 年。14.Hill AB。环境与疾病:关联还是因果关系?J R Soc Med。2015;108(1):32-37。本文首次发表于 JRSM 第 58 卷第 5 期,1965 年 5 月。https://doi.org/10.1177/ 0141076814562718。15.Mercuri M、Baigrie B、Upshur RE。从证据到建议:GRADE 能帮我们实现目标吗?J Eval Clin Pract 。2018;24(5):1232- 1239。https://doi.org/10.1111/jep.12857。
使用 AHP 和框架对供应链风险进行优先级排序...
[1] GA Zsidisin,“管理者对供应风险的认知”,《供应链管理杂志》,第 39 卷,第 4 期,第 14-26 页,2006 年,doi:10.1111/j.1745-493X.2003.tb00146.x。[2] T. Moyaux、B. Chaib-draa 和 S. D'Amours,“信息共享对订购方法在减少牛鞭效应方面的效率的影响”,《IEEE 系统、人与控制论汇刊》,C 部分 (SMC-C),第 37 卷,第 3 期,第 396-409 页,2007 年,doi:10.1109/TSMCC.2006.887014。 [3] S. Fazli 和 A. Masoumi,“使用分析网络过程方法评估供应链的脆弱性”,《国际应用与基础科学研究杂志》,第 3 卷,第 13 期,第 2763-2771 页,2012 年。[4] M. Punniyamoorthy、N. Thamaraiselvan 和 L. Manikandan,“供应链风险评估:量表开发与验证”,《基准测试:国际杂志》,第 20 卷,第 1 期,第 79-105 页,2013 年,doi:10.1108/14635771311299506。[5] F. Aqlan 和 S. Lam,“供应链风险建模与缓解”,《国际生产研究杂志》,第 53 卷,第 13 期,第 2763-2771 页,2012 年。 18,第 5640-5656 页,2015 年,doi:10.1080/00207543.2015.1047975。[6] S. Ambulkar、J. Blackhurst 和 SJ Grawe,“企业对供应链中断的适应力:量表开发和实证检验”,运营管理杂志,第 33 卷,第 111-122 页,2015 年,doi:10.1016/J.JOM.2014.11.002。[7] A. Andjelkovic,“主动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方法 - 塞尔维亚案例”,经济年鉴,第 62 卷,第 5640-5656 页,2015 年,doi:10.1080/00207543.2015.1047975。 214,第 121-137 页,2017 年,doi:10.2298/EKA1714121A。[8] T. Sawik,“供应链中断管理的投资组合方法”,《国际生产研究杂志》,第 55 卷,第 7 期,第 1970-1991 页,2017 年,doi:10.1080/00207543.2016.1249432。 [9] M. Pavlovi ć、U. Marjanovi ć、S. Raki ć、N. Tasi ć 和 B. Lali ć,“大数据在制造业的巨大潜力: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证据”,收录于:B. Lalic、V. Majstorovic、U. Marjanovic、G. von Cieminski 和 D. Romero(编),生产管理系统的发展。迈向智能数字化制造,2020 年,卷 AICT 592,第 100–107 页,doi:10.1007/978-3-030-57997-5_12。[10] J. Zhou、G. Bi、H. Liu、Y. Fang 和 Z. Hua,“理解员工能力、运营 IS 一致性和组织敏捷性——一种灵巧的视角”,信息与管理,卷55,第 6 期,第 695-708 页,2018 年,doi:10.1016/j. im.2018.02.002。[11] Y. Ju、H. Hou 和 J. Yang,“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整合质量、价值共创和弹性:数字技术的调节作用”,工业管理与数据系统,第 121 卷,第 2 期,第 364-380 页,2021 年,doi:10.1108/IMDS-08-2020-0445。[12] ZJH Tarigan、J. Mochtar、SR Basana 和 H. Siagian,“能力管理通过供应链整合和质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不确定的供应链管理,第 9 卷,第 2 期,第 364-380 页,2021 年,doi:10.1108/IMDS-08-2020-0445。 2,第 283-294 页,2021 年,doi:10.5267/j.uscm.2021.3.004。[13] S. Chakraborty、S. Bhattacharya 和 DDDobrzykowski,“供应链协作对价值共创和公司绩效的影响:医疗服务业视角”,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第 11 卷,第 676-694 页,2014 年,doi:10.1016/S2212-5671(14)00233-0。[14] B. Gaudenzi 和 A. Borghesi,“使用 AHP 方法管理供应链中的风险”,国际物流管理杂志,第 17 卷,第 1 期,第 114-136 页,2006 年,doi:10.1108/09574090610663464。[15] O. Khan 和 B. Burnes,“风险与供应链管理:制定研究议程”,国际物流管理杂志,第 18 卷,第 1 期,第 114-136 页,2006 年,doi:10.1108/09574090610663464。 2,第 197-216 页,2007 年,doi:10.1108/09574090710816931。[16] S. Jaffee、P. Siegel 和 C. Andrews,“快速农业供应链风险评估:概念框架”,世界银行,美国华盛顿特区:农业和农村发展部,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