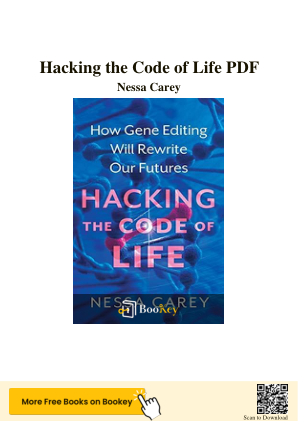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podsumowanie raportu技术愿景2024
但是,前景不必与艺术家的想象相符 - 前提是我们改变了与技术的关系并应得的(或目标)来加强使我们人民的原因。是时候进行更改了。在未来几年中,企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技术选择,从而可以提高人类潜力,生产力和创造力。自主代理人准备代表我们采取行动;智能界面改变了我们对信息和计算机程序的态度;由于我们从桌子后面移到工厂或山顶,它们连接数字和物理世界的空间技术;甚至大脑计算机界面界面BCI)以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 都开始在业务中找到重要的应用。过早的用户和领先的公司已经开始朝着新价值和可能性时代的竞争。他们的策略有一个共同的线程 - 技术变得越来越人性化。
超人:基因工程和以人为本的生物工程的含义
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在寻求改善自身并获得优势的方法,无论是通过信息、技术还是身体增强。尽管机器学习的进步为计算机具有“超人”能力提供了希望,但另外两项进步很快将提供只有科幻小说才能想象和探索的选择。生物技术——具体来说,利用技术对生物进行物理改造——的发展轨迹超越了可逆的“人机合作”,最终实现了像机器人一样的无尽增强和修改的可能性。而基因工程,尤其是 CRISPR 1(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和相关技术提供的可访问性,其发展轨迹有望使人类从出生起就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优秀”,预示着“高级人类”的到来。
电子工程
电子产品无处不在,它是信息、通信、控制、自动化、能源、电动汽车和航空电子时代所有当前和未来技术不可替代的基础。电子学研究不断进行并受到各种不同需求的推动。例如,越来越快、越来越低功耗的微处理器以及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无缺陷的存储器是任何计算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子电路,智能机器就无法实现,而只能是科幻小说。超灵敏、微型的半导体传感器,在最先进的机器人系统和无处不在的广泛分布式网络中,能够相互通信并与外界通信,对于获取现实世界、理解现实世界、管理现实世界、控制现实世界和干预现实世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子设备,机器就无法自主,与机器的交互也只能是虚拟的。
汽车-T细胞传奇 - 癌症
在4月13日(星期六)在洛杉矶的一项政府中,米歇尔·萨德兰(Michel Sadelain)因这种细胞免疫疗法的发展而有效。由硅谷企业家创建的,这种“奥斯卡式科学”经过是诺贝尔的前房。“从那以后,多年来,这种治疗策略已经通过了科幻小说了,”他说。他正在分享与美国免疫学家Carl June相关的300万美元,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到费城。如果第一位患者于2007年在纽约医院接受治疗,卡尔·六月的小组将于2011年出版,这是慢性白血病的第一个标志临床结果。在2013年,MSKCC团队将在成年人的急性Leuchies和Carl June的急性Leuchies中做同样的事情。
破解生命密码 PDF
在这个科幻小说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世界里,Nessa Carey 的《破解生命密码》对革命性的基因工程领域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探索。通过引人入胜的叙述和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Carey 揭开了 CRISPR 技术的复杂世界及其对医学、农业和其他领域的惊人影响的神秘面纱。这本书不仅是基因编辑的入门书,而且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我们如何利用或滥用这种强大的力量来改变生命的本质。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科学家还是好奇的外行,Carey 富有洞察力的文字都会让您思考我们新发现的改写基因命运的能力所引发的伦理、社会和生存问题。深入这段迷人的旅程,发现刻在我们 DNA 中的秘密如何重塑人类的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的爱情
4 饰演 L3 的女演员菲比·沃勒-布里奇和饰演兰多的演员唐纳德·格洛弗也这么认为。正如沃勒-布里奇所说:“唐纳德和我都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爱,他们之间是一种带着大写字母‘R’的浪漫联系。”(见 https://www.syfy.com/syfywire/phoebe-waller-bridge-on-l3-and-lando-the-first-romantic-human-droid- romance-in-star-wars)5 有趣的是,阿什/阿什机器人的扮演者多姆纳尔·格里森,他也是《机械姬》中程序员迦勒的扮演者。因此,格里森塑造了人机浪漫关系中双方的人物。6 科幻小说也经常探索机器可以替代遥不可及的爱情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吸血鬼猎人巴菲》第五季中,斯派克向巴菲表白了自己的爱意,却遭到了她的严厉拒绝,之后他委托制作了巴菲机器人。
隐私是数字世界的共同利益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开始寻找范式,以便理解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并为可能形成电子空间的社会世界提供愿景。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将这个世界称为赛博空间,即“不是空间的空间”。(吉布森,1986,38)在大众媒体和学术媒体中都可以找到截然不同的愿景:狂野的西部或虚拟社区;种族、性别、民族和收入无关紧要的地方或分层的环境,其中根据您是谁以及您过去消费的东西提供选择;信息自由流动的地方或每一点数据都可以商品化的地方;一个珍惜旧的行为规范并发展新规范的公民社会或一个霍布斯国家,其中火焰四起,混乱不堪。这些对比可能都代表着极端(Negroponte,1995 和 Stoll,1995),而事实往往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