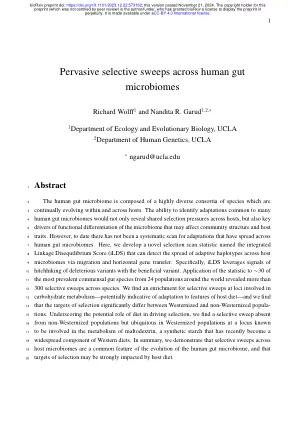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慢性肠道伪obstruction
您可能还需要测试,以了解食物如何通过您的胃,小肠和结肠移动。胃功能通常是通过要求您用放射性同位素吃鸡蛋三明治餐的方法来衡量的,然后跟踪饭菜从胃中排空需要多长时间。该测试称为胃闪烁显像或胃排空测试。小肠运动可以通过跟踪鸡蛋三明治餐中放射性同位素的运动或进行呼吸测试来测量。通常通过跟踪X射线上吞咽塑料标记的运动来测量结肠中的运动。有时需要小肠测压器来帮助诊断,帮助计划提供营养的最佳方法,通过吸入肠道液体识别细菌过度生长或评估预后。例如,测量法提供了有关问题是否影响小肠神经或肌肉的线索。疾病与肠肌肉的缩水弱有关,而如果神经受到影响,则收缩的强度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模式会混乱。您的医生可能建议进行呼吸测试,以查看小肠中是否有太多细菌。很少需要对肠道影响部分的活检来研究显微镜下的神经和肌肉。这需要钥匙孔(腹腔镜)或开放手术。
应用肠道轴的机会
*)电子邮件korespestensi:zahwaarsyazzahra@gmail.com摘要:应用肠道脑轴微生物群的机会,以优化婴儿的神经增长和发育。婴儿的神经发育非常重要,并且在塑造其未来的智力,情感和身体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神经细胞(神经元)从怀孕开始就形成了婴儿的神经网络。肠道菌群与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称为肠脑轴的途径发生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会影响脑功能和人类行为。通过利用肠道脑轴微生物群的概念来找出最大程度地提高婴儿大脑发展的努力。使用PubMed,Cochrane,Embase,Scopus,Google Scholar和Techtbook中的特定关键字在2013 - 2023年使用国际文章的文献审查技术。使用肠道轴轴菌群的概念改善神经发育的努力本质上是为在肠道中建立良好的微生物群平衡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维持和维持孕妇健康菌群的平衡,生育前阴道,提供独家母乳,减少不需要的抗生素的使用,从而提供富含益生菌和益生菌的互补母乳的抗生素,提供刺激,并降低使用药物的使用。肠脑轴微生物群的概念非常适用于通过特别注意产前和产后时期开始的婴儿的神经发育。关键字:微生物群,肠道轴,婴儿,脑发育,神经生长。摘要:应用菌群肠轴的机会来优化婴儿神经的生长和发育。婴儿的神经发展非常重要,并且在未来形成其智力,情感和身体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神经细胞(神经元)在婴儿中形成神经组织。肠道菌群与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称为肠轴的路径发生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会影响脑功能和人类行为。出于这个原因,需要了解可以通过利用肠脑 - 轴微生物群的概念来最大化婴儿大脑发展的努力。使用PubMed,Cochrane,Embase,Scopus,Google Scholar和Techtbook中的某些关键字在2013 - 2023年使用国际文章的文献研究技术。通过使用肠道微生物群的概念来增加神经发育的努力基本上是在肠道中建立良好平衡微生物群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维持和维持健康的微生物孕妇的平衡,阴道分娩,提供独家的母乳喂养,减少不需要的抗生素的使用,提供富含益生菌和
我们对Covid-19对肠道的影响有何了解?
Cruickshank说:“肠道症状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该病毒使用的ACE2受体进入我们的肠道上皮细胞上。我们知道,病毒RNA已从粪便样品中分离出来,尽管这可能不是感染性的。”这一证据是在中国研究的早期在大流行中收集的,3 4在医院患者的粪便样品中发现了SARS-COV-2 RNA更多的研究5证实,病毒RNA的粪便脱落发生在大约一半的COVID患者中,这与GI症状有关。
肠道微生物组和动脉粥样硬化
背景:根据最近的研究,动脉粥样硬化和肠道菌群是相关的。尽管如此,已经发现肠道菌群随着研究而有所不同,其功能仍在争论中,并且这种关系并未被证明是因果关系。因此,我们的研究旨在在不同的分类学水平上识别关键的肠道菌群分类单元(GM分类单元),即门,阶级,秩序,秩序,家庭和属,以研究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任何潜在因果关系。方法:我们采用了来自肠道微生物群的Mibiogen联盟中的汇总数据来进行复杂的两样本Mendelian随机分析(MR)分析。有关动脉粥样硬化统计的相关信息是从Finngen Consortium R8出版物中获取的。评估因果关系,利用的主分析技术是反向方差加权(IVW)方法。补充IVW,采用了其他MR方法,包括加权中位数,MR-EGGER,加权方法和简单模式。敏感性分析涉及Cochrane的Q检验,MR-Egger截距测试,MR-Presso全球测试和剩余分析的应用。结果:最后,在对动脉粥样硬化的211 gm分类单元进行了211 gm分类单元的风险进行MR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了20个名义联系和一个牢固的因果关系。Firmicutes(门ID:1672)(几率(OR)= 0.852(0.763,0.950),p = 0.004)仍然与较低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有关,即使在Bonferroni校正后,也是如此。这项研究可以通过关注肠道菌群来提供有关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目标的新见解。结论:基于发现的数据,确定菲洛姆·菲尼科特斯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降低表现出因果关系。
遍布人类肠道微生物
人类的肠道微生物组由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物种的财团组成,它们在宿主内外不断发展。识别许多3个人类肠道微生物的适应性的能力不仅会揭示宿主之间的共同选择压力,而且还会揭示可能影响社区结构和宿主5个特征的微生物组功能分化的关键驱动力。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的扫描,这些适应已经散布在6个人类肠道微生物中。在这里,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选择扫描统计量,称为Integrated 7链接不平衡评分(ILDS),该评分(ILDS)可以通过迁移和水平基因转移来检测自适应单倍型在宿主8微生物中的扩散。具体来说,ILD利用了具有有益变体的有害变体的9搭便车的信号。将统计数据应用于10个中最普遍的共生肠道物种中的30种,来自世界24个人群,揭示了跨物种的11300多种选择性扫描。我们发现,在12个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基因座中有选择性扫描的富集 - 潜在地表明适应宿主饮食的特征 - 我们发现13位选择的靶标在西方化和非媒介物popula-14 tions之间显着差异。强调了饮食在驾驶选择中的潜在作用,我们发现在非西方人群中没有选择性扫描15,但在西方人种群中无处不在,在一个已知的16个基因座中,与Maltodextrin的代谢有关,这是一种合成淀粉的代谢,最近已成为西方饮食的17种广泛范围。20总而言之,我们证明了跨18个宿主微生物组的选择性扫描是人类肠道微生物组进化的常见特征,并且19个选择靶标可能会受到宿主饮食的强烈影响。
Axivite-将肠道与体重管理和...
几个因素在肠道健康及其与肠道___轴的联系中起作用。的例子将是有足够的好或有益的微生物,有助于抑制或消除有害的微生物,减少肠道炎症,并提高肠壁的强度(肠渗透性)。最近对腋窝的研究表明,它影响了两个主要区域,这些区域会通过抑制群体感应和肠渗透性来影响减少有害微生物的影响。对于那些不熟悉群体感应的人,它最好将其视为细菌物种中的交流手段。相反,细菌组或细菌与宿主之间可能发生竞争性或合作信号传导。法定感应在致病细菌和酵母(例如白色念珠菌)的毒力中起着重要作用。i抑制有害微生物之间的通信的能力在微生物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肠渗透性不一定是不好的,除非细胞之间的连接(紧密连接)变得太大,从而导致肠道漏水。 小肠和大肠的衬里被设计为使营养,水等进入血流,并使废物和其他毒素流入消化道以消除。 当这些连接将细胞固定在一起时,它们会变得虚弱,使得不属于血液的颗粒。 这可能会引发肠道,皮肤,免疫系统,疲劳,体重增加,关节不适等其他更严重的健康问题。i抑制有害微生物之间的通信的能力在微生物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肠渗透性不一定是不好的,除非细胞之间的连接(紧密连接)变得太大,从而导致肠道漏水。小肠和大肠的衬里被设计为使营养,水等进入血流,并使废物和其他毒素流入消化道以消除。当这些连接将细胞固定在一起时,它们会变得虚弱,使得不属于血液的颗粒。这可能会引发肠道,皮肤,免疫系统,疲劳,体重增加,关节不适等其他更严重的健康问题。ii研究观察到了腋窝抑制群体感应和降低蛋白质齐原蛋白的能力。上面描述了抑制群体感应及其对肠道健康的积极影响的影响。较高的Zonulin水平与肠道通透性的增加有关。 通过降低Zonulin水平,我们可以看到肠道健康的好处。较高的Zonulin水平与肠道通透性的增加有关。通过降低Zonulin水平,我们可以看到肠道健康的好处。
微生物-肠道-眼睛轴
摘要 人体的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微生物群,眼睛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组分器官也不例外。由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对眼部微生物组 (OM) 的详细研究直到 2010 年才作为眼部微生物组项目的一部分开始,当时研究方法的进步使得获得详细数据成为可能,尽管之前一直存在争议,即微生物是否能够附着在眼部表面——具有抗菌特性的泪膜层上。眼球表面的结构由角膜、结膜、泪腺及泪膜、睑板腺以及睑板膜组成;它们共同对抗刺激物、过敏原和病原体。眼部微生物群的稳态对于维持视觉器官的健康至关重要。大多数微生物位于角膜和结膜上,包括16S rRNA测序在内的现代研究方法已经能够确定眼表微生物群的“核心”,并确定最常见的类型:葡萄球菌、棒状杆菌、丙酸杆菌和链球菌,尽管“核心”的具体组成仍然存在争议。 MB的组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年龄、佩戴隐形眼镜、服用眼科药物和抗生素。与许多其他器官一样,眼表面的微生物群受到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这种联系被称为“微生物-肠道-眼睛”轴。在肠眼轴内,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吲哚、多胺和其他对免疫系统和视网膜健康有益的物质。菌群失调会导致体内平衡被破坏,而炎症反应的加剧会导致视神经受损和眼部疾病的进展。一些眼科疾病,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脉络膜新生血管、葡萄膜炎、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干燥综合征和干眼症,可能与肠道微生物组成的变化有关。使用各种方法纠正肠道菌群失调可以降低患眼疾的风险,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发现沿“微生物-肠道-眼”轴治疗眼科疾病的新方法。
肠道轴是否涉及?
1体育科学学院体育与健康大学研究所(IMUDS)的体育与体育系,格拉纳达大学,18071年,西班牙格拉纳达; sanchez.javier.andre@gmail.com 2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德烈斯·贝洛大学,维尼亚·贝洛大学,维纳尔·德尔8370134,智利3 AFYSE小组,体育活动研究和学校健康研究,教育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学院,de las am am am am am anaméricas,siniago 7500975,Chile,Chile,Chile,Chile,Chile; jorge.olivares.ar@gmail.com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II,校园校园,de Cartuja s/n,格拉纳达大学,格拉纳达大学,18071年,西班牙格拉纳达5.渥太华安大略研究所,加拿大K1H 8L1 *通信:patricio.solis.u@gmail.com(P.S.-U. ); jrplaza@ugr.es(J.P.-D。);电话。 : +34-958241599(J.P.-D。)1体育科学学院体育与健康大学研究所(IMUDS)的体育与体育系,格拉纳达大学,18071年,西班牙格拉纳达; sanchez.javier.andre@gmail.com 2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德烈斯·贝洛大学,维尼亚·贝洛大学,维纳尔·德尔8370134,智利3 AFYSE小组,体育活动研究和学校健康研究,教育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学院,de las am am am am am anaméricas,siniago 7500975,Chile,Chile,Chile,Chile,Chile; jorge.olivares.ar@gmail.com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II,校园校园,de Cartuja s/n,格拉纳达大学,格拉纳达大学,18071年,西班牙格拉纳达5.渥太华安大略研究所,加拿大K1H 8L1 *通信:patricio.solis.u@gmail.com(P.S.-U.); jrplaza@ugr.es(J.P.-D。);电话。: +34-958241599(J.P.-D。)
与您的肠道和澳大利亚鳄梨一起去
1。理发师TM等。饮食对微生物群 - 脑轴的影响。int J Mol Sci。2021; 22(7):3502。2。Martin CR等。 脑肠球菌轴。 细胞mol胃肠道乙醇。 2018; 6(2):133-148 3。 健康直接。 良好的心理健康。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good-mental-health 4。 Gomaa EZ。 健康与疾病中的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微生物组:评论。 Antonie van Leeuwenhoek。 2020; 113(12):2019-2040 5。 Makki K等。 饮食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群在宿主健康和疾病中的影响。 细胞宿主微生物。 2018; 23(6):705-715 6。 园艺创新分析,2021 7。 li bw等。 J食品comp and Anal 2002; 15:715-723 8。 Fraga CG等。 多酚和其他生物活性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食物功能。 2019年2月20日; 10(2):514-528。 9。 Redondo-Useros N等。 微生物群和生活方式:特别关注饮食。 营养。 2020; 12(6):177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53459/访问21.12.21Martin CR等。脑肠球菌轴。细胞mol胃肠道乙醇。2018; 6(2):133-148 3。健康直接。良好的心理健康。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good-mental-health 4。Gomaa EZ。 健康与疾病中的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微生物组:评论。 Antonie van Leeuwenhoek。 2020; 113(12):2019-2040 5。 Makki K等。 饮食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群在宿主健康和疾病中的影响。 细胞宿主微生物。 2018; 23(6):705-715 6。 园艺创新分析,2021 7。 li bw等。 J食品comp and Anal 2002; 15:715-723 8。 Fraga CG等。 多酚和其他生物活性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食物功能。 2019年2月20日; 10(2):514-528。 9。 Redondo-Useros N等。 微生物群和生活方式:特别关注饮食。 营养。 2020; 12(6):177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53459/访问21.12.21Gomaa EZ。健康与疾病中的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微生物组:评论。Antonie van Leeuwenhoek。2020; 113(12):2019-2040 5。Makki K等。饮食纤维对肠道微生物群在宿主健康和疾病中的影响。细胞宿主微生物。 2018; 23(6):705-715 6。 园艺创新分析,2021 7。 li bw等。 J食品comp and Anal 2002; 15:715-723 8。 Fraga CG等。 多酚和其他生物活性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食物功能。 2019年2月20日; 10(2):514-528。 9。 Redondo-Useros N等。 微生物群和生活方式:特别关注饮食。 营养。 2020; 12(6):177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53459/访问21.12.21细胞宿主微生物。2018; 23(6):705-715 6。园艺创新分析,2021 7。li bw等。J食品comp and Anal 2002; 15:715-723 8。Fraga CG等。 多酚和其他生物活性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食物功能。 2019年2月20日; 10(2):514-528。 9。 Redondo-Useros N等。 微生物群和生活方式:特别关注饮食。 营养。 2020; 12(6):177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53459/访问21.12.21Fraga CG等。多酚和其他生物活性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食物功能。2019年2月20日; 10(2):514-528。9。Redondo-Useros N等。微生物群和生活方式:特别关注饮食。营养。2020; 12(6):177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53459/访问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