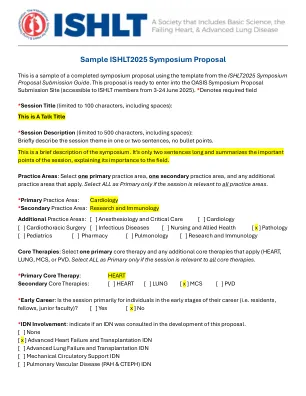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Messenger - Squarespace
长老波菲里曾谈到青少年及其在教会生活中的挣扎:“男孩和女孩有时会来找我。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犯下了肉体的各种罪孽,但我爱他们。”长老并没有为年轻人的行为辩解,他将这些行为描述为肉体的罪孽,但同时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为他们而死”的宝贵灵魂。他的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逐渐治愈了他们对肉体的崇拜。保守的清教徒误解了长老的这种教父态度,他们为此感到悲痛,而一些不负责任的进步人士则为此而欢欣鼓舞,原因相同:据说长老“容忍”肉体的罪孽。他们不明白,罪恶不能通过对罪人的不宽容谴责或对堕落的罪恶律法主义来对抗。长老通过爱罪人并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堕落的责任以及在基督里的可能性来有效地对抗罪恶
信使-Squarespace
波菲里长老曾经谈到青少年及其在教会生活中的挣扎:“男孩和女孩有时会来找我。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犯下了肉体的各种罪孽,但我爱他们。”长老并没有为年轻人的行为辩护,他将这些行为描述为肉体的罪孽,但同时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为他们而死”的宝贵灵魂。他的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逐渐治愈了他们对肉体的崇拜。长老的这种教父态度被保守的清教徒误解了,他们为此感到悲痛,而一些不负责任的进步人士则为之欢欣鼓舞,原因相同:据说长老“容忍”了肉体的罪孽。他们不明白,不能通过对罪人的不宽容谴责来对抗罪恶,也不能通过对堕落的罪恶律法主义来对抗罪恶。长老通过爱罪人并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堕落的责任,以及他们在基督里可能摆脱罪恶,有效地对抗了罪恶。
信使-Squarespace
波菲里长老曾经谈到青少年及其在教会生活中的挣扎:“男孩和女孩有时会来找我。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犯下了肉体的各种罪孽,但我爱他们。”长老并没有为年轻人的行为辩护,他将这些行为描述为肉体的罪孽,但同时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为他们而死”的宝贵灵魂。他的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逐渐治愈了他们对肉体的崇拜。长老的这种教父态度被保守的清教徒误解了,他们为此感到悲痛,而一些不负责任的进步人士则为之欢欣鼓舞,原因相同:据说长老“容忍”了肉体的罪孽。他们不明白,不能通过对罪人的不宽容谴责来对抗罪恶,也不能通过对堕落的罪恶律法主义来对抗罪恶。长老通过爱罪人并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堕落的责任,以及他们在基督里可能摆脱罪恶,有效地对抗了罪恶。
信使-Squarespace
波菲里长老曾经谈到青少年及其在教会生活中的挣扎:“男孩和女孩有时会来找我。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犯下了肉体的各种罪孽,但我爱他们。”长老并没有为年轻人的行为辩护,他将这些行为描述为肉体的罪孽,但同时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为他们而死”的宝贵灵魂。他的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逐渐治愈了他们对肉体的崇拜。长老的这种教父态度被保守的清教徒误解了,他们为此感到悲痛,而一些不负责任的进步人士则为之欢欣鼓舞,原因相同:据说长老“容忍”了肉体的罪孽。他们不明白,不能通过对罪人的不宽容谴责来对抗罪恶,也不能通过对堕落的罪恶律法主义来对抗罪恶。长老通过爱罪人并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堕落的责任,以及他们在基督里可能摆脱罪恶,有效地对抗了罪恶。
信使-Squarespace
波菲里长老曾经谈到青少年及其在教会生活中的挣扎:“男孩和女孩有时会来找我。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犯下了肉体的各种罪孽,但我爱他们。”长老并没有为年轻人的行为辩护,他将这些行为描述为肉体的罪孽,但同时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为他们而死”的宝贵灵魂。他的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逐渐治愈了他们对肉体的崇拜。长老的这种教父态度被保守的清教徒误解了,他们为此感到悲痛,而一些不负责任的进步人士则为之欢欣鼓舞,原因相同:据说长老“容忍”了肉体的罪孽。他们不明白,不能通过对罪人的不宽容谴责来对抗罪恶,也不能通过对堕落的罪恶律法主义来对抗罪恶。长老通过爱罪人并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堕落的责任,以及他们在基督里可能摆脱罪恶,有效地对抗了罪恶。
安全空间,或脆弱性的宪法化
蔑视脆弱性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保守派嘲笑多元化倡议、政府援助、反歧视政策、#MeToo 运动、工人保护、全民医疗保健、家庭假、学生债务减免和其他进步概念,认为这些是脆弱者和依赖者的痴迷。对脆弱性的蔑视在校园言论自由危机叙事中得到了生动展示,该叙事哀叹“雪花”学生的崛起,他们要求远离冲突和不适的安全空间。1 根据这种叙事的支持者,雪花既危险又荒谬,他们的恶劣影响超出了大学校园。保守派批评人士警告说,“反法西斯”和其他左翼极端分子试图在各地压制和解除异议,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2 危险的雪花叙事有其道理,但并非其倡导者所认为的真理。确实,那些被教导要害怕他们不理解的想法或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的易受影响的个人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基于他们的恐惧形成群体认同时,危险尤其严重。当这样的团体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其身份时,它实际上就变成了邪教。但抗议有争议的演讲者或要求内容警告的大学生并不是邪教。要求对性虐待、种族主义政策或经济不公负责的进步人士也不是邪教。如果有一群人真正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整个世界变成他们的个人安全空间,那就是那些自称第二修正案活动家的人,他们太害怕了
进步年鉴2005
在本第六版的FEPS进步年鉴中,我们回顾了决定性的一年的选举,并在欧盟的政治算术与生活记忆中的任何事物不同时,又回到了一个周期。去年6月,当选了新的欧洲议会,到今年年底,新的欧盟领导层就揭幕了。同时,美国和英国的选举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右边是一个;另一个向左。不仅公民,而且议员们对这些变化在特定政策领域的含义充满了疑问:经济学,气候和移民,仅举几例。在2024年,欧洲的政治地图变得更加不平衡。因此,FEP认为,对年度进步人士的决定应该突出一些近年来我们政治家庭非常困难的事情:改善社会民主党在欧盟东部统计上的地位。这也反映了欧盟在东欧有一个地缘政治难题的事实。最重要的问题是,鲁斯索 - 乌克兰战争的进程将在2025年发生变化,以及三年后是否会停止,停滞,甚至某种交易。,但这也是我们如何从这种侵略性和破坏经历中得出结论来为自己以及为更广阔的世界建立安全性的问题。欧盟是否可以在来年进行测试。当创造新的跨性能动量以通过放松管制和金融化来提高竞争力时,我们的社会模型的韧性将再次承受压力。工会已经开始动员削减,我们可能会再次朝着一轮社会对抗进行,需要勇敢。然而,这个问题不仅要抵抗,而且要维护一种进步的替代方案:从长远来看,在短期内迈向繁荣和可持续性的议程,同时解决短期内顽固的生活成本危机,增强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创新领域的投资,并在自动企业中辅助自动化行业,例如自动化行业,例如自动化行业,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竞争。2025将是一年,必须为欧盟政策的弹性做更多的工作,而更多的是欧盟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监管中进一步的能力。然而,建立这样的计划(着重于社会维度)不仅需要反对最右翼,而且还需要对胆度的中右力量进行批判性评估。无论是关于中东还是其他地区,社会民主党人都可以再次成为和平的领导声音,即使有时需要在战争时期延长团结的尽可能多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