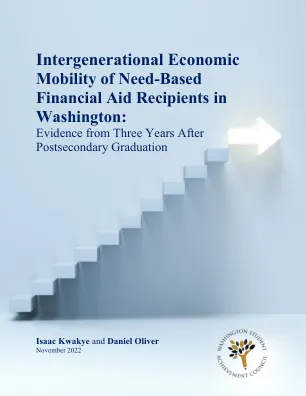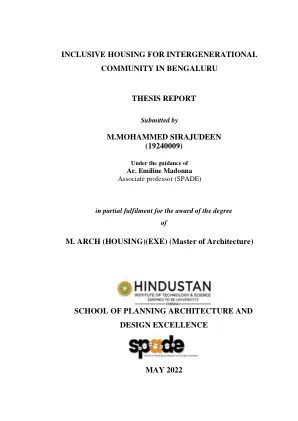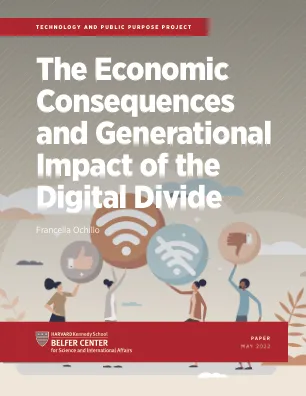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教育程度和代际流动性
在基于全基因组AS-ASIOT研究(GWASS)的表型的最新研究中,已经确定了许多标记。GWAS是对跨整个基因组的常见遗传变异的研究(通常是1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或更多),以确定是否与性状相关,以确定是否与性状相关。在常规GWAS阈值1处获得显着性的标记仍然有限,并且它们共同解释了表型变异性的有限部分。尽管如此,可以用大量的表型变异来解释一组较大的遗传标记,其中包括GWAS标准不明显的变体。一种考虑标记中可用信息的方法,包括那些明显低于GWAS阈值的信息,是计算多基因分数(PGS)。a pgs是一个特定的分数,被视为选定集中标记的值的总和,每个值都由系数加权,这些值已在非独立培训样本上分别估计(Dudbridge 2013)。我们在这里的分析是基于Lee等人报告的大量教育程度。(2018;另请参见Rietveld等人2013和Okbay等。2016)。对现代GWAS时代的教育成就分析的启发性讨论是Cesarini和Visscher(2017)。理论框架。- 我们以完全指定的父母投资在儿童教育的指定模型中进行了调查。(2017)。一些经典的遗产建立了这一传统的是Becker和Tomes(1979,1986)和Loury(1981)。早期模型的重要发展都在Solon(1992,2004),Mulligan(1997,1999),Black和Devereux(2011)和Black等人中。我们的模型在两个方面与现有的模型不同,这两者都引入了,因为我们需要考虑有关基因型及其传输的信息。首先,我们明确介绍了一个事实,即儿童是涉及父亲和母亲的联合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在模型中包含一个纪念理论(类似于Aiyagari,Greenwood和Guner 2000和Greenwood,
代际贫困与公共福利的交集
I. 概述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它仍然延续着将低质量的生活从穷人的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趋势——从而加剧并延续了可预见的未来贫困。代际贫困,这个概念恰如其分地命名,对有色人种的影响尤为严重。虽然贫困有很多根源,但本文专门讨论了导致代际贫困的两项公共福利——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收入。这些公共“福利”遍布全国,同时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II.什么是代际贫困?“贫困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把它戴在脸上,背在背上,像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而且它很重。” 1 - 丹尼斯·库辛尼奇 贫困影响着数百万美国人,但对有色人种的影响尤为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只有 8.7% 的白人是穷人,而黑人美国人的贫困率为 21.2%,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为 18.3%。2 有色人种意味着你“在美国经历贫困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多”。 3 在评估时,这种差异得到了进一步说明
中大西洋地区经济的代际流动
Ward 2020, 2021)。在长期代际流动性的国际比较中,有两种模式显而易见(Perez 2019)。首先,在 1900 年之前,美洲的“新世界”经济体表现出儿子和父亲之间的流动性高于欧洲的“旧世界”经济体。其次,在历史案例中,人口快速增长和获得丰富土地资源的机会已被确定为流动性差异的关键决定因素,而不是教育和不平等。尽管加拿大是土地丰富、不断扩张的定居者经济的典型例子,但人们对 1950 年代之前的流动模式知之甚少。加拿大与美国和其他“新世界”定居者经济体有相似之处。加拿大西部的扩张为定居提供了充足的新土地,有机会进入农业或迁往新的城市中心。相对的劳动力稀缺吸引了内部移民到西部边境寻找新的机会,并吸引了来自欧洲和加拿大农村的移民到工业和服务业活动迅速扩张的城市地区。然而,有关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强调了加拿大案例的僵化性,特别是相对于美国而言。Porter (1965) 强调了种族、宗教和阶级是进入加拿大精英职位的障碍。流动的一个潜在障碍是英语加拿大人和法语加拿大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对二十世纪后期职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加拿大经验的这一方面,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按语言细分,法语加拿大人的代际职业流动率较低 (McRoberts 1985)。这种障碍会抑制加拿大的整体流动性,也会表现为魁北克 (以法语为主) 和该国其他地区 (以英语为主) 之间的地区差异。十九世纪后期,加拿大各地区在教育政策和公立学校提供方面也存在差异;安大略省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行义务教育,而魁北克省和加拿大东部沿海省份的部分地区几十年来都没有效仿。尽管最近的研究发现,如今加拿大的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美国(Corak 和 Heinz 1999;Chetty 2016),但由于缺乏数据,人们对加拿大人口历史流动性的差异程度、加拿大代际流动性的长期路径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情况知之甚少。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加拿大人口普查中新链接的记录来提供
代际经济
执行摘要 高等教育学位被广泛推崇为出生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的代际经济均衡器。然而,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表明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来自所有种族、民族和语言背景的人是否都能平等地受益。我们通过报告华盛顿居民的经济流动性模式来提供难得的视角,这些居民获得了基于需求的经济援助,并从华盛顿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毕业,获得副学士或学士学位。为了提供见解,我们将华盛顿失业保险计划的工资记录与报告父母家庭收入的经济援助记录进行匹配。数据匹配使我们能够直接将成年子女在中学毕业后第三年的年薪与其父母的家庭收入进行比较。虽然我们的分析仅限于了解基于需求的援助接受者的流动性模式,但这个群体非常广泛。华盛顿州的经济援助计划非常慷慨,为许多家庭提供了支持。例如,以 2021 年的美元计算,我们数据样本中父母家庭收入的第 25、50 和 75 百分位数分别约为 35,000 美元、63,000 美元和 100,000 美元。总体而言,我们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家庭收入低于 35,000 美元的家庭中出生的高等毕业生是否与出生在收入高得多的家庭中的毕业生拥有相似的挣钱机会。我们的描述性分析的结果令人鼓舞,表明基于需求的援助和高等学位为华盛顿人提供了一条通往经济流动的道路。分析的主要发现是:• 出生在经济最弱势家庭(样本的第 25 百分位数以下)的所有人口统计亚群的孩子在毕业后第三年所赚的工资高于其父母的家庭收入。 • 来自经济最贫困家庭的儿童,无论获得副学士学位还是学士学位,其工资都比其父母的家庭收入高。
代际的包容性住房...
Dean HOD (SPAD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NTERNAL EXAMINER EXTERNAL EXAMINER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ign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 Designation: -----------------------------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Viva voce:
数字鸿沟的经济后果和代际影响
在研究收入中位数最高和最低的十个州时,数据显示,面临网络连接困难的人口非常相似。贫困往往是居住在数字基础设施附近但无力维持全年宽带订阅的家庭的根本问题。大约 50% 居住在部落土地上的原住民仍然没有基本的宽带接入或在家中上网的计算设备。2 高收入和低收入州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家庭在宽带采用率方面一直落后于白人家庭,这一统计数据更糟糕的是,他们因疫情造成的财务压力而取消家庭宽带服务的可能性是白人家庭的两倍。3
代际经济转型计划
当人们谈论新奥尔良的经济时,他们可能会想到我们的主要产业、世界级的活动或自然资源。但当我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的经济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宝贵和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产:我们的人民——这个计划就是为他们而制定的。COVID-19 疫情和最近的风暴夺走了我们人民的生命和生计,并暴露了我们当地经济的弱点。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现在知道的“必不可少”的工人被视为可有可无。使我们的社区独一无二并雇用我们大多数工人的小企业没有获得与获得充足联邦支持的大公司相同的资源。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个有针对性的战略,强调投资于我们的人民,不仅要生存,还要繁荣,并确保我们有更多的工作、更好的工作。
多年代际和湍流变化之间的能量转移
摘要:解释北大西洋海面温度数十年变化的建议机制之一是,由于时间平均环流的大规模斜压不稳定性,自发形成了一种大规模低频内部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已在浮力方差预算方面得到广泛研究,但其能量特性仍然知之甚少。在这里,我们执行了这种内部模式的完整机械能预算,包括可用势能 (APE) 和动能 (KE),并将预算分解为三个频带:平均、与大规模模式相关的低频 (LF) 和与中尺度涡旋湍流相关的高频 (HF)。这种分解使我们能够诊断不同储存器之间的能量通量并了解源和汇。由于该模式的规模很大,它的大部分能量都包含在 APE 中。在我们的配置中,LF APE 的唯一来源是从平均 APE 到 LF APE 的转移,这归因于大规模斜压不稳定性。反过来,LF APE 的汇点是参数化的扩散、流向 HF APE 的通量,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流向 LF KE 的通量。额外风应力分量的存在削弱了多年代振荡并改变了不同能量库之间的能量通量。在所有实验中,与其他涉及 APE 的能量源相比,KE 转移似乎对多年代模式的影响很小。这些结果突出了完整 APE – KE 预算的实用性。
经济制裁的代际影响
∗ 本文是我博士论文一章的修订和扩展版本,该论文于 2019 年 6 月提交给卡尔加里大学,之前以“家庭收入和儿童教育: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的证据”为题发表。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 Atsuko Tanaka 和 Alexander Whalley 在本研究的规划和发展过程中提供的指导和宝贵建议。我要感谢 Joseph Altonji、Pamela Campa、Yu (Sonja) Chen、Eugene Choo、David Eil、Kelly Foley、Jean-William Laliberté、Karen Macours、Christine Neill、Stefan Staubli、Leslie Stratton、Scott Taylor 和 Trevor Tombe 提供的有益反馈。我还受益于 2018 年加拿大经济学会、2021 年 CSWEP CeMENT 研讨会、2021 年加拿大经济学会、2021 年国际教育应用经济学研讨会、汉堡大学、蒙特爱立森大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于默奥大学、卡尔加里大学、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新不伦瑞克大学、里贾纳大学和萨斯喀彻温大学的会议参与者的反馈。其余所有错误均由我承担。† 里贾纳大学经济学系,电子邮件:Safoura.Moeeni@uregina.ca 1 经济制裁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对目标国家实施的贸易和金融限制。制裁旨在向目标国家施压,迫使其改变违法政策,和/或削弱其治理能力(Askari 等人(2001 年))。 1966 年,联合国首次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多国制裁。自此以后,安理会已对南非、前南斯拉夫、海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伊拉克、伊朗等实施了 25 项制裁制度。目前有 14 项制裁正在实施中,重点是冲突、核计划和恐怖主义。2 2006 年,家庭教育支出占 GDP 的 5%,政府教育支出占 GDP 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