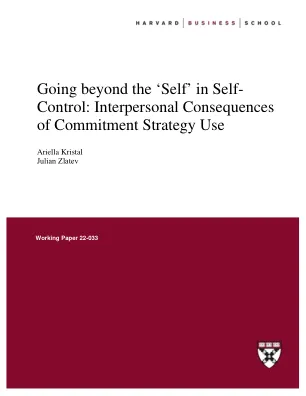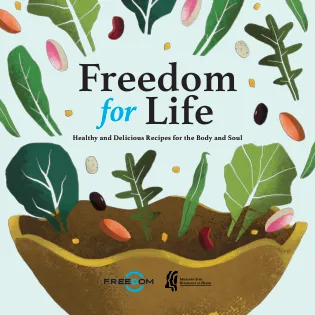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承诺策略使用的人际后果
2 在本研究中,我们不一定对各种自我控制策略的客观努力程度持立场。认知努力的构造最近受到批评,被认为不精确且难以定义(Thomson & Oppenheimer,2022 年)。相反,我们关注的是人们对自我控制策略的努力程度的看法,以及这对印象形成的影响。
特刊
跨越社会感知的多个领域(包括社会分类,情感感知,印象形成和心理化) - 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数据的多元化模式分析(MVPA)允许对社交信息如何处理和在大脑中进行处理和表示。与其他神经影像领域一样,对社会感知的神经科学研究最初依赖于从单变量fMRI分析中得出的广泛结构 - 功能性关联,以绘制涉及这些过程中涉及的神经区域。在这篇综述中,我们追踪了使用MVPA的社会神经科学研究在这些神经解剖学协会上的构建方式,以更好地表征不同大脑区域的计算相关性,并讨论MVPA如何允许对心理模型与社会信息神经表示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明确测试。我们还描述了多元fMRI数据的方法论方法的当前和未来进展及其对社会感知神经科学的理论价值。
承诺策略的人际后果
承诺策略是个人可以用来克服自我控制问题的有效机制。在七项研究(和两项补充研究)中,我们探讨了承诺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对人际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研究 1 中,我们使用激励信任游戏证明,个人对选择使用承诺策略的人的信任度低于对选择使用意志力实现目标的人的信任度。研究 2 表明,这种关系适用于四个领域,尤其是基于诚信的信任。研究 3 提供的证据表明,选择使用策略而不是策略使用本身会导致这种诚信惩罚。在研究 4 – 5b 中,我们证明这种影响至少部分是由人们从策略选择中推断过去的表现这一事实所驱动的。最后,研究 6 提供的证据表明,人们在私下比在公开场合更多地选择承诺策略,这与人们预期承诺策略选择的负面后果的观点一致。因此,我们确定了意志力在印象形成中的作用是积极信号,以及在面对诱惑时选择依赖外部助手的负面人际后果。
生命 - 密西西比州卫生部
SadéMeeks,MS,RD是来自MS Jackson的作家,食品活动家和注册营养师。米克斯(Meeks)拥有密西西比大学的烹饪艺术学士学位,并拥有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营养科学硕士学位。Meeks自行出版了一本食品素养食谱,她的营养专业知识在读者的Digest,MSN和Yahoo News中得到了介绍。她是Grits Inc(南部越来越弹性)和纽约购买学院的兼职教授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对Meeks个人和专业角度的最大影响力来自她的祖母Rosemary(Rosemary)。sadé回想起成为注册营养师后不久与祖母坐在桌子上。在一碗砂砾上,罗斯奶奶回想起她家庭花园的回忆。“我什至在那里有花生,”罗斯奶奶说。这个故事与米克斯(Meeks)在一起,因为它与关于黑人饮食文化的消极故事和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Meeks知道她的任务不仅仅是准备好食物。这是关于改变叙事,并以一种赋予和变革性的方式帮助人们与食物建立联系,但仍然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真实。食物只是使自然讲故事的米克斯能够分享她的目的的另一种工具。她希望这些食谱将成为您故事的一部分,以某种方式将您与食物,家庭和文化联系起来。
可重现的WISDM:使用标准化的开放数据
我们对他人的印象的能力取决于在不确定性下提供的信息,因此我们使用启发式法来做出判断和决定(Tversky and Kahneman,1974)。这种印象形成与刻板印象有关:例如,图像可以而且经常体现和永久化性别刻板印象(Coltrane and Adams,1997; Len-Ríos等,2005; Rodgers and Thorson,2000)。男女的视觉代表塑造了我们对性别角色的心理表征,并可以加强或稳定它们 - 数字和模拟媒体,例如报纸,杂志,电视和社交媒体,可以在刻画中归因于严格的作用,在刻画中归因于妇女的性行为,并在男性中比男性更大(Courtney and Lockere and Lockeretz and lockeretz and Milers and Mirers;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Biocca,1992; Zotos and Tsichla,2014年)。,但在男人和女人的描绘中,即使是简单的风格差异也可能已经巧妙地延续了性别偏见(Archer等,1983; Blumberg,2008; Grau和Zotos,2016)。例如,在线媒体中,女性政治家的代表性影响了选民对她们感知的能力和讨人喜欢的影响(Bligh等,2012),面部突出的变化导致女性对智力的评价较低(Archer等,1983)。自动处理大量潜在偏见的信息一直是近年来在交流研究中特别感兴趣的话题(Goldman,2008; Noble,2018; O'Neil,2017)。这些决定的输出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现实(Just and Latzer,2017; Noble,2018)及其对公民和机构的影响数字文化和新媒体研究正在将数据移至其学术叙事的中心;具体而言,媒体平台(例如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的数据现在被视为文化研究对象(Schäfer和van es,2017年)。在这个新范式的背景下,算法的转换和问责制的问题通常是关于平台利用的辩论的最前沿,尽管通常由于其“黑匣子”依赖性,异质性和嵌入性而无法理解,因此在更广阔的系统中(Crawford,2016年Crawford,2016; Kitchin; Kitchin,2017; kitchin; kitchin,2017; reshle; kitchin; kitchin; kitchin; kitchin; kitchin; 2017; reshle;搜索引擎提供商,例如Google或Bing,由于其作为守门人的角色而受到了学术审查:他们通过过滤和排名在网上可用的信息来源来决定内容的相关性(Laidlaw,2010; Schulz等,2005; Wallace,2018)。
代表性和面部主义:图像搜索中的性别偏见
我们对他人的印象的能力取决于在不确定性下提供的信息,因此我们使用启发式法来做出判断和决定(Tversky and Kahneman,1974)。这种印象形成与刻板印象有关:例如,图像可以而且经常体现和永久化性别刻板印象(Coltrane and Adams,1997; Len-Ríos等,2005; Rodgers and Thorson,2000)。男女的视觉代表塑造了我们对性别角色的心理表征,并可以加强或稳定它们 - 数字和模拟媒体,例如报纸,杂志,电视和社交媒体,可以在刻画中归因于严格的作用,在刻画中归因于妇女的性行为,并在男性中比男性更大(Courtney and Lockere and Lockeretz and lockeretz and Milers and Mirers;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Biocca,1992; Zotos and Tsichla,2014年)。,但在男人和女人的描绘中,即使是简单的风格差异也可能已经巧妙地延续了性别偏见(Archer等,1983; Blumberg,2008; Grau和Zotos,2016)。例如,在线媒体中,女性政治家的代表性影响了选民对她们感知的能力和讨人喜欢的影响(Bligh等,2012),面部突出的变化导致女性对智力的评价较低(Archer等,1983)。自动处理大量潜在偏见的信息一直是近年来在交流研究中特别感兴趣的话题(Goldman,2008; Noble,2018; O'Neil,2017)。这些决定的输出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现实(Just and Latzer,2017; Noble,2018)及其对公民和机构的影响数字文化和新媒体研究正在将数据移至其学术叙事的中心;具体而言,媒体平台(例如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的数据现在被视为文化研究对象(Schäfer和van es,2017年)。在这个新范式的背景下,算法的转换和问责制的问题通常是关于平台利用的辩论的最前沿,尽管通常由于其“黑匣子”依赖性,异质性和嵌入性而无法理解,因此在更广阔的系统中(Crawford,2016年Crawford,2016; Kitchin; Kitchin,2017; kitchin; kitchin,2017; reshle; kitchin; kitchin; kitchin; kitchin; kitchin; 2017; reshle;搜索引擎提供商,例如Google或Bing,由于其作为守门人的角色而受到了学术审查:他们通过过滤和排名在网上可用的信息来源来决定内容的相关性(Laidlaw,2010; Schulz等,2005; Wallace,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