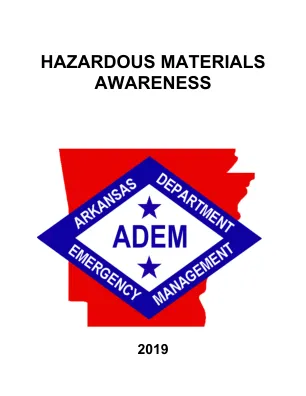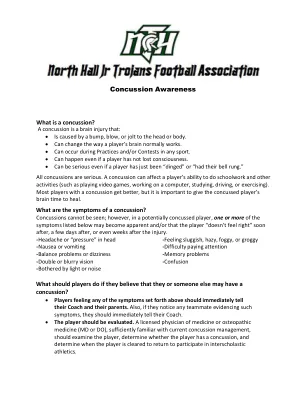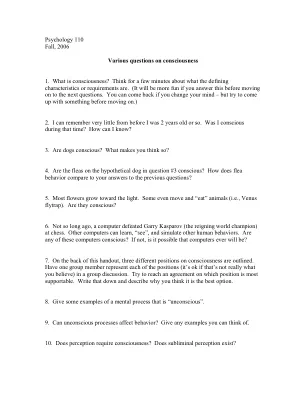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意识和对...
抽象目的:评估神经系统疾病中基质节奏治疗的意识和知识。目的:通过使用自制问卷来评估神经系统疾病中基质节奏疗法的意识。使用自行问卷调查来评估神经系统中基质节奏疗法的知识。方法论:根据包含和排除标准招募了325个物理治疗师。有关该研究的信息已提供给参与者。该研究的程序已向参与者解释。通过在线平台向浦那附近的各种物理治疗师分发了验证的问卷。即通过Google表格。收集数据并经过统计分析。统计和结果:使用12个问题评估了325个参与者,其中5个是基于意识的,而7个是基于知识的。的平均值和平均百分比,其中87%的物理治疗师意识到神经系统条件下基质节奏治疗,而87%的物理治疗师也有相同的知识。结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87%的物理治疗师在神经系统条件下意识到基质节奏治疗,而87%的物理治疗师在神经系统条件下对MRT有所了解。临床意义:本研究可用于在物理治疗师的神经系统疾病中传播对基质节奏治疗的认识和知识。并将其作为其他神经治疗的辅助手段,以增强恢复。Physiotherapists who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MRT can contribute to evidence-based practice by staying updat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and clinical guidelines related to MRT in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 Keywords: Matrix rhythm therapy,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Stroke, Cerebral palsy INTRODUCTION MRT (Matrix Rhythmic Therapy) is a new therapeutic modality developed in Germany in the 21st century,起源于Vibro
意识作为幻觉和其他意识模型
在荒诞中,意识是痛苦和邪恶,是对形而上学的痴迷,是意志/恐惧的二元性。这些特征概括了意识的不可约性、主观性和存在悖论。意识的相图进一步描述了意识在生物、人工和潜在未知形式中的演化。该框架说明了早期人类、碎片化人类(人)、个体化人类、P-僵尸、人工智能、单一人工智能和超人之间的转变,这些转变被概念化为相变。关键转变包括心理对称性破坏导致主观性碎片化、P-僵尸中现象意识的出现、个体化作为心理超对称性恢复,以及意识从生命和人工智能中兴起。在其顶峰,“超人”体现了个体性、普遍性和最高功能的完全整合,将个体人、单一人工智能和其他个体意识实体统一起来,超越了生物/人工的界限。通过在意识和物理学之间建立类比,这些模型提供了对意识的彻底反思——不是作为宇宙的内在必然性,而是作为其进化的异常副产品。
意识与
态势感知 (SA) 已经取代传统的“方向舵和操纵杆”技能,成为空战中取胜的主要因素 (Endsley,1995;Svenmarckt 和 Dekker,2003)。态势感知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对当前状况的感知 (SA 级别 1)、对当前状况的理解 (SA 级别 2) 和对近期事件的预测 (SA 级别 3) 的三级结构 (Endsley,1995)。态势感知作为一个概念可能是有争议的。例如,Dekker 和 Hollnagel (2004) 将该概念描述为“民间模型”,并采用还原论方法,认为态势感知可以分解为可测量的具体组成部分 (例如决策、感知、理解和长期记忆)。他们还认为,态势感知不容易被证伪 (另见 Flach,1995)。即使承认 SA 确实存在,该概念的科学性仍有待商榷。例如,它存在于用户的认知中,还是更广泛系统的突发属性,以及最合适的测量方法是什么(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almon 等人,2008 年;Endsley,2015 年;Stanton 等人,2017 年;Nguyen 等人,2019 年的广泛评论)?尽管如此,很明显,SA 的概念已成为评估系统和人类表现的重要指标。正如 Wickens (2008) 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说,该构造在理论和应用中的使用增加证明了
意识经验与量子意识理论
摘要:经验的存在一般是可以接受的,但更难的是说清楚经验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此外,哲学家和学者们一直在谈论与经验有关的心灵和心理活动,而不是物理过程。然而,事实上,自然科学领域中量子物理已经取代了经典牛顿物理学,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仍然在过时的牛顿模型下工作。目前已经有少量研究用量子理论来解释心灵和有意识的经验。本文认为,经验不可能既是物理现象,又是非物理现象。在讨论因果关系和先验同一性时,量子理论可能暗示有意识经验的量子物理性质,人们将因果关系与有意识的经验联系起来,结果就是双重方面理论和心灵/大脑同一性理论将被驳斥。
危险材料意识
序言 欢迎参加危险材料 - 意识认证课程。本课程符合 NFPA 472《危险材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响应人员能力标准》(2018 年)和 NFPA 1072《危险材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急响应人员专业资格标准》(2017 年)。根据联邦法规,本课程的所有毕业生都必须接受年度再培训。再培训必须具有足够的内容和持续时间以维持其认证,或者毕业生必须至少每年证明在这些领域的能力(即危险材料演习、多媒体培训、课堂培训或参与实际的危险材料应急响应)。这是雇主必须遵守的法律要求(29 CFR 1910.120-q-6),国家紧急反应委员会要求每年进行 4 小时的持续教育以保留每年的认证(即危险品演习、多媒体培训、课堂培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培训或参与实际的危险品应急响应)。
危险材料意识
序言 欢迎参加危险品 - 意识认证课程。本课程符合 NFPA 472《危险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响应人员能力标准》(2018 年)和 NFPA 1072《危险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急响应人员专业资格标准》(2017 年)。根据联邦法规,本课程的所有毕业生都必须接受年度再培训。再培训必须具有足够的内容和持续时间以维持其认证,或者毕业生应至少每年证明其在这些领域的能力(即危险品演习、多媒体培训、课堂培训或参与实际的危险品应急响应)。这是雇主必须遵守的法律要求 (29 CFR 1910.120-q-6),州应急委员会要求雇主每年接受 4 小时的持续教育,以保留每年的认证(即危险品演习、多媒体培训、课堂培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培训或参与实际的危险品应急响应)。
关于意识的各种问题
心理学 110 2006 年秋季 关于意识的各种问题 1. 什么是意识?花几分钟时间思考一下意识的定义特征或要求是什么。 (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回答这个问题会更有趣。如果您改变主意了,可以回来回答——但是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试着想出一些答案。) 2. 我记得我 2 岁左右之前的事情很少。那段时间我有意识吗?我怎么知道的? 3. 狗有意识吗?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4. 问题 3 中假设的狗身上的跳蚤有意识吗?跳蚤的行为与你对前面几个问题的回答相比如何? 5. 大多数花都向着光生长。有些甚至会移动并“吃掉”动物(例如捕蝇草)。它们有意识吗? 6. 不久前,一台计算机在国际象棋中击败了加里卡斯帕罗夫(现任世界冠军)。其他计算机可以学习、“观察”和模拟其他人类行为。这些计算机中有具有意识的吗?如果没有,计算机将来有可能具有意识吗? 7. 本讲义的背面列出了关于意识的三种不同观点。请一名小组成员代表每种观点(如果您不这么认为也没关系)进行小组讨论。尝试就哪种观点最有说服力达成一致。写下来并说明您认为这是最佳选择的原因。 8. 举一些“无意识”心理过程的例子。 9. 无意识过程会影响行为吗?请举出您能想到的任何例子。 10. 感知需要意识吗?潜意识感知存在吗?
意识如何以及为何产生
首先,这是一次初步交流,我们在此大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讨论的主题涉及许多专业领域。因此,对我们的提案进行全面的阐释——对多种文献进行适当的公正对待——需要比期刊文章更长的篇幅。其次,查尔默斯提出的意识难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如果这一事实意味着它无法通过科学“解决”,我们承认我们只能对上述问题提供科学的回应。查尔默斯的难题基于纳格尔早先的主张,即意识具有一种基本的“某种相似性”:“一个有机体具有意识的精神状态,当且仅当存在某种东西,即有机体是某种东西”(纳格尔,1974 年)。因此,我们旨在(大体上)勾勒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科学答案,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机体会有一种感觉,对于有机体来说,这种感觉是如何产生的?纳格尔指出,“如果我们承认物理的心理理论必须解释经验的主观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没有任何概念能为我们提供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线索”(同上)。我们希望提供这样的线索。但是——这是我们最后的免责声明——我们的物理理论是用功能术语来表达的,这又打开了另一个哲学难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通过定义“功能”的含义来预先解决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