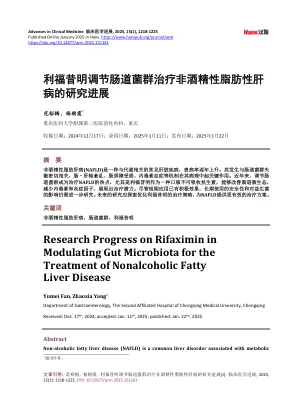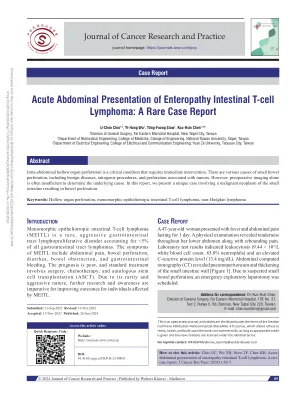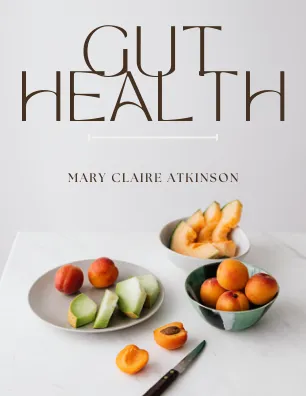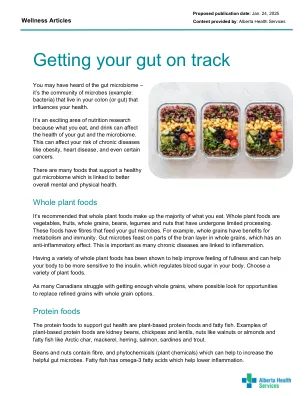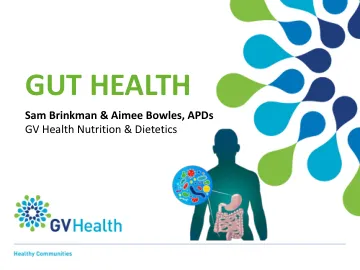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利福昔明调节肠道菌群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研究进展
异常及其患病率每年增加。其发育与肠道微生物群的不平衡密切相关,诸如肠道肝轴的破坏,对睾丸屏障的损害以及内毒素血症在其发病机理中起关键作用。近年来,肠道菌群的调节已成为NAFLD治疗的热门话题。Rifaximin是一种口服施用的不可吸收抗生素,在改善肠道菌群,减少氧毒素和减少炎症因子方面已显示出潜力。虽然短期使用已显示出积极的影响,但长期使用的安全及其对有益细菌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future研究应着重于优化利福昔明治疗策略,以为NAFLD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肠道肠道肠道T- ...
在恢复肠功能和正常日常活动的平稳恢复后,患者在第30天进行术后出院。然后,她接受了六个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和泼尼松(CHOP)化学疗法的周期。在此初始课程之后,进行了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扫描以评估治疗反应。结果表明腹腔内肿瘤的局部复发,尽管没有肠梗阻的迹象。作为一种打捞疗法,她接受了依托泊苷,顺铂,高剂量ARA − C和甲基促苯甲甲醇方案,然后是干细胞收获。随后,她接受了九个对福洛特尼的化学疗法的周期。由于进行性疾病,她接受了两个循环的地塞米松,顺铂和高剂量的Ara -c,以及一个吉西他滨,地塞米松和顺铂循环。然后,她接受了自体血干细胞移植的弯曲霉,依托泊苷,细胞蛋白滨和梅尔法兰调节。
产生遗传毒素的肠道肠道肠道诱导组织 -
一组蛋白质是运输(ESCRT)所需的内体分选复合物,在膜重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涉及细胞膜重排的细胞过程。理解和控制ESCRT的特定部分由于其复杂的组织而具有挑战性。在这里,我们描述了一种天然产物 - 例如复合触觉,专门破坏了ESCRT的特定部分,称为IST1 -CHMP1B复合物。使用触觉素作为化学工具,我们研究了该复合物如何有助于不同的膜重塑事件。有趣的是,诱使诱导非规范的LC3脂质 - 涉及失速内体的非规范自噬(自饮食)的过程。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ESCRT功能的理解,并强调了小分子作为揭示复杂生物学机制的宝贵工具的重要性。
肠道轴轴:肠道菌群对
摘要:简介:皮肤稳态与营养不良之间的双向联系,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及其对皮肤等远处器官(例如皮肤)的免疫调节潜力的影响,已成为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伴随着人口老化的现象,可以预防策略娱乐的发展,并延迟娱乐的发展。以健康的方式按时间顺序排列。材料和方法:这是对文献的叙述性回顾,使用了皮肤老化,肠道营养不良,肠道微生物群,肠,肠,肠,益生菌和益生菌轴的描述符。被调查的电子数据库是NCBI,PubMed,Scielo和Google Scholar。调查是在2024年3月至2024年11月之间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进行的。总共将25篇文章用作有关研究的基础。理论参考:微生物群失衡,称为营养不良,会损害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导致皮肤衰老。饮食和药物等因素会影响营养不良及其与衰老的关系。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肠道轴轴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益生元和益生菌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调节可以促进皮肤健康益处。最终考虑:这项工作有助于未来的研究,以阐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机制,尤其是制定新策略和干预措施以防止皮肤过早衰老,以健康的方式延迟年代老化并保持皮肤健康。
肠道连接
神经可塑性是指大脑回路重组和改变网络特性的能力,从而导致脑功能和行为的改变。传统上认为,神经可塑性受到外部刺激,学习和经验的影响。有趣的是,有新的证据表明,人体外围的内聚合信号可能起作用。肠道微生物群是一个与宿主和谐相处的微生物社区,可能能够通过调节肠道轴的调节来影响可塑性。有趣的是,肠道微生物群的成熟与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相吻合,在此期间,神经回路是高度塑性且潜在脆弱的。因此,早期生命中的营养不良(肠道菌群组成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正常发育轨迹的破坏,导致神经发育障碍。本综述旨在检查肠道菌群会影响神经可塑性的方式。还将讨论将胃肠道问题和细菌性营养不良与各种神经发育疾病及其对神经逻辑结果的潜在影响联系起来的最新研究。
肠道微生物
新生儿中对抗生素的抽象抗药性是一个巨大的关注点,因为其免疫系统仍在发展,并且早期生活中的感染和抵抗获得对其健康产生了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双歧杆菌物种是能够主导婴儿肠道微生物组的重要份量,并且众所周知,比其他可能在婴儿中定位的分类群相比,它不容易拥有抗菌耐药基因。我们旨在研究新生儿中主导的双歧杆菌肠肠菌群和抗生素耐药基因负荷之间的关联,并确定可能有助于抗生素耐药性的围产期因子。在7天和1个月大的MAMI出生队列中包括200个婴儿粪便样本,并为此提供了孕产妇的炎症性临床记录。通过16S rRNA扩增子测序进行微生物群,并通过qPCR定量靶向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包括TETM,TETW,TETO,TETO,Blatem,Blatem,Blashv和ERMB)。婴儿菌群根据双歧杆菌的丰度聚集成两组:高和低。使用基于双歧杆菌属相对丰度的时间点,使用无监督的K均值分配的非线性非线性算法进行组的主要分离。微生物群的组成均显着不同,并且在每个簇中富集了特定的双歧杆菌物种。婴儿肠道中的双歧杆菌的丰度较低与较高的抗生素耐药基因载荷有关。我们的结果强调了双歧杆菌属在早期获得中的相关性,并确立了肠道中抗生素耐药性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制定策略,以促进健康的早期定殖并与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