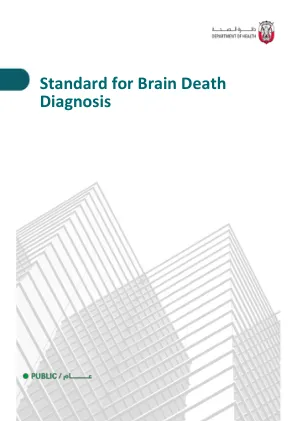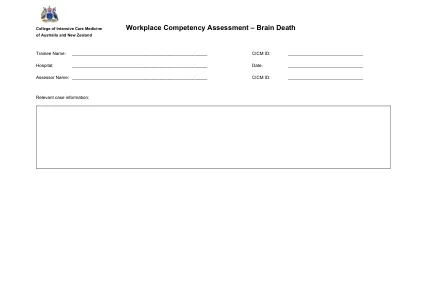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儿童和成人脑死亡/神经系统死亡标准共识指南
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 Chobanian & Avedisian 医学院和波士顿医学中心神经内科 (DMG, CT);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费城儿童医院麻醉学和重症监护医学系、神经内科和儿科 (MPK);纽约市 NYU Langone 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 (AL);堪萨斯城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内科 (GSG);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克利夫兰诊所勒纳医学院神经内科 (AR-G.);加利福尼亚州罗马琳达大学医学院儿科和神经内科 (SA);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外科附属机构管理组 (MAB);休斯顿德克萨斯儿童医院贝勒医学院神经外科 (DFB);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内科 (LB);亚特兰大 VA 医疗中心和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放射学和影像科学系 (AC);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神经病学和儿科学系 (SP);达拉斯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神经病学系 (MAR);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重症监护医学、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 (LS) 系;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儿童医院麻醉系 (RCT);纽约州奥尔巴尼医学院神经病学系 (PNV);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梅奥诊所神经病学系 (EW);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美国神经病学学会 (AB、SRW);新泽西州萨米特 Overlook 医疗中心神经科学系 (JJH)。
循环系统与大脑死亡的统一确定死亡法案的不一致性
对死亡法案的统一确定(UDDA)规定:“维持循环和呼吸功能的不可逆转的停止,或(2)(2)不可逆转的停止,包括大脑在内的整个大脑的所有功能,包括大脑茎,都死了。”我们表明,UDDA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相互作用,“功能停止”。通过一种解释,无论是通过人工手段而产生的,对死亡的确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停止自发和人为支持的功能。由于每个UDDA标准都使用不同的解释,因此法律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单一一致的相互作用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为支持的呼吸和循环功能的有意识的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或者那些大脑完全被不可逆转地破坏的人可能还活着。我们探索解决方案以减轻不一致。
《统一死亡判定法》中循环系统死亡标准与脑死亡标准不一致
《统一死亡判定法》(UDDA)规定,“个人(1)循环和呼吸功能不可逆停止,或(2)整个大脑(包括脑干)所有功能不可逆停止,即为死亡”。我们发现,UDDA 对“功能停止”一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判定死亡只看自发功能的停止,与是否通过人工手段产生无关。另一种解释认为,判定死亡看自发功能的停止和人工支持的功能的停止。由于每条 UDDA 标准使用不同的解释,因此法律在概念上不一致。一种一致的解释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意识的个体,其呼吸和循环功能由人工支持,实际上已经死亡,或者大脑被完全不可逆地破坏的个体可能还活着。我们探索了缓解不一致的解决方案。
模板5:脑死亡诊断的标准
➢新生儿 /婴儿:年龄[37周妊娠 - 60天]➢婴儿 /儿童:[> 60天 - 1天 - 1岁]➢儿童:年龄[> 1年 - 18岁]➢成年人:年龄[> 18岁] F)定义一个过程,以识别和管理与适用的UAE法律相一致的替代同意治疗的过程,并确保他们能够确保他们的支持,并确保他们的支持人员的支持。g)定义与诊断有关的文档,报告和通知要求以及手续,并管理涉嫌或确认的脑死亡及其家人的患者。h)确保为医疗保健劳动力的相关成员提供有关潜在脑死亡患者诊断的必要资源,支持,培训和方向。
作为人类有机体死亡的脑死亡的新防御
改变死亡的定义是否合理?在有关脑死亡的文献中,有1个广泛且相关的原因是针对积极答案的。首先是,在任何重新定义之后,我们将不再谈论以前谈论的同一件事。第二个是重新定义一个术语可以拒绝接受信念或假设已被驳斥,从而保护原始假设或信念免于伪造(Nair-Collins,2010)。该过程是以“扭曲”死亡概念为代价的(Joffe,2007年)。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有关在有关脑死亡的辩论中改变死亡定义的怀疑的两个原因。我们将争辩说,这两个原因都被夸大了,我们将捍卫一种新的理由,以证明将脑死亡与人类的死亡相当。
脑死亡争论:从生物伦理学到生命哲学
摘要 脑死亡引入 50 年后,学者们对其仍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是:脑死亡是确定死亡的良好标准吗?这个问题已从医学、形而上学、伦理、法律或政治等各个角度得到解答。大多数作者要么坚持原样捍卫该标准,要么提出一些小的或大的修改,要么主张放弃它并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脑死亡引入时旨在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我呼吁一种被文献忽视的不同方法:科学哲学方法。一些学者声称,人类死亡是一个事实,是一种生物现象,其发生可以通过科学经验确定。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一说法,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人类死亡是一个科学事实?采取科学哲学的方法,包括考察人的死亡判定如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探索脑死亡标准本身的性质,分析其“不可逆性”、“功能”等核心概念的含义。
放射核素对脑死亡后患者的评价...
5. ACR–SPR 实践参数,用于执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SPECT) 脑灌注和脑死亡检查。收录于:美国放射学会 (ACR)、儿科放射学会 (SPR),编辑;2014 年。
重新思考脑死亡:一种生理,哲学和...
“脑死亡”一词是一个相当站不住脚的描述,可以在道德上捍卫。这需要对“皮质脑死亡”,“全脑死亡”和WBD进行整理。器官移植混淆了WBD和“生物死亡”之间的差异,即完全停止身体功能。显然,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清楚地证明,不可逆性通过多个标准(呼吸暂停,脑干功能,缺乏长发脑电图等)来提出自己的利益。如果符合这些标准,我们可以拥有医学,生理和道德标准,并且宣布脑死亡,从而允许器官移植是道德的,从定义上讲,通过这样做会造成生物学死亡。这是一种非常有结果的方法,但是它确实通过将大脑分开或更重要的是“良心”的概念以及定义“人格”或缺乏二元的概念来安抚二元主义伦理。我认为1968年的哈佛“死亡宣言”不符合上述标准,而AMA宣言(2003年正式通过)指出:“必须根据公认的医疗标准确定死亡的决定”,但是,这些医疗标准未描述。本文解决了这些标准。
工作场所能力评估 – 脑死亡
• 昏迷测试(脑神经分布对面部、躯干和四肢的有害刺激没有运动反应,脑神经分布对周围刺激没有反应 - 眶上神经压力/胸骨摩擦音/深甲床压力) • 进行脑干反射的临床测试并准确解释结果(瞳孔对光反射、角膜反射、三叉神经分布对疼痛的反射反应、前庭眼反射、呕吐反射、咳嗽反射、呼吸暂停测试) • 确定观察结果是否与脑死亡相符/不相符 • 相符:脊髓反射/出汗脸红心动过速/血压正常而不需要正性肌力药物/没有尿崩症 • 不相符:去大脑或去皮质姿势/对疼痛刺激的真正伸肌或屈肌运动反应/癫痫
脑死亡是人类有机体的终结...
同事)撤回了这一主张,并断言生物体本身的损失是重要的。这种断言是深层形而上学的,因为人类死亡与人类生物有关,而不是像“人格”这样的组织的某些特殊特性,这种特殊特性通常是根据精神或社会建构的特性(或两者)进行分析的。它也不允许诸如死亡的生物之类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整个死者。它也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除了有机体的活动外,有生物的整体存在什么?很难指定。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什么样的活动表明总体上停止的生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相信大脑的破坏是停止人类有机体的足够标准的理由是什么?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可能会想知道确定人类生物的死亡是否甚至是正确的起点。也许“我们的”死亡条件与一般的生物的死亡条件不同,而“我们”根本不是生物。本文的目的是回答这些问题,并捍卫“脑死亡”或“完全脑部衰竭”(总统的生物伦理会理事会,2008年),这认真对待人类本体论和人类生物学的问题。是假设一个人可以在一个人的生物继续前进时停止存在“人”来“死亡”。我的目的是驳斥这两种观点。1通常在脑死亡文献中没有争论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机体,除了某些所谓的“更高”的大脑拥护者倡导者,他们认为我们是某种心理或社会实体(或两者都可以通过与某种形式的新皮大脑活动相关的意识或社交互动的能力链接到我们的Neoportical脑活动的能力)(VEATCER),1975年,1975年,1975年; 1975年; McMahan,2002年; Lizza,2006年)。一个相反的观点是我们是生物体,但是我们的生物可以在整个大脑的功能上丧失,包括大脑茎(例如Shewmon,2010; Miller and Truog,2012年)。在第一部分中,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形而上学理由将死亡视为涉及人类有机体作为一个自我移动的整体的终结 - 在基本的二阶能力方面分析了整体性(viz。具有限制性的能力),用于对物种特异性末端的自动移动,而不是仅仅丢失了整个整体的特殊特性,例如“人格”,甚至是自我移动的一阶能力(在低温或巴比妥酸盐过量的可逆情况下可能会丢失)。在第二个中,我谈到了D. Alan Shewmon的有影响力的论点,即神经系统标准与确定死亡相同。在第三局中,我对整体的“充满乐趣工作”标准提供了新的辩护,这些标准在总统理事会(2008年)(2008年)的“白皮书”中所规定,并解释了对物种特定目的的自我动作与“基本工作”的自我作用如何在死亡的定义和司法性方面的定义中所涉及的,并在临时努力方面和努力努力,并涉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