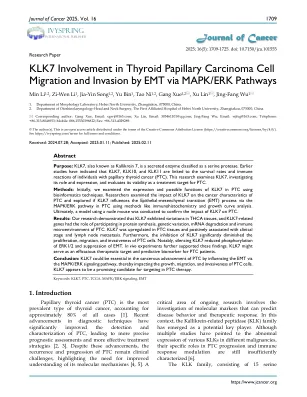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kallikrein
2024; 15(2):494-507。 doi:10.7150/jca.89986研究论文Baicalin通过NF-κB-NLRP3信号轴诱导胃癌细胞凋亡
目的:KLK7,也称为kallikrein 7,是一种分泌的酶,被分类为丝氨酸蛋白酶。较早的研究表明,KLK7,KLK10和KLK11与甲状腺乳头状甲状腺癌(PTC)个体的存活率和免疫反应有关。本研究检查了KLK7,研究其作用和表达,并评估其作为PTC治疗靶标的生存能力。方法:最初,我们使用生物信息学技术检查了KLK7在PTC中的表达和可能功能。研究人员检查了KLK7对PTC癌症特征的影响,并探讨了KLK7是否使用PTC中的MAPK/ERK途径使用免疫组织化学和生长曲线分析来影响上皮 - 间质转变(EMT)过程。最终,进行了使用裸鼠的模型,以确认KLK7对PTC的影响。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KLK7在THCA组织中表现出差异,而KLK7相关的基因具有参与PTC的蛋白质合成,遗传变异,mRNA降解和免疫微环境的作用。klk7在PTC组织中被上调,并与临床阶段和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此外,KLK7的抑制显着降低了PTC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入性。值得注意的是,沉默的KLK7降低了ERK1/2的磷酸化和EMT的抑制。体内实验进一步支持了这些发现。klk7可能是PTC患者的有效治疗靶标和预测性生物标志物。KLK7似乎是针对PTC治疗的有前途的候选人。结论:通过通过MAPK/ERK信号通路影响EMT,KLK7可能在PTC的癌变中至关重要,从而影响PTC细胞的生长,迁移和侵入性。
jnumed.124.267416.full.pdf
尽管前列腺癌治疗领域已包含多种药物,但仍需要新的治疗方案来满足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mCRPC) 患者尚未满足的需求。尽管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是唯一对晚期前列腺癌男性产生临床益处的细胞表面靶点,但其他靶点可能会进一步促进针对这些患者的免疫、细胞毒性、放射性药物和其他肿瘤导向疗法。人激肽释放酶 2 (hK2) 是一种新型前列腺特异性靶点,在非前列腺组织中几乎没有表达。这项首次人体 0 期试验使用 111 In 放射性标记的抗 hK2 单克隆抗体 [ 111 In]-DOTA-h11B6,证实 hK2 是前列腺癌治疗的潜在靶点。方法:患有进行性 mCRPC 的参与者单次输注 2 mg [ 111 In]-DOTA-h11B6(185 MBq 111 In),同时输注或不输注 8 mg 未标记的 h11B6,以评估抗体质量效应。采集连续成像和连续血样,以确定 [ 111 In]-DOTA-h11B6 的生物分布、剂量、血清放射性和药代动力学。在 [ 111 In]-DOTA-h11B6 给药后的 2 周随访期内评估安全性。结果:22 名参与者接受了 [ 111 In]-DOTA-h11B6 治疗,并纳入本次分析。给药后 6 – 8 天内,[ 111 In]-DOTA-h11B6 在已知的 mCRPC 病变中明显蓄积,而其他器官的摄取有限。发生了两起与治疗无关的治疗引起的不良事件,包括 1 名患者的肿瘤相关出血,这导致研究提前终止。血清清除率、生物分布和肿瘤靶向性与总抗体质量(2 或 10 毫克)无关。结论:这项首次人体研究表明,可以使用 h11B6 作为平台识别和靶向肿瘤相关的 hK2,因为 h11B6 抗体选择性地在 mCRPC 转移中积累,具有与质量无关的清除动力学。这些数据支持 hK2 作为成像靶标和 hK2 靶向药物作为 mCRPC 患者潜在疗法的可行性。
Schmidt_遗传性血管性水肿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孟德尔随机化研究结果_审查后划红线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是一种罕见疾病,每 5 万到 10 万中就有一例发生。[1] 其特征是皮肤和黏膜下组织反复肿胀,这是由于遗传性 C1 抑制剂缺乏导致缓激肽产生抑制不足所致。C1 抑制剂通过抑制几种丝氨酸蛋白酶(包括补体 C1a、C1r、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丝氨酸蛋白酶 1 (MASP-1)、MASP-2、纤溶酶、激肽释放酶和凝血因子 XIa 和 XIIa)来控制补体、纤溶酶、内源性凝血和接触系统。[2] D-二聚体水平通常在血管性水肿发作期间升高(可能是由于纤溶酶生成增强),但血管性水肿发作期间的这种升高与血栓风险增加无关。[3]几篇关于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评论指出,HAE(即使在 D-二聚体水平升高的情况下)也不会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的风险。但是,除了患者和医生的经验之外,没有其他资料可以支持这一说法。但是,最近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检查了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与 C1 抑制剂缺乏症的许多潜在合并症,报告了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与 VTE 之间的关联。[4, 5]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可能会因 VTE 的指征和错误分类而受到混淆。[6] 鉴于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极为罕见,很难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调查这一发现。如果 HAE 确实与 VTE 有关,则可以假设 C1 抑制剂水平不太明显的变化也可能与 VTE 风险有关。孟德尔随机化 (MR) 是一种适合进一步研究 C1 抑制剂水平与 VTE 潜在风险之间潜在因果关系的方法。MR 是一种使用遗传变异作为工具来评估暴露和结果之间潜在因果关系的方法。MR 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受通常困扰观察性研究的混杂和反向因果关系风险的影响要小得多。Davies 等人撰写了一份关于孟德尔随机化工作原理的全面概述。[7] 为了探索较低的 C1 抑制剂水平与静脉血栓栓塞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进行了一项孟德尔随机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