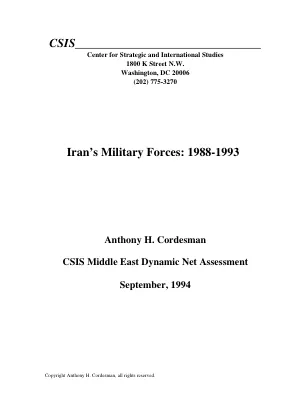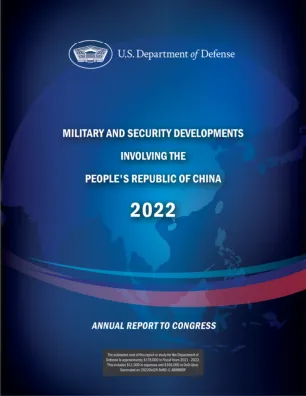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伊朗军事力量:1988-1993 - 亚马逊 AWS
人们很容易将伊朗和伊拉克视为对南部海湾和西方利益的共同威胁。然而,这样做也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这两个国家可能在许多方面对邻国和西方抱有政治敌意,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并不一定会导致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革命意识形态是否意味着愿意直接进行军事对抗还远未可知。尽管伊朗言辞激烈,但它似乎不像伊拉克那样愿意冒险。如果伊朗面临强大的威慑力量,它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政治行动和国内需求,而不是使用武力和军事攻击。伊朗现任政府不能像对待伊拉克那样被视为一个铁板一块或敌对的政权。自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去世以来,伊朗变得更加务实。伊朗近代史不像伊拉克那样具有侵略性和暴力性,它正在发展与西方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并寻求改善与南部海湾国家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尚不清楚实用主义是否意味着向温和方向发展,而不是对该地区力量平衡进行更现实的评估。伊朗仍然是一个革命性的伊斯兰社会,经常采取极端主义立场。其政府是压制性的,经常支持海外的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即使伊朗寻求与其南部海湾邻国和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也发生了逮捕、殴打和暗杀事件,这表明伊朗政权存在分歧,仍然有强大的强硬派分子。影响伊朗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二元论”也影响了其军事发展。一方面,伊朗正在积极建设军事力量,以便威胁和恐吓邻国。另一方面,伊朗有合法的强大防御需求。自 1980 年伊拉克首次入侵伊朗以来,伊朗与伊拉克交战了八年。地理位置既威胁着伊朗,也使其成为威胁。伊朗位于所谓的“危机弧”地带,其边界横跨前苏联与海湾地区以及西南亚与中东地区。伊朗面积约为 165 万平方公里。它与前苏联有 1,690 公里的边界,与土耳其有 499 公里的边界,与伊拉克有 1,448 公里的陆地边界,与巴基斯坦有 909 公里的边境,与印度有 936 公里的边界。
伊朗军事力量:1988-1993 - 亚马逊 AWS
人们很容易将伊朗和伊拉克视为对南部海湾和西方利益的共同威胁。然而,这样做也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这两个国家可能在许多方面对邻国和西方抱有政治敌意,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并不一定会导致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革命意识形态是否意味着愿意直接进行军事对抗还远未可知。尽管伊朗言辞激烈,但它似乎不像伊拉克那样愿意冒险。如果伊朗面临强大的威慑力量,它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政治行动和国内需求,而不是使用武力和军事攻击。伊朗现任政府不能像对待伊拉克那样被视为一个铁板一块或敌对的政权。自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去世以来,伊朗变得更加务实。伊朗近代史不像伊拉克那样具有侵略性和暴力性,它正在发展与西方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并寻求改善与南部海湾国家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尚不清楚实用主义是否意味着向温和方向发展,而不是对该地区力量平衡进行更现实的评估。伊朗仍然是一个革命性的伊斯兰社会,经常采取极端主义立场。其政府是压制性的,经常支持海外的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即使伊朗寻求与其南部海湾邻国和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也发生了逮捕、殴打和暗杀事件,这表明伊朗政权存在分歧,仍然有强大的强硬派分子。影响伊朗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二元论”也影响了其军事发展。一方面,伊朗正在积极建设军事力量,以便威胁和恐吓邻国。另一方面,伊朗有合法的强大防御需求。自 1980 年伊拉克首次入侵伊朗以来,伊朗与伊拉克交战了八年。地理位置既威胁着伊朗,也使其成为威胁。伊朗位于所谓的“危机弧”地带,其边界横跨前苏联与海湾地区以及西南亚与中东地区。伊朗面积约为 165 万平方公里。它与前苏联有 1,690 公里的边界,与土耳其有 499 公里的边界,与伊拉克有 1,448 公里的陆地边界,与巴基斯坦有 909 公里的边境,与印度有 936 公里的边界。
伊朗军事力量:1988-1993 - 亚马逊 AWS
人们很容易将伊朗和伊拉克视为对南部海湾和西方利益的共同威胁。然而,这样做也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这两个国家可能在许多方面对邻国和西方抱有政治敌意,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并不一定会导致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革命意识形态是否意味着愿意直接进行军事对抗还远未可知。尽管伊朗言辞激烈,但它似乎不像伊拉克那样愿意冒险。如果伊朗面临强大的威慑力量,它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政治行动和国内需求,而不是使用武力和军事攻击。伊朗现任政府不能像对待伊拉克那样被视为一个铁板一块或敌对的政权。自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去世以来,伊朗变得更加务实。伊朗近代史不像伊拉克那样具有侵略性和暴力性,它正在发展与西方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并寻求改善与南部海湾国家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尚不清楚实用主义是否意味着向温和方向发展,而不是对该地区力量平衡进行更现实的评估。伊朗仍然是一个革命性的伊斯兰社会,经常采取极端主义立场。其政府是压制性的,经常支持海外的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即使伊朗寻求与其南部海湾邻国和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也发生了逮捕、殴打和暗杀事件,这表明伊朗政权存在分歧,仍然有强大的强硬派分子。影响伊朗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二元论”也影响了其军事发展。一方面,伊朗正在积极建设军事力量,以便威胁和恐吓邻国。另一方面,伊朗有合法的强大防御需求。自 1980 年伊拉克首次入侵伊朗以来,伊朗与伊拉克交战了八年。地理位置既威胁着伊朗,也使其成为威胁。伊朗位于所谓的“危机弧”地带,其边界横跨前苏联与海湾地区以及西南亚与中东地区。伊朗面积约为 165 万平方公里。它与前苏联有 1,690 公里的边界,与土耳其有 499 公里的边界,与伊拉克有 1,448 公里的陆地边界,与巴基斯坦有 909 公里的边境,与印度有 936 公里的边界。
伊朗军事力量:1988-1993 - 亚马逊 AWS
人们很容易将伊朗和伊拉克视为对南部海湾和西方利益的共同威胁。然而,这样做也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这两个国家可能在许多方面对邻国和西方抱有政治敌意,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并不一定会导致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革命意识形态是否意味着愿意直接进行军事对抗还远未可知。尽管伊朗言辞激烈,但它似乎不像伊拉克那样愿意冒险。如果伊朗面临强大的威慑力量,它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政治行动和国内需求,而不是使用武力和军事攻击。伊朗现任政府不能像对待伊拉克那样被视为一个铁板一块或敌对的政权。自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去世以来,伊朗变得更加务实。伊朗近代史不像伊拉克那样具有侵略性和暴力性,它正在发展与西方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并寻求改善与南部海湾国家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尚不清楚实用主义是否意味着向温和方向发展,而不是对该地区力量平衡进行更现实的评估。伊朗仍然是一个革命性的伊斯兰社会,经常采取极端主义立场。其政府是压制性的,经常支持海外的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即使伊朗寻求与其南部海湾邻国和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也发生了逮捕、殴打和暗杀事件,这表明伊朗政权存在分歧,仍然有强大的强硬派分子。影响伊朗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二元论”也影响了其军事发展。一方面,伊朗正在积极建设军事力量,以便威胁和恐吓邻国。另一方面,伊朗有合法的强大防御需求。自 1980 年伊拉克首次入侵伊朗以来,伊朗与伊拉克交战了八年。地理位置既威胁着伊朗,也使其成为威胁。伊朗位于所谓的“危机弧”地带,其边界横跨前苏联与海湾地区以及西南亚与中东地区。伊朗面积约为 165 万平方公里。它与前苏联有 1,690 公里的边界,与土耳其有 499 公里的边界,与伊拉克有 1,448 公里的陆地边界,与巴基斯坦有 909 公里的边境,与印度有 936 公里的边界。
2022 年中国军事力量报告(CMPR)
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公法106-65)第1202节经修订规定,国防部长应提交一份“关于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情况的机密和非机密形式的报告”。报告应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发展的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中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宗旨和可能的发展,以及未来20年支持此类发展的军事组织和作战概念。报告还应涉及报告所述期间中美在安全事务上的接触与合作,包括通过中美军事接触,以及美国未来此类接触与合作的战略。”
TM E 30-480 日本军事力量手册
中型火炮 重型火炮 防空 气球 空中工兵(K6kQ)。 气象。 铁路信号(Denshin) 运输 特殊机动运输。 步兵迫击炮
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本文探讨了美国是否应该建立一支独立的网络军事力量。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美国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然后回顾了历史先例和大国竞争。然后,分析当前的网络军事结构,以帮助确定当前进攻性和防御性网络行动方法中的潜在差距。为了在推荐框架的背景下提供可能的行动方案,本文建议使用一个著名的军事框架,即 DOTMLPF-P(理论、组织、培训、物资、领导和教育、人员、设施和政策)。所采用的方法是定性文献综述,包括期刊文章、军事理论、历史参考、主题专家文章、美国政府会计局报告、网络行业报告和立法。该研究旨在让读者得出结论:现在是时候建立一支独立的美国网络部队了。
网络军事、交叉军事力量缺乏的两种解释...
本文探讨了为什么各国发动了如此多的网络攻击,却很少发起跨域行动(这里指网络和军事领域之间的行动)。我探讨了五种假设,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网络攻击不会与军事打击同时发生。我的分析表明,在这五种假设中,有两种是令人信服的。首先,国家攻击者出于基于内部分工的组织原因,做出不“跨域”的战略决策。其次,许多网络攻击者即使将网络和军事力量整合在一起,在跨域行动中仍面临重大技术挑战。其他三个原因不那么令人信服,包括对冲突升级的担忧、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国际法以及网络空间行为规范。
航空母舰和调动美国跨太平洋军事力量的能力,1919-1929
本文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一个十年期间,航空母舰在美国海军太平洋战争规划中的发展和定位。在卡伦·卡普兰将军事机动性定义为一种能力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随着航母技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它们不仅仅是负责支援舰队重炮的机动岛屿。本文借鉴了一系列主要资料,特别是有关橙色战争计划(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主要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的资料,并分析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文件,这些文件将航母定位为美国太平洋力量投射的关键工具(通常是雄心勃勃)。通过讨论 1924 年和 1929 年举行的两次美国舰队问题海军演习,本文认为,人们认识到需要同时考虑舰船和飞机的能力,这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战争规划者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战略机遇。© 2017 Elsevier Ltd. 出版。
航空母舰和调动美国跨太平洋军事力量的能力,1919-1929
本文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一个十年期间,航空母舰在美国海军太平洋战争规划中的发展和定位。本文以卡伦·卡普兰 (Caren Kaplan) 对军事机动能力的框架为基础,认为随着航母技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进步,人们认识到航母不仅仅是负责支援舰队大炮的机动岛屿。本文借鉴了一系列主要资料,特别是有关橙色战争计划(美国对日作战计划,主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制定)的资料,并分析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文件,这些文件将航母定位为美国太平洋力量投射的关键工具,通常是抱有远见卓识。通过讨论 1924 年和 1929 年举行的两次美国舰队问题海军演习,本文认为,人们认识到需要同时考虑舰船和飞机的能力,这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战争规划者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战略机遇。© 2017 作者。由 Elsevier Ltd. 出版。这是一篇根据 CC BY 许可开放获取的文章(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