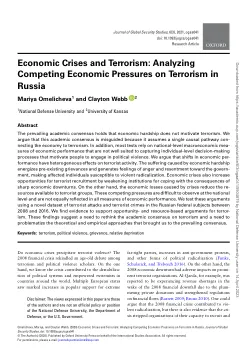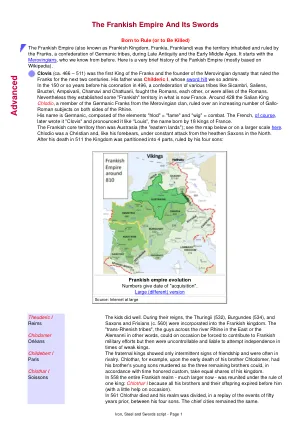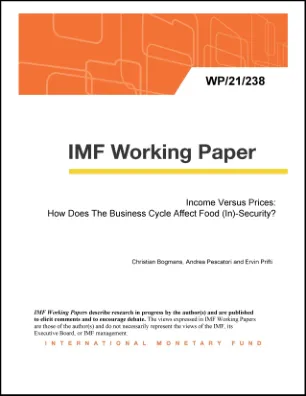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分析俄罗斯恐怖主义的竞争经济压力
普遍的学术共识认为,经济困难不会激发恐怖主义。我们认为,这一学术共识被误导了,因为它假设一种因果关系途径将经济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此外,大多数测试都依赖于国家水平的宏观经济表现,这些绩效不适合捕获个人级别的决策过程,这些过程激发人们参与政治暴力。我们认为,经济表现的转变会对恐怖活动产生异质作用。经济困难造成的痛苦使现有的申诉充满活力,并对政府产生愤怒和不满情绪,使受影响的个体容易受到暴力激进化。经济危机还通过削弱机构应对急剧经济低迷的后果来增加恐怖招募的机会。另一方面,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减少了恐怖组织可用的资源。这些竞争压力很难在国家一级观察,并且在所有经济绩效的措施中都没有得到同样的反映。我们使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在俄罗斯联邦臣民中的恐怖袭击和恐怖犯罪的新颖数据集测试了这些论点。我们找到了支持恐怖ISM的基于机会和资源的论点的证据。这些发现表明,有必要重新考虑恐怖主义的学术共识,并需要使我们达成了普遍共识的理论和经验方法的问题。
铁、钢与剑脚本
克洛维(约466 – 511)是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也是统治法兰克人两个世纪的墨洛温王朝的创始人。他的父亲是希尔德里克一世,我们非常钦佩他的剑柄。在他 496 年加冕之前的 150 年左右,西坎布里、萨利恩、布鲁克特里、安普西瓦里、查马维和查图阿里等各种部落组成的联盟与罗马人作战,相互争斗,或成为罗马人的盟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现在的法国建立了一些“法兰克”领土。大约在 428 年,萨利安国王 Chlodio 是日耳曼法兰克人中墨洛温家族的一员,他统治着莱茵河两岸越来越多的高卢罗马臣民。他的名字是日耳曼语,由“hlod”=“fame”和“wig”=“combat”组成。当然,法国人后来把它写成“Clovis”,发音为“Louis”,这是 18 位法国国王的名字。当时法兰克人的核心领土是奥斯特拉西亚(“东部土地”);请参见下面的地图或此处的较大比例。Chlodio 是一名基督徒,和他的祖先一样,不断受到北方异教撒克逊人的攻击。511 年他去世后,王国被分为四个部分,由他的四个儿子统治:
铁、钢与剑脚本
克洛维(约466 – 511)是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也是统治法兰克人两个世纪的墨洛温王朝的创始人。他的父亲是希尔德里克一世,我们非常钦佩他的剑柄。在他 496 年加冕之前的 150 年左右,西坎布里、萨利恩、布鲁克特里、安普西瓦里、查马维和查图阿里等各种部落组成的联盟与罗马人作战,相互争斗,或成为罗马人的盟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现在的法国建立了一些“法兰克”领土。大约在 428 年,萨利安国王 Chlodio 是日耳曼法兰克人中墨洛温家族的一员,他统治着莱茵河两岸越来越多的高卢罗马臣民。他的名字是日耳曼语,由“hlod”=“fame”和“wig”=“combat”组成。当然,法国人后来把它写成“Clovis”,发音为“Louis”,这是 18 位法国国王的名字。当时法兰克人的核心领土是奥斯特拉西亚(“东部土地”);请参见下面的地图或此处的较大比例。Chlodio 是一名基督徒,和他的祖先一样,不断受到北方异教撒克逊人的攻击。511 年他去世后,王国被分为四个部分,由他的四个儿子统治:
公平通知、法治和改革有限豁免权
在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警察暴力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法院、学者和政客要求废除有条件豁免权。该原则要求法院驳回对侵犯原告宪法权利的官员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除非一名合理的官员知道该权利是“明确确立的”。学者们认为,该原则剥夺了受害者获得赔偿和辩护的权利,阻碍了未来宪法违规行为的遏制。反对有条件豁免权的一个论点是依靠实证证据来挑战学者们认为的有条件豁免权的主要理由:它防止宪法责任的威胁过度阻止有效的执法。然而,美国最高法院一直为该原则提供另一种理由:在没有充分通知官员其行为违宪的情况下追究其责任是不公平的。与过度威慑理由不同,学者们几乎完全忽视了有条件豁免权的公平通知理由。本文评估了公平通知理由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当前的有条件豁免权原则。本文通过探索法理学前瞻性原则的局限性来实现这一点,该原则认为法律通常只能前瞻性地适用。为了接近法治并以平等的尊严对待臣民,法律必须能够指导行为。前瞻性原则显然适用于追溯性立法。本文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案例,即不可预测的裁决也无法提供这样的指导,而且当它们施加追溯性道德谴责时,它们尤其不公平。宪法责任往往是高度不可预测的,
内容 - ROSPHOTO
“范德莱”。荷兰或英国生产的纸张,18 世纪下半叶中叶。[11,第 11 页] 125,第2749号],即上面可能写着一封 19 世纪初的信。这封信的法文版中没有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签名,很自然地可以解释为,法文原件被发送到其预定目的地,但不一定是巴黎,而是收件人目前所在的地方。现在是时候谈谈信的内容了,两个版本的信纸边缘都被一个哀悼框包围着,这与当时为死者设立的死亡通知和哀悼形式非常一致。这封信涉及大公夫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夫娜 (Elizaveta Alexandrovna) 于 1808 年 4 月 30 日去世,她的母亲是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 (Elizaveta Alekseevna),出生于 1806 年 11 月 3 日。在《Camerfour 礼仪杂志》中有关 1808 年 4 月 30 日的条目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道:“早上八点陛下无限悲痛,皇室万分遗憾,太子殿下在她出生的第二年就去世了”[5,p.11]。330]。那里还报道说,下午两点,当皇家告解神父和其他宫廷神职人员已经主持了葬礼时,向外交部长伯爵发出了最高命令。N.P.Rumyantsev“关于礼仪部门准备埋葬殿下遗体的命令”[5,第 17 页]332]。两岁女大公去世的通知,当然是专门针对政府官场发表的一份特别宣言:“去年四月三十日,以全能上帝的力量,我们的亲爱的女儿伊丽莎白女大公在她两岁时就去世了。通过为我们宣布这一悲伤事件,我们确信我们所有忠实的臣民将与我们分享我们的悲伤”[9]。以下为1808年5月21日法国特使维琴察公爵阿尔芒·德·科兰古向拿破仑的报告,5月12日正式宣布其逝世消息,同时科兰古代表法国大使馆,向N.P.表示深切哀悼。Rumyantsev [6,第 14 页]141],因为无法与皇帝交谈。第二天,在给拿破仑的报告中,大使指出:“皇帝对 12 日去世的女儿深感悲痛”[6,第 12 页]。148]。他们周围的人利用这一点,使配偶之间的关系恢复......” [6,第 14 页]151]。154] 1 。在同一份电报中,谈到其他主题,特使写道:“大公夫人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皇后的极大同情:她处于彻底的绝望之中,皇帝本人也感到深深的悲伤。5 月 22 日,科兰古在致外交部长卡多尔公爵让-巴蒂斯特·尚帕尼 (Jean-Baptiste Champagny) 的一份报告中报告称,皇帝“已经好几天没有外出或处理事务了”[6,第 14 页]。5月29日,使者报告:“自从太子妃死后,皇帝很少出来,也不邀请任何人到他的地方;”
考蒂利耶的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简介 Arth 是 purusharthas 之一,其他三个是 dharma、kama 和 moksha。Arth 的含义远比财富广泛。财富是生活的来源,而国家的财富包括领土和居民。Shastra 是科学,因此,一个国家在实现 Dharma 目标的过程中获取和维持财富的科学就是 Arthashastra。考底利耶的 Arthashastra 是古印度治国之道的主要信息来源和不朽的著作。考底利耶的名字叫毗湿奴笈多。他之所以被称为考底利耶,是因为他是外交和政治战略方面的专家。他的著名著作《Arthashastra》本质上是一本关于国家管理的书,也是获取和防止财富的指南。《Arthashastra》这本书基于早期的条约,分为 15 个 adhikaranas 或书籍。本书共有 150 章、180 个主题和 6000 首诗。它详细介绍了过去,尤其是孔雀王朝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组织。考底利耶对财富一词的理解非常广泛。根据考底利耶的说法,财富对于一个国家保持主权至关重要,但财富的管理,考底利耶经常提到,国王必须让臣民幸福,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否则不应施加任何压迫性规则(Sarkar,2000 年)。一般来说,古印度人意识到财富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事实上,获得财富被描述为人生四大目标之一,即 Dharma(慈善)、Artha(财富)、Kama(爱)和 Moksha(救赎)。考底利耶认为,财富是一粒一粒地积累起来的,就像学习是每时每刻都要获得的一样。目标 1. 强调考底利耶经济思想的重要性。 2. 注重最佳管理;方法论 整篇论文本质上是基于描述性的。信息是从不同结构的经济思想史书籍中收集的。本文强调了考底利耶经济思想的意义。 考底利耶经济思想的意义 基础设施发展 考底利耶明白建立基础设施对发展经济的首要重要性。他非常重视通讯和交通。交通工具在古印度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考底利耶在他的《政事论》中强调了陆路和水路在贸易、防御和一般运输中的作用。他建议在村庄、堡垒、设防城市、农场等周围修建道路。他还强调主要用于贸易目的的河流和海上交通。道路分为各种类型,即 Rajya-Marga 或国王之路、高速公路、省道。道路供战车、牛车和商队使用。需求与供给 考底利耶熟知需求与供给的概念,以及它们对价格的综合影响。他认为,国王不应不考虑产品供需情况而随意确定产品价格。如果不适当考虑需求与供给,我们可能认为价格不能被称为公平价格,无法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
内容 - ROSPHOTO
“范德莱”。荷兰或英国生产的纸张,18 世纪下半叶中叶。[11,第 11 页] 125,第2749号],即上面可能写着一封 19 世纪初的信。这封信的法文版中没有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签名,很自然地可以解释为,法文原件被发送到其预定目的地,但不一定是巴黎,而是收件人目前所在的地方。现在是时候谈谈信的内容了,两个版本的信纸边缘都被一个哀悼框包围着,这与当时为死者设立的死亡通知和哀悼形式非常一致。这封信涉及大公夫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夫娜 (Elizaveta Alexandrovna) 于 1808 年 4 月 30 日去世,她的母亲是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 (Elizaveta Alekseevna),出生于 1806 年 11 月 3 日。在《Camerfour 礼仪杂志》中有关 1808 年 4 月 30 日的条目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道:“早上八点陛下无限悲痛,皇室万分遗憾,太子殿下在她出生的第二年就去世了”[5,p.11]。330]。那里还报道说,下午两点,当皇家告解神父和其他宫廷神职人员已经主持了葬礼时,向外交部长伯爵发出了最高命令。N.P.Rumyantsev“关于礼仪部门准备埋葬殿下遗体的命令”[5,第 17 页]332]。两岁女大公去世的通知,当然是专门针对政府官场发表的一份特别宣言:“去年四月三十日,以全能上帝的力量,我们的亲爱的女儿伊丽莎白女大公在她两岁时就去世了。通过为我们宣布这一悲伤事件,我们确信我们所有忠实的臣民将与我们分享我们的悲伤”[9]。以下为1808年5月21日法国特使维琴察公爵阿尔芒·德·科兰古向拿破仑的报告,5月12日正式宣布其逝世消息,同时科兰古代表法国大使馆,向N.P.表示深切哀悼。Rumyantsev [6,第 14 页]141],因为无法与皇帝交谈。第二天,在给拿破仑的报告中,大使指出:“皇帝对 12 日去世的女儿深感悲痛”[6,第 12 页]。148]。他们周围的人利用这一点,使配偶之间的关系恢复......” [6,第 14 页]151]。154] 1 。在同一份电报中,谈到其他主题,特使写道:“大公夫人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皇后的极大同情:她处于彻底的绝望之中,皇帝本人也感到深深的悲伤。5 月 22 日,科兰古在致外交部长卡多尔公爵让-巴蒂斯特·尚帕尼 (Jean-Baptiste Champagny) 的一份报告中报告称,皇帝“已经好几天没有外出或处理事务了”[6,第 14 页]。5月29日,使者报告:“自从太子妃死后,皇帝很少出来,也不邀请任何人到他的地方;”
内容 - ROSPHOTO
«范德莱»。18 世纪中叶至下半叶荷兰或英国制造的纸张。[11,页125,第2749号],即上面可能写着一封 19 世纪早期的信件。法语版信件中没有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签名,这很自然地可以解释为,法语原件已寄往目的地,但不一定寄往巴黎,而是寄往收件人当时所在的任何地方。现在来看看信件的内容,这两份信件的纸张边缘都用哀悼的框架勾勒出来,这与当时为死者设立的死亡和哀悼通知形式完全一致。死者。这封信涉及 1808 年 4 月 30 日大公夫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去世,她于 1806 年 11 月 3 日为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所生。在 1808 年 4 月 30 日的宫廷礼仪日记中,记载道:“早晨八点,皇太后陛下无限悲痛,皇室极为惋惜,皇太后殿下在出生第二年便去世了。”[5,第 196 页]330].另据报道,下午 2 点,当皇帝的忏悔者与其他宫廷神职人员一起主持完葬礼后,最高命令下达给了外交部长,数数。N.P.鲁缅采夫“关于为礼仪部门准备关于安葬皇太后遗体的命令” [5,第 173 页]332].这位两岁大公爵夫人的死讯当然是针对一份在政府官僚机构中发表的特别宣言而发布的:“去年四月三十日,以全能上帝的力量,我们挚爱的女儿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公夫人在两岁时去世。在向我们宣布这一悲伤事件时,我们确信,我们所有忠实的臣民都会与我们分享悲痛“[9]根据 1808 年 5 月 21 日法国特使维琴察公爵阿尔芒·德·科兰古给拿破仑的报告,拿破仑的死讯于 5 月 12 日正式公布,当时科兰古代表法国大使馆向N.P.表示深切哀悼。鲁缅采夫 [6,页.141],因为无法与皇帝交谈。第二天,大使在给拿破仑的报告中指出:“皇帝对他的女儿的去世深感悲痛,她于 12 日去世”[6,第 123 页]148].周围的人利用这一点,使夫妻之间的关系得到更新……”[6,第 173 页]151].154] 1.在同一份电报中,谈到其他主题,特使写道:“大公夫人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皇后的极大同情:她处于彻底的绝望之中,皇帝本人也感到深深的悲伤。5 月 22 日,科兰古在致外交部长卡多尔公爵让-巴蒂斯特·尚帕尼 (Jean-Baptiste Champagny) 的一份报告中报告称,皇帝“已经好几天没有外出或处理事务了”[6,第 14 页]。5月29日,使者报告:“自从太子妃死后,皇帝很少出来,也不邀请任何人到他的地方;”
下载 PDF
随着新冠疫情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有关全球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状况迅速恶化的传闻证据浮出水面。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停止导致失业,收入减少,再加上供应链中断导致粮食短缺和粮食价格上涨,数百万家庭陷入贫困,随后可能不得不降低所消费粮食的质量和数量。虽然贫困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粮食不安全将如何影响疫情引发的宏观经济衰退的证据充其量仍是传闻或仅限于灰色文献(Meyer 和 Sullivan,2011 年;粮农组织,2020 年)。本文旨在填补关于商业周期波动导致的粮食(不)安全短期变化的严格证据空白,并探讨相关政策工具在应对粮食不安全状况激增方面的作用。关于家庭粮食安全的微观决定因素的文献已大量记录了家庭收入、教育、种族、社会福利获得等因素的作用(Gundersen 等人,2011 年;Akter 和 Basher,2014 年;Tiwari 等人,2016 年)。另一方面,国家粮食安全的宏观驱动因素受到的关注较少。很少有研究调查过 GDP 或食品价格总体水平等总体经济因素对单个国家粮食不安全的影响,只有少数研究使用跨国数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过此类研究(Gregory 和 Coleman-Jensen,2013 年;Nord 等人,2014 年;Heady,2013 年;Soriano 和 Garrido,2016 年)。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篇采用跨国方法研究粮食不安全问题的论文,同时考虑了饮食的数量充足性和质量充足性的表现。具体来说,我们量化了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食品通胀、社会保护支出和初始条件对营养不足 (PoU) 发生率和饮食结构的影响。在综合框架中确定收入和食品通胀的相对强度、食品购买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社会保护等收入支持措施,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如果我们考虑到粮食(不)安全对经济发展的长期重大影响,其宏观相关性就变得清晰起来。营养不良和不良饮食结构,尤其是在儿童时期,会对身体和智力发育产生负面影响,限制教育水平和终身收入潜力——从而使人们陷入贫困陷阱,从而加剧不平等(Victora 等人,2008 年;Atinmo 等人,2009 年)。从总体上看,如果这种现象在人口中普遍存在,就会降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因此,其经济增长潜力(Fogel,2004)。更广泛地说,由于与人类基本需求有关,粮食(不)安全在整个历史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催化了政治变革并引发了冲突。例子很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轻松地邀请她的臣民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