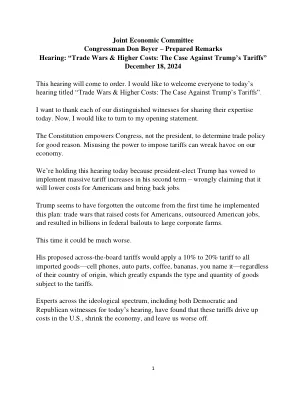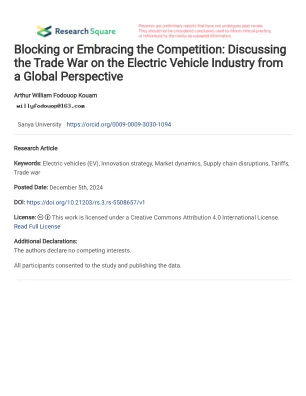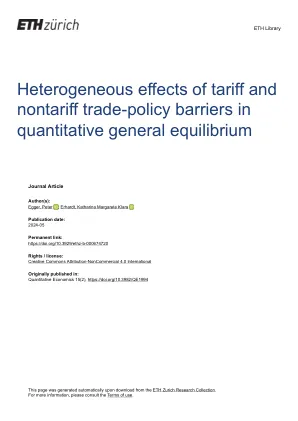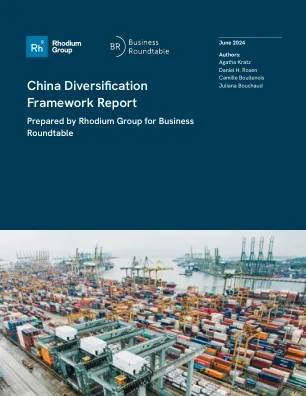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经济学
•我们的基线前景仍然避免衰退。•进一步的关税升级很容易翻转脚本。•这次贸易转移将不再是令人震惊的吸收者。•铝和钢制关税将在本地受到伤害,但在宏观水平上不关心。全球贸易战的开幕式已经交换了,尽管拉丁美洲却险些脱离了射击线,但艰难的日子仍在前面。与2018年至2019年的贸易战相反,当时该地区能够通过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出口更大的商品,更高的关税和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将对全球增长的份额出口较大,将对增长的增长造成更大的影响。,我们在2025年将对拉丁美洲的预测降低了0.3个百分点,在2026年将0.4个百分点降低了,以反映美国关税的直接影响以及降低的全球经济。,即使不是为阿根廷的新生反弹,拉丁美洲的增长的打击将更高,而阿根廷的经济正在从近一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EDC媒体背景模板 - 2025年3月
截至3月4日,特朗普总统已向美国进口进口征收25%的关税,并对能源进口征收10%的关税。一场长时间的贸易战将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加拿大人造成巨大后果,而EV制造和农业等重要部门可能首当其冲。关税可能会使无数的加拿大就业机会处于危险之中,破坏该国的国内外投资,并随着公司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重新点燃通货膨胀。加拿大对这些不合理的关税的反应必须集中在保护最受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以及已经为生活成本而苦苦挣扎的脆弱家庭中。应对特朗普对关税的威胁和全面爆炸的贸易战,加拿大政府征得了自己的报复性关税。自身的报复性关税可能不会阻止特朗普政府,也不会充分提高加拿大的谈判立场。加拿大政府应使用其最强大的工具,并采用反对措施,以建立财政部,以减轻工人和社区的打击,并使加拿大长期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确保加拿大工人和家庭得到保护
贸易战和更高的成本:针对特朗普的关税案件
这次听证会将订购。我想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题为“贸易战与更高成本:针对特朗普的关税的案件”。我要感谢我们的每位杰出见证人今天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现在,我想转向我的开幕词。宪法赋予国会,而不是总统,有充分的理由确定贸易政策。滥用权力征收关税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我们今天举行了这次听证会,因为当选总统特朗普已发誓要在其第二任期内实施大量关税 - 错误地声称它将降低美国人的成本并带回工作。特朗普似乎从第一次实施这一计划就忘记了结果:贸易战提高了美国人的成本,外包美国的工作,并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救助到大型企业农场。这次可能会更糟。他提议的全板关税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包括手机,汽车零件,咖啡,香蕉,您命名)对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申请10%至20%的关税 - 对他们的原籍国没有任何责任,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受到关税的商品类型和数量。各个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专家,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证人的今天听证会,发现这些关税在美国增加了成本,缩小了经济,并使我们变得更糟。
阻止或拥抱竞争:从全球角度讨论电动汽车行业的贸易战争
Blocking or Embracing the Competition: Discussing the Trade War on the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rthur William Fodouop Kouam Assistant Professor, Saxo Fintech Business School, Sanya University, China E-mail: willyfodouop@163.com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ultifaceted impact of the ongoing US-China trade war on the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EV) industry, scrutinizing how tariffs, supply chain干扰和竞争动态使生产成本,市场份额和创新策略重塑。利用混合方法方法,我们通过多个线性回归(MLR)对从20个领先的EV市场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我们通过与15位行业专家的半结构化访谈中的定性见解相辅相成。我们的分析表明,对电动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生产成本显着提高,从而导致市场份额从中国公司向国内生产商处于关税国家的国内生产商的明显转变。此外,研究结果表明,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公司相比,拥护协作竞争的公司倾向于促进更高水平的创新水平。通过整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这项研究增加了有关贸易战和工业竞争力的现有文献,强调了关税可能提供临时保护,但它们阻碍了EV部门的长期创新和韧性。关键字:电动汽车(EV),创新策略,市场动态,供应链中断,关税,贸易战jelcodes:F13,L62,O38 1。世界上最大的这场冲突这项研究通过对贸易战对全球规模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来填补一个关键的差距,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行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战略建议,这些建议是快速发展的景观。引言全球电动汽车(EV)行业在环境问题,政府支持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历了显着的增长(Mutta&Soumya,2024; Chaudhari,2024)。市场正在迅速扩展,成熟的汽车制造商和新进入者都争夺市场份额(Mutta&Soumya,2024年)。evs提供了许多好处,包括减少的排放和能源独立性(Chaudhari,2024; Tilkar等,2024)。然而,挑战持续存在,例如范围焦虑,有限的充电基础设施和更高的前期成本(Mutta&Soumya,2024; Sun等,2020)。政府的激励措施和政策在促进电动汽车的采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n等,2020; Tilkar等,2024)。电池技术的进步和充电基础设施的扩展有助于该行业的增长(Tilkar等,2024)。 但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对全球行业(尤其是技术和钢铁部门)引入了重大复杂性。 它破坏了供应链,网络安全风险增加并影响了知识产权问题(Choudary&Saleem,2023年)。 冲突导致了对基本技术产品的关税,从而影响了价格和供应链效率(Choudary&Saleem,2023; Bown,2020)。电池技术的进步和充电基础设施的扩展有助于该行业的增长(Tilkar等,2024)。但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对全球行业(尤其是技术和钢铁部门)引入了重大复杂性。它破坏了供应链,网络安全风险增加并影响了知识产权问题(Choudary&Saleem,2023年)。冲突导致了对基本技术产品的关税,从而影响了价格和供应链效率(Choudary&Saleem,2023; Bown,2020)。在中国有直接供应商的美国公司在库存管理和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现较差,尤其是那些具有高度外包和供应基础复杂性的公司(Fan等,2022)。最初不情愿的半导体行业是通过针对供应链的出口限制来纳入冲突的(Bown,2020年)。公司现在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的制造和采购依赖性,寻求替代生产地点和新市场(Choudary&Saleem,2023年)。贸易战的影响范围超出了美国和中国,影响了钢铁部门的欧盟和奥地利公司等其他政党(Scheipl等,2020)。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导致关税和限制影响了包括电动汽车部门在内的各个行业。这些措施导致价格上涨,供应链中断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减少(Mutambara,2019年; Choudary,2023年)。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对钴,加剧供应链脆弱性等关键材料的需求(Liu等,2023)。地缘政治风险和电动汽车需求冲击显着影响了钴供应链,在严重的进口量下,潜在价格上涨高达15.01%(Liu等,2023)。汽车行业向电动汽车的过渡促使供应链生态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影响了供应商的关系和协作(Jagani等,2024)。此外,贸易战引起了人们对电动汽车行业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关注。诸如改进回收技术,增加库存和探索物质替代的策略以增强弹性(Liu等,2023)。始于2018年的美国 - 中国贸易战争涉及两个国家对彼此商品征收关税(Khan&Khan,2022; SU,2024; Qiu等人,2019年; Ovuakporaye,2020年)。
降低电信行业供应链风险
地缘政治动荡,包括贸易战、政治不稳定和国际冲突,也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和中国之间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征收关税和贸易限制增加了半导体和稀土矿物等关键部件的成本,影响了电信公司的盈利能力。此外,COVID-19 疫情凸显了全球供应链对不可预见事件的脆弱性。疫情引发的封锁以及制造、物流和劳动力供应的中断导致半导体和显示面板等关键部件严重短缺,严重影响了智能手机、5G 设备和其他电信设备的生产和交付。
定量一般平衡中关税和非贸易贸易政策障碍的异质效应
peter H.沙尔。We are also thankful for comments from participants at several seminars (University of Salzburg,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versity of Mannheim) and conferences (Villars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RONTO Workshop in Paris, DEGIT in Nottingham, EEA in Geneva, ETSG in Paris, Stoos Sinergia Workshop, TRISTAN workshop in Bayreuth).1参见Breinlich等人的最新作品。(2016),Felbermayr,Aichele和Heiland(2016)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或Fajgelbaum,Goldberg,Kennedy和Khandelwal(2019)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2018年美国贸易战。
中国多元化框架报告
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正在重新思考中国过度依赖的全球制造业和采购中心。第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中国规模和范围巨大规模的经济,中国的多元化是否可能是可能的。我们发现,正确定义(Box 1),多元化已经达到有限但重要的程度。震惊美国 - 中国“贸易战”,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以及其他活动的震惊使超大全球化价值链的风险清晰明了,从而改变了商业和政策计划中这些风险的估值。 尽管政治当局寻求稳定,但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和中国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 但中国的市场规模,四十年的制造投资繁荣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带来了多元化的重大障碍。 即使其他经济体享有相同的属性,使中国具有吸引力并与美国保持更好的安全性一致性,多元化也可能很困难。震惊美国 - 中国“贸易战”,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以及其他活动的震惊使超大全球化价值链的风险清晰明了,从而改变了商业和政策计划中这些风险的估值。尽管政治当局寻求稳定,但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和中国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但中国的市场规模,四十年的制造投资繁荣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带来了多元化的重大障碍。即使其他经济体享有相同的属性,使中国具有吸引力并与美国保持更好的安全性一致性,多元化也可能很困难。
使用自然语言分析金融新闻...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实时更新和分析至关重要。这些市场容易受到全球事件和现象的影响,例如贸易战、内乱、创新和科学发现。金融新闻可从多种来源获得,包括在线和离线。这里的在线来源是指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的来源,这里的离线来源是指通过其他媒体传播的来源。离线来源包括通过报纸和电视获得的新闻和见解。对于像股票市场一样敏感的金融市场来说,通过报纸获得的新闻已经过时了。电视上的新闻是现场直播的,但这种新闻无法轻松分析。在相关性和分析的简易性方面,在线资源比离线资源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