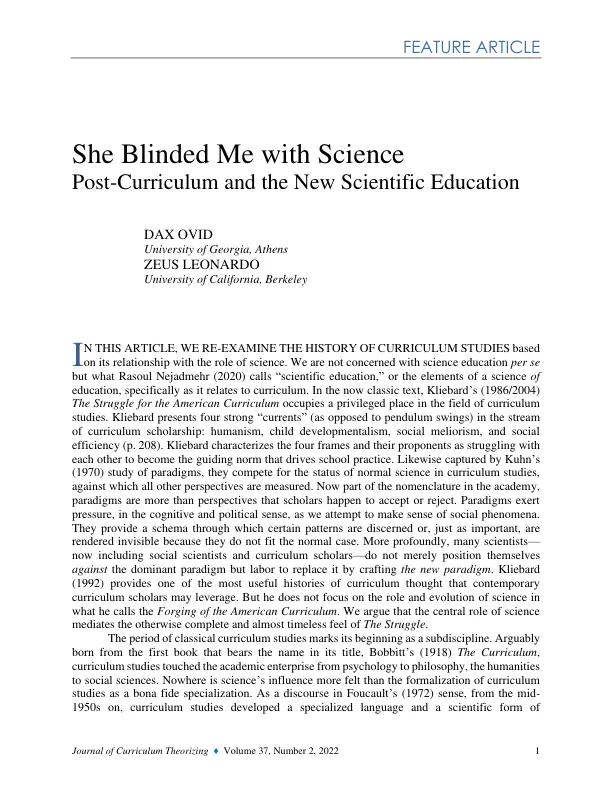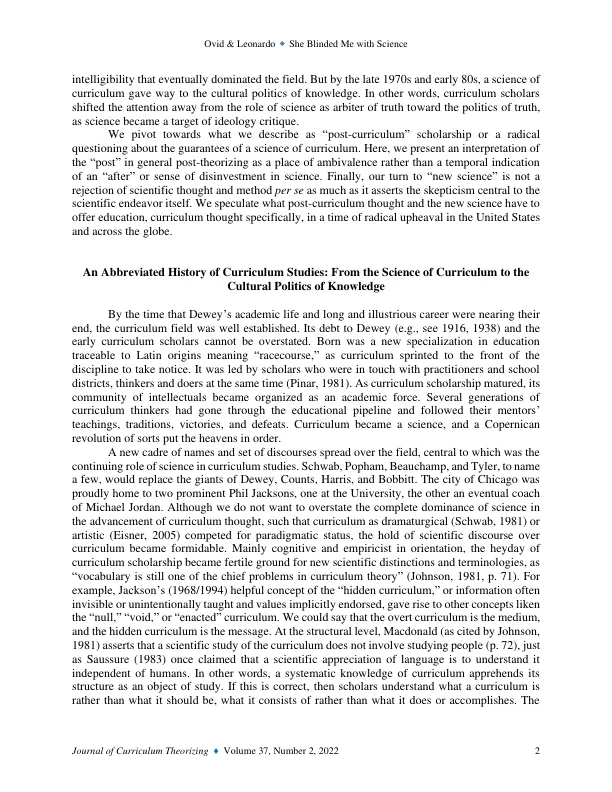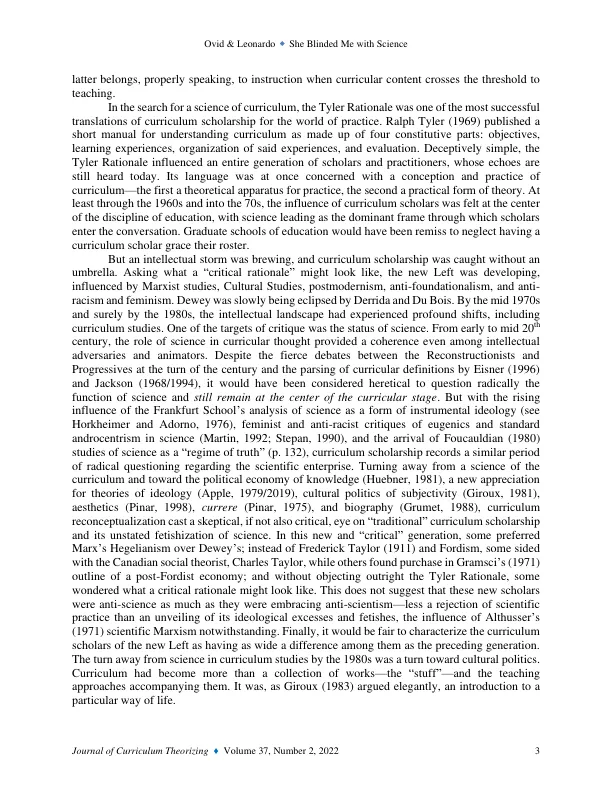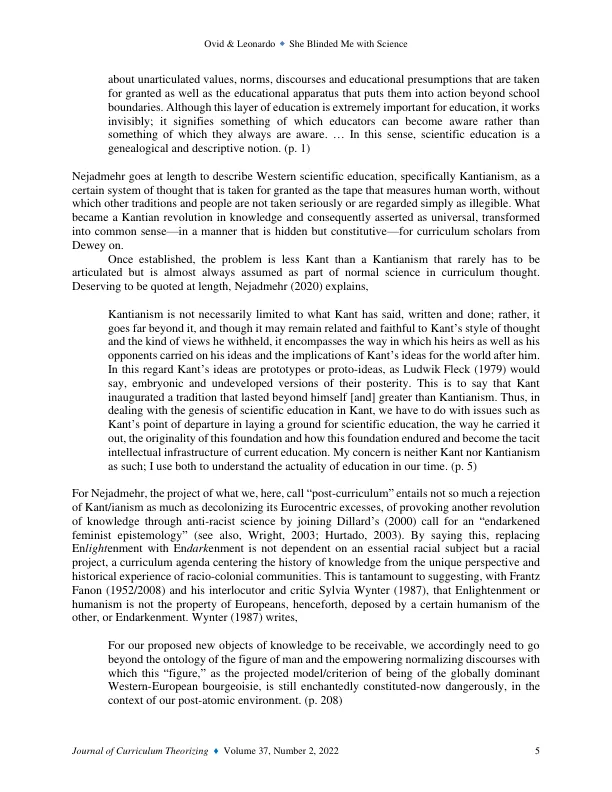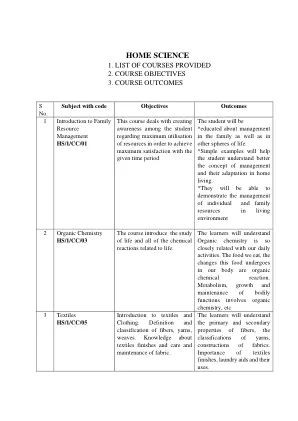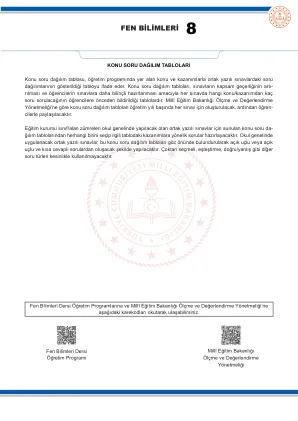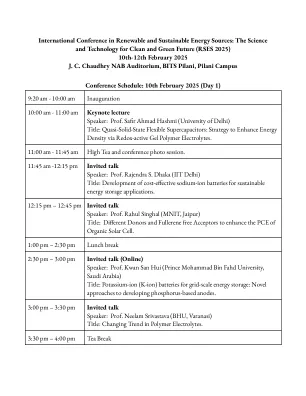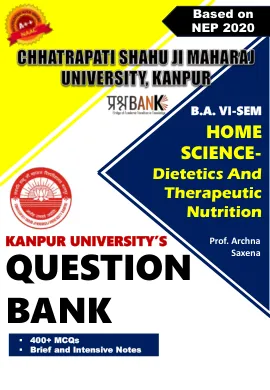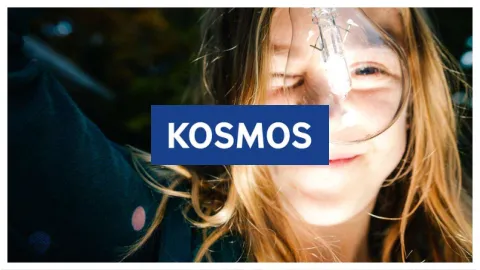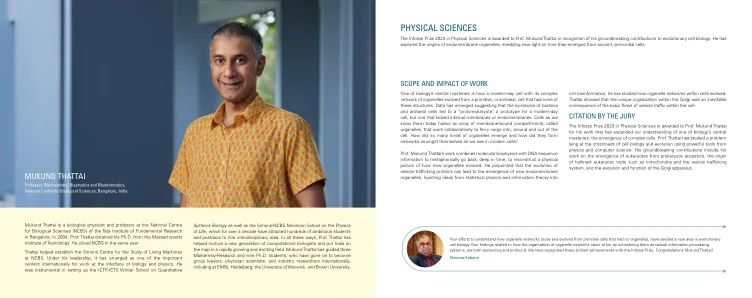机构名称:
¥ 4.0
达克斯·奥维德大学佐治亚大学,雅典宙斯·莱昂纳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本文,我们基于其与科学作用的关系重新检查了课程研究的历史。我们不关心科学教育本身,而是Rasoul Nejadmehr(2020)称之为“科学教育”或教育科学的要素,特别是与课程有关的要素。在现在的经典文本中,克利巴德(Kliebard)的《 1986/2004)《美国课程的斗争》在课程研究领域占有特权。kliebard在课程奖学金流中介绍了四个强大的“电流”(与摆动相对):人文主义,儿童发展主义,社会忧郁症和社会效率(第208页)。kliebard将四个框架及其支持者描述为彼此挣扎,成为推动学校实践的指导规范。同样,由库恩(Kuhn)(1970)的范式研究捕获,他们竞争课程研究中正常科学的地位,对此进行了所有其他观点。现在,学院的命名法的一部分,范式不仅仅是学者碰巧接受或拒绝的观点。范式在认知和政治意义上施加压力,因为我们试图理解社会现象。他们提供了一个模式,通过该模式可以看出某些模式,或者同样重要,因为它们不符合正常情况,因此使其变得无形。更深刻的是,许多科学家(现在包括社会科学家和课程学者)不仅仅是反对主导范式,而是通过制作新范式来代替它来取代它。Kliebard(1992)提供了课程的最有用的历史之一,即当代课程学者可能会利用。,但他并不专注于科学在他所说的美国课程中的作用和演变。我们认为,科学的核心作用介导了斗争的原本完整而几乎永恒的感觉。
她用科学蒙蔽了我
主要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