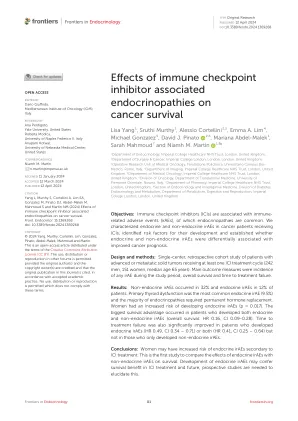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SLC30A8 基因座的多种遗传变异影响局部超级增强子活性并影响胰腺 β 细胞的存活和功能
缩写:3C,染色体构象捕获;4C,环状染色体构象捕获;ATAC-seq,使用测序检测转座酶可及染色质;Cas9,来自化脓性链球菌的内切酶;CHIP-seq,染色质免疫沉淀和 DNA 测序;CRISPR,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TCF,CCCTC 结合因子;EXT1,外骨化素糖基转移酶 1;GSIS,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GWAS,全基因组关联研究;MED30,RNA 聚合酶 II 转录亚基 30 的介质;pcHi-C,启动子捕获 Hi-C;R,调控区;RAD21,双链断裂修复蛋白 rad21 同源物;SLC30A8,溶质载体家族 30 成员 8;SNP,单核苷酸多态性; T2D,2 型糖尿病;TAD,拓扑关联结构域;UTP23,UTP23 小亚基加工体成分。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内分泌病的影响对癌症存活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通过促进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细胞死亡来上调适应性免疫系统。这样做,ICIS以出色的反应率彻底改变了癌症护理,并改善了多种癌症类型的总体生存率(1)。最近,有人提出ICI在更罕见的肿瘤亚型(如pha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中也可能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2)。ICI分为三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和编程的死亡凸 - 辅助法(PD-L1)抑制剂(1)。ipilimumab是要批准的第一个ICI,并且仍然是常用的CTLA-4抑制剂,靶向CTLA-4在CD4阳性和CD8阳性T淋巴细胞上。迅速进行了抗PD-1疗法,包括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将PD-1靶向CD8阳性T淋巴细胞。更多的新型抗PD-L1疗法,包括atezolizumab,avelumab和durvalumab,直接与肿瘤本身表达的PD-L1结合(3)。虽然ICIS对免疫系统的激活提供了显着的治疗性好处,但这些药物也与免疫相关的不良事件(IRAE)有关,这可能是对预测,诊断和治疗的具有挑战性(3)。iraes通常以含有CTLA-4抑制剂的治疗方案的剂量依赖性出现,但对于用作单一疗法的PD-1和PD-L1抑制剂的PD-1和PD-L1抑制剂的预测较低(4,5)。通常,IRAE通常发生在治疗的第一个月中,但可以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的任何时间出现(6)。iraes可以发生在任何器官系统中,但在具有广泛环境界面(例如皮肤,肺,肝脏和胃肠道)或自身免疫倾向增加(例如甲状腺和关节)的患者中更频繁地发生。内分泌IRAE是接受ICI治疗的患者中最常见的伊拉斯之一,根据ICI类型的不同(5,7),其发病率为15-40%。最常见的内分泌伊拉斯包括甲状腺功能障碍,原发性肾上腺不足,降低症和免疫介导的糖尿病(5)。与其他伊拉斯一样,在治疗的第一个几个月中,发病更为常见,但也可以在治疗期间和之后的任何时间发生(5)。内分泌iraes由于内分泌病的非特异性表现而经常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诊断,这些表现可能与癌症相关或与治疗相关的并发症重叠(例如,疲劳,性欲,性欲,抑郁症,抑郁症)(5)(5)。尽管与其他IRAE相比,但经常被认为是温和的,但由于已经报道了紧急情况和死亡,但内分泌伊拉斯可以出现,强调需要迅速识别和治疗(8,9)。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抑制剂治疗对晚期或复发性子宫癌患者存活的影响:荟萃分析
结果:接受PD-1抑制剂的患者的OS(HR,0.65,95%CI,0.59 - 0.72; p <.001)和PFS(HR,0.59,95%CI,0.49 - 0.70; P <.001)都比那些接受可变的非PD-1 in pd-1 in抑制剂患者的患者中的3.452 cancer in cance in cance中。OS HR的剩余荟萃分析对整体效应大小的估计没有任何个人研究影响。亚组分析显示,PD-1抑制剂使用的OS比宫颈癌中的对照(HR,0.68,95%CI,0.59 - 0.79),子宫内膜癌(HR,0.62,95%CI,0.54-0.72)和0.54-0.72)和Pembrolizumab使用(pembrolizumab subseps subseps subsobs subseps subsefs 0.65%ci,95%CI,95%CI,95%CII,95%,95%,95%,95%,95%,95%,95%,95%CII。与对照组相比,患有CPS> 1的晚期宫颈癌患者在OS上具有统计学上的好处(HR,0.65,95%CI,0.53-0.80)。与未接受PD-1抑制剂的患者相比,与未接受PD-1抑制剂的患者相比,对接受PD-1抑制剂的患者的总生存率为0.71(95%CI,0.60-0.82; p <.001)。但是,在有效的MMR患者中,HR为0.30(95%CI,
多种酶系统的代谢启动支持早期缺氧的糖酵解,HIF1α稳定和人类癌细胞的存活
适应慢性缺氧是通过蛋白质表达的变化而发生的,蛋白质表达受到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控制,对于癌细胞存活是必要的。然而,在HIF1α介导的转录程序完全确定之前,使癌细胞能够适应早期缺氧的机制仍然很少了解。在这里,我们在人类乳腺癌细胞中表明,在缺氧暴露3小时内,糖酵解液以HIF1α非依赖性方式增加,但受NAD +可用性的限制。早期缺氧的糖酵解ATP维持和细胞存活依赖于储备乳酸脱氢酶A的能力以及谷氨酸 - 氧化甲酸乳凝集酸酯酸酯酸酯酶1(GOT1)的活性,该酶是一种燃料的酶,该酶燃料母体脱氢酶1(MDH1)衍生的NAD NAD +。此外,GOT1保持较低的α-酮戊二酸水平,从而限制了早期缺氧中HIF1α稳定的丙酰羟化酶活性,并在后期缺氧中启用强大的HIF1α靶基因表达。我们的发现表明,在北莫西亚中,多种酶系统将细胞保持在启动状态下,准备支持增加糖酵解的糖酵解和HIF1α稳定在氧气限制下,直到其他需要更多时间的自适应过程已完全确定为止。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和辅助化疗后胃癌患者的存活:经典试验的事后分析
©作者,在Springer Nature Limited的独家许可下2023。该文章的此版本已被接受,在同行评审(适用时)之后,并受到Springer Nature的AM使用条款的约束(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gp/open- research/laticies/clestion/comented-compacted-manuscript-terms),但并不反映记录和任何更正后的记录和任何更正的记录。记录版本可在线获得:http://dx.doi.org/10.1038/s41416-023-02257-3
微生物在国际空间站附近外层空间暴露两年期间的存活情况
在这些长达六个月的研究中,表明生物物体和微生物能够在各种破坏因素的影响下生存。然而,在这些实验中,测试了有限数量的外层空间物理因素的影响。例如,在“Exposure-R”实验[5,6]中,研究了宇宙紫外线对研究样本的影响,并在对照陆地实验中模拟,这些样本被浓缩到特殊的聚合物袋中,然后放置在金属三层轨道中,从而保护生物物体免受太空真空的影响。在“Biorisk”实验[8,9]中,研究了微生物对宇宙真空参数影响的抵抗力,金属主体保护微生物免受紫外线的作用。在“Tanpopo”实验中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及其微生物在蘑菇加工表面的生物膜形成和干燥存活以及清洁和消毒的影响
在食品加工环境中使用的材料上可以建立由背景微生物群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组成的微生物多物种群落。这些微生物多物种群落中菌株的存在、丰度和多样性可能受到相互作用和对常规清洁和消毒 (C & D) 程序的抵抗力差异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表征在没有和存在多种背景微生物群 (n = 18) 的情况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菌株混合物 (n = 6) 在聚氯乙烯 (PVC) 和不锈钢 (SS) 上形成生物膜过程中的生长和多样性。从蘑菇加工环境中分离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背景微生物菌株,并在模拟蘑菇加工环境条件下进行实验,使用蘑菇提取物作为生长培养基,以环境温度 (20 ◦ C) 作为培养温度。在单一物种生物膜培养期间施用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菌株在 PVC 和 SS 试样上均形成生物膜,并使用氯化碱性清洁剂和基于过氧乙酸和过氧化氢的消毒剂进行四轮 C & D 处理。每次 C & D 处理后,在总共 8 天的培养期内将试样重新培养两天,C & D 可有效去除 SS 上的生物膜(减少量为 4.5 log CFU/cm 2 或更少,导致每次 C & D 处理后计数都低于检测限 1.5 log CFU/cm 2 ),而对 PVC 上形成的生物膜进行 C & D 处理产生的减少量有限(减少量在 1.2 到 2.4 log CFU/cm 2 之间,分别相当于减少量 93.7 % 和 99.6 %)。在多物种生物膜培养过程中,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菌株与微生物群一起培养,48 小时后,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在生物膜中形成,因此 SS 和 PVC 上的多物种生物膜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菌株多样性较高。C & D 处理可从 SS 上的多物种生物膜群落中去除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减少 3.5 log CFU/cm 2 或更少,导致每次 C & D 处理后计数低于 1.5 log CFU/cm 2 的检测限),在不同的 C & D 周期中,微生物群落物种的优势有所不同。然而,与单一物种生物膜相比,PVC 上多物种生物膜的 C & D 处理导致李斯特菌的减少量较低(介于 0.2 和 2.4 log CFU/cm 2 之间),随后李斯特菌重新生长,肠杆菌科和假单胞菌稳定占主导地位。此外,在没有和存在浮游背景微生物群培养物的情况下,李斯特菌的浮游培养物沉积在干燥表面上并干燥。与 PVC 相比,SS 上观察到的干燥细胞计数随时间的下降速度更快。然而,C & D 的应用导致两个表面上的计数低于 1.7 log CFU/coupon 的检测限(减少 5.9 log CFU/coupon 或更少)。这项研究表明,在 C & D 处理后,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能够在 PVC 上形成单一和多种生物膜,并且菌株多样性高。这突出表明需要对 PVC 和类似表面应用更严格的 C & D 制度处理,以有效去除食品加工表面的生物膜细胞。
在15年内,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中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药物存活率的变化
摘要。目标。在15年内,在15年内,在类风湿关节炎(RA),银屑病关节炎(PSA)和障碍性脊柱炎(AS)中,研究了第一种生物疾病修饰的抗肿瘤药物(DMARD)治疗的变化。方法。我们评估了在2004年至2019年在阿姆斯特丹风湿病学和免疫学中心,荷兰雷德(Reade)的常规护理中,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风湿病学和免疫学中心进行了生物学特征和药物存活。开始分为早期(2004-2008),中级(2009-2013)和最近(2014- 2018年)。Kaplan-Meier图和对数秩检验评估了3个观察组和诊断之间药物存活的总体差异,然后进行COX回归对估计危险比(HRS)。结果。我们包括1938年连续开始TNFI疗法的患者,有63%的RA,19%的PSA和19%的AS;女性为65%。随着时间的流逝,药物存活率显着降低(总体p <0.001),主要是由于最近4年的降低而引起的。对于早期组,药物持续的HR为2.04(95%CI 1.71-2.43,p <0.001),中间组的HR为1.92(95%CI 1.58-2.35,p <0.001)。药物的生存时间在疾病之间显着差异(总体p <0.001),主要是由于RA中较短的生存率引起的。RA vs PSA的药物持续性HR为0.58(95%CI 0.47-0.73,p <0.001),RA与AS的HR为0.63(95%CI 0.51-0.78,p <0.001)。结论。患有RA,PSA和目前开始生物学(TNFI)疗法的患者停止使用该药物的时间要比引入药物后不久的患者要早得多。 这很可能是因为替代性新型生物学和靶向合成DMARD处理以及对靶向目标方案的可用性可用,并需要提前切换。患有RA,PSA和目前开始生物学(TNFI)疗法的患者停止使用该药物的时间要比引入药物后不久的患者要早得多。这很可能是因为替代性新型生物学和靶向合成DMARD处理以及对靶向目标方案的可用性可用,并需要提前切换。
低酒精和无酒精精酿啤酒中食源性病原体的存活情况
近来,啤酒厂和饮料公司对开发有别于传统啤酒风格的创新啤酒品种很感兴趣,这些啤酒要么酒精含量低(<2.5% 体积酒精度 (ABV))要么完全不含酒精(<0.5% ABV)。传统啤酒(ABV 高达 10%)含有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可防止病原体增殖或繁殖。低 pH 值、乙醇和啤酒花酸的存在、有限的氧气以及特殊的加工技术(包括麦汁煮沸、巴氏灭菌、过滤、冷藏和处理)等理化特性均有助于微生物稳定性和安全性。这些抗菌屏障中的一个或多个可能发生变化或缺失,可能导致最终产品易受病原体存活和生长的影响。本研究评估了 pH 值、储存温度和乙醇浓度对低酒精和无酒精啤酒中食源性病原体生长或死亡的影响。 pH 值和乙醇浓度分别从初始值 3.65 和 <0.50% ABV 调整为 pH 4.20、4.60 和 4.80;以及 3.20 ABV。样品分别接种大肠杆菌 O157:H7、肠道沙门氏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五种菌株混合物,然后在两个不同的温度(4 和 14°C)下储存 63 天。使用选择性琼脂在 35°C 下孵育进行微生物计数。结果表明,与低酒精啤酒相比,无酒精啤酒允许病原体生长和存活。大肠杆菌 O157:H7 和肠道沙门氏菌在 14°C 时生长约 2.00 对数,但在 4°CL 下未观察到生长,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更敏感,在所有测试条件下都迅速降至或低于检测限。结果表明,储存温度对于防止病原体的生长至关重要。pH 值似乎对病原体的存活没有显著影响(p < 0.05)。这项挑战性研究表明,饮料制造商需要优先考虑和维护食品安全计划,以及针对低酒精和无酒精啤酒制造商的具体做法。
在15年内,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中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药物存活率的变化
摘要。目标。在15年内,在15年内,在类风湿关节炎(RA),银屑病关节炎(PSA)和障碍性脊柱炎(AS)中,研究了第一种生物疾病修饰的抗肿瘤药物(DMARD)治疗的变化。方法。我们评估了在2004年至2019年在阿姆斯特丹风湿病学和免疫学中心,荷兰雷德(Reade)的常规护理中,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之间,在2004年至201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风湿病学和免疫学中心进行了生物学特征和药物存活。开始分为早期(2004-2008),中级(2009-2013)和最近(2014- 2018年)。Kaplan-Meier图和对数秩检验评估了3个观察组和诊断之间药物存活的总体差异,然后进行COX回归对估计危险比(HRS)。结果。我们包括1938年连续开始TNFI疗法的患者,有63%的RA,19%的PSA和19%的AS;女性为65%。随着时间的流逝,药物存活率显着降低(总体p <0.001),主要是由于最近4年的降低而引起的。对于早期组,药物持续的HR为2.04(95%CI 1.71-2.43,p <0.001),中间组的HR为1.92(95%CI 1.58-2.35,p <0.001)。药物的生存时间在疾病之间显着差异(总体p <0.001),主要是由于RA中较短的生存率引起的。RA vs PSA的药物持续性HR为0.58(95%CI 0.47-0.73,p <0.001),RA与AS的HR为0.63(95%CI 0.51-0.78,p <0.001)。结论。患有RA,PSA和目前开始生物学(TNFI)疗法的患者停止使用该药物的时间要比引入药物后不久的患者要早得多。 这很可能是因为替代性新型生物学和靶向合成DMARD处理以及对靶向目标方案的可用性可用,并需要提前切换。患有RA,PSA和目前开始生物学(TNFI)疗法的患者停止使用该药物的时间要比引入药物后不久的患者要早得多。这很可能是因为替代性新型生物学和靶向合成DMARD处理以及对靶向目标方案的可用性可用,并需要提前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