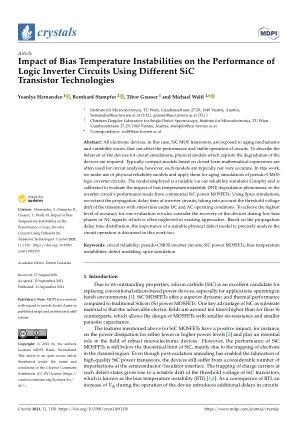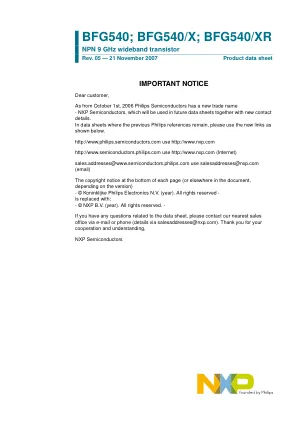XiaoMi-AI文件搜索系统
World File Search System负电容铁电场效应晶体管
将铁电负电容 (NC) 集成到场效应晶体管 (FET) 中有望突破被称为玻尔兹曼暴政的功耗基本限制。然而,在非瞬态非滞后状态下实现稳定的静态负电容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问题源于缺乏对如何利用由于域状态出现而产生的 NC 的根本起源来实现 NC FET 的理解。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铁电域的场效应晶体管的巧妙设计,具有稳定的可逆静态负电容。使用铁电电容器的电介质涂层可以实现负电容的可调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场效应晶体管的性能。
用于监测的有机电化学晶体管...
专用阻抗系统的引入。[4] 其最简单的形式是,在浸入细菌培养物的一对电极上测量单一频率的交流阻抗。[5] 随着细菌的生长,培养基的电导率会发生变化[6],这是细菌代谢的结果,不带电的底物会转化为带电的代谢物。[4,7] 这反过来又导致阻抗的变化。[5] 事实证明,阻抗优于通常用于尿液[8] 和血液中细菌检测的菌落形成单位计数。[9,10] 研究发现,培养基的电导率与吸光度监测的细菌生长有很好的相关性。[11] 尽管该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只有少数阻抗传感器实现了商业化,主要是因为检测限不令人满意且生产成本高。 [5] 1977 年共轭聚合物的发现和有机生物电子学的出现,为科学界提供了能够进行离子和电子传输的低成本、易于加工的材料。[12,13] 这导致了微生物学和感染研究的创新方法和新型设备的开发。[14–17]
使用不同的SIC晶体管技术
摘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电子设备都暴露于老化的机制和可变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电路的性能和稳定运行。要描述电路模拟设备的行为,需要捕获设备降解的物理模型。通常基于封闭形式数学表达式的紧凑模型通常用于电路分析,但是,这种模型通常不是很准确。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使用物理可靠性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伪CMOS逻辑逆变器电路的老化模拟。采用的模型可通过我们的可靠性模拟器构成获得,并经过校准,以评估偏置温度不稳定性(BTI)降解现象对逆变器电路的性能由商业SIC Power MOSFET制成的性能。使用香料模拟,我们提取逆变器电路的传播延迟时间,并考虑到在DC和AC工作条件下的压力时间的晶体管阈值电压漂移。为了达到评估的最高准确性,我们还考虑在AC信号的低偏置阶段回收设备的恢复,这在现有方法中通常被忽略。基于传播延迟时间分布,在本工作中也讨论了合适的物理缺陷模型精确分析电路操作的重要性。
神经形态应用的电解晶体管
摘要:冯·诺伊曼(Von Neumann)计算机目前未能遵循摩尔定律,受到冯·诺伊曼(Von Neumann)瓶颈的限制。为增强计算性能,正在开发可以模拟人脑功能的神经形态计算系统。人造突触是神经形态结构的必不可少的电子设备,它们具有在相邻的人造神经元之间执行信号处理和存储的能力。近年来,电解质门控晶体管(EGT)被视为模仿突触动态可塑性和神经形态应用的有前途的设备。在各种电子设备中,基于EGT的人工突触提供了良好稳定性,超高线性和重复循环对称性的好处,并且可以从多种材料中构造。他们还在空间上分开“读”和“写”操作。在本文中,我们对神经形态应用的电气门控晶体管领域的最新进展和主要趋势进行了回顾。我们介绍了电动双层的操作机理和基于EGT的艺术突触的结构。然后,我们回顾了基于EGT的人工突触的不同类型的通道和电解质材料。最后,我们回顾了生物学功能中的潜在应用。
低功耗软晶体管引发电子革命
自20世纪40年代问世以来,晶体管就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作为逻辑门和集成电路(芯片)的核心元件,晶体管无疑在推动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显示器、物联网乃至所有电子或电气系统的发展方面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过去几十年来,主流晶体管通常由硅材料和金属氧化物等无机半导体制成,有利于实现高迁移率、快速开关速度和优异的稳定性。因此,硅晶体管和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应用。然而,尽管这些晶体管的制造规模要小得多以满足摩尔定律的预测,但它们却非常坚硬,并且几乎接近速度和功耗的基本极限。由于未来对具有机械灵活性/坚固性和低功耗的晶体管的需求,功能材料、设备配置和集成处理技术的创新以促进从刚性设备到柔软、耐用和生物相容性的设备的演变势在必行。1
顶部接触有机电化学晶体管-NSF-PAR
有机电化学晶体管(OECTS)将离子转换为电信号,这使它们成为广泛的生物电子应用的有前途的候选人。,尽管他们承诺,但仍未完全了解其设备几何形状对性能的影响。在此,将两个不同的设备几何形状(顶部接触和底部接触OECT)根据其接触性,可重复性和开关速度进行比较。表明,底部接触设备的切换时间更快,而其顶部接触式对应器在略有降低的接触抗性和增加的可重复性方面表现出色。讨论了速度和可重复性之间这种权衡的起源,该速度和可重复性之间的权衡为特定应用程序提供了优化指南。
BFG540/XR NPN 9 GHz 宽带晶体管
NPN 硅平面外延晶体管,适用于 GHz 范围内的宽带应用,例如模拟和数字蜂窝电话、无绳电话(CT1、CT2、DECT 等)、雷达探测器、卫星电视调谐器 (SATV)、MATV/CATV 放大器和光纤系统中的中继放大器。
基于二维材料的晶体管,用于未来集成电路
硅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 技术的缩放已达到 10 纳米以下技术节点,但进一步缩放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为器件的栅极静电要求大幅减少沟道厚度以保持所需的性能 1 。场效应晶体管 (FET) 的最终沟道厚度可能在 1 纳米以下范围内。但是,任何三维 (3D) 半导体晶体都无法轻易实现这一点,因为在沟道到电介质界面处电荷载流子的散射增加,导致迁移率严重下降 2 。二维 (2D) 半导体材料单层厚度约为 0.6 纳米,可以提供解决方案。这类材料包括过渡金属二硫属化物 (TMD),其通式为 MX 2 ,其中 M 是过渡金属(例如,Mo 或 W),X 是硫属元素(例如,S、Se 或 Te)3 – 8。材料中没有悬空键也提供了实现更好的通道到电介质界面的潜力。基于机械剥离的单晶 2D 薄片的早期研究,以及基于大面积生长的合成 2D 单层的最新发展,都表明了 2D 晶体管的良好特性。然而,仍有许多挑战有待解决,这使得 2D FET 在未来超大规模集成 (VLSI) 技术中的应用潜力尚不明确。在本篇评论中,我们探讨了 2D FET 在未来集成电路中的发展。我们首先考虑大面积生长
用于高效功率转换的 GaN 晶体管...
四十多年来,随着功率金属氧化物硅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结构、技术和电路拓扑的创新与日常生活中对电力日益增长的需求保持同步,电源管理效率和成本稳步提高。然而,在新千年,随着硅功率 MOSFET 渐近其理论界限,改进速度已经放缓。功率 MOSFET 于 1976 年首次出现,作为双极晶体管的替代品。这些多数载流子器件比少数载流子器件速度更快、更坚固,电流增益更高(有关基本半导体物理的讨论,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是 [1])。因此,开关电源转换成为商业现实。功率 MOSFET 最早的大批量消费者是早期台式计算机的 AC-DC 开关电源,其次是变速电机驱动器、荧光灯、DC-DC 转换器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成千上万的其他应用。最早的功率 MOSFET 之一是国际整流器公司于 1978 年 11 月推出的 IRF100。它拥有 100V 漏源击穿电压和 0.1 Ω 导通电阻 (R DS(on)),堪称当时的标杆。由于芯片尺寸超过 40mm2,标价为 34 美元,这款产品注定不会立即取代备受推崇的双极晶体管。从那时起,几家制造商开发了许多代功率 MOSFET。40 多年来,每年都会设定基准,随后不断超越。截至撰写本文时,100V 基准可以说是由英飞凌的 BSZ096N10LS5 保持的。与 IRF100 MOSFET 的电阻率品质因数 (4 Ω mm 2 ) 相比,BSZ096N10LS5 的品质因数为 0.060 Ω mm 2 。这几乎达到了硅器件的理论极限 [2]。功率 MOSFET 仍有待改进。例如,超结器件和 IGBT 已实现超越简单垂直多数载流子 MOSFET 理论极限的电导率改进。这些创新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肯定能够利用功率 MOSFET 的低成本结构和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设计人员的专业知识,这些设计人员经过多年学习,已经学会了从功率转换电路和系统中榨干每一点性能。